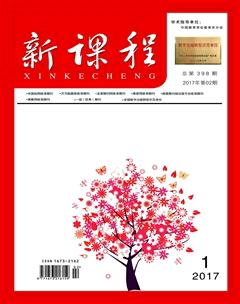人品塑造與早期教育的關系
王小麗+袁佩奇
摘 要:早期教育是按照嬰幼兒身心發(fā)展的規(guī)律實施的一種全面教育,抓緊早期教育,可以提高學習效果,促進幼兒的智力發(fā)展,早期教育是幼兒塑造人格的關鍵時期,探討了人品塑造與早期教育的關系,人品塑造中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早期教育中人品塑造的方法。
關鍵詞:人品塑造;早期教育;關系
社會的發(fā)展與不斷進步,人們對于早期教育有了更多的認識,越來越意識到早期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早期教育是由成人對嬰幼兒實施的教育,是人生的啟蒙教育,對于嬰兒人品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早期教育對人品塑造的體現(xiàn)
不同的年齡階段,早期教育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周歲以內(nèi)的兒童以感官功能訓練、動作訓練、語言發(fā)聲訓練為主,從而與兒童互動,周歲至3歲兒童在此基礎上還應加入感知動作思維,連貫性動作與活動,語言、玩伴交往及個性形成等方面的訓練和培養(yǎng),早期教育是對0~6歲嬰幼兒及其父母、嬰幼兒與父母之間開展的、有助于身體、情感、智力、人格、精神等多方面的綜合發(fā)展與健康成長的互動式活動。
(一)活動訓練
各式各樣的活動,對于早期教育中的人格塑造起著關鍵的作用,活動能夠培養(yǎng)兒童豐富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力,具體的活動訓練可有游戲設施、腦力活動與勞動活動等,兒童玩耍的游戲設施可以是一些滑滑梯、蹺蹺板、蹦蹦床等設施,游戲與玩耍可以很大程度上釋放孩子的天賦,激發(fā)孩子的潛能,培養(yǎng)兒童活潑的性格,鍛煉兒童的身體素質(zhì),腦力活動可以讓兒童搭建積木、教兒童識字、讀書等,培養(yǎng)兒童的智力,勞動活動也是很有必要的,可以讓兒童掃地、為花澆水、喂食小動物等,鍛煉孩子的動手能力以及培養(yǎng)愛護小動物的情感。
(二)人際交往
讓兒童多接觸同齡的兒童,通過建立伙伴關系,促進兒童早期自我意識的發(fā)展,與同齡兒童建立良好的關系,能夠一定程度上避免兒童形成孤僻、自卑、自傲等方面的心理,實踐證明,不善于交友的兒童往往就形成了各種不健康、不利于兒童發(fā)展的心理,善于交友的兒童能夠從對方身上進行一定的模仿,取長補短,相互促進,進而形成優(yōu)良的品格,比如謙讓、禮貌、自尊、自信、樂于助人等。
二、早期教育中塑造人格的重要性
(一)社會發(fā)展的需求
現(xiàn)今社會的發(fā)展趨勢要求塑造完美人格,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需要人才的培養(yǎng),社會更加關注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發(fā)展的任務是使每個人能夠發(fā)展自己的才能與創(chuàng)造的能力,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yǎng)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人。
(二)素質(zhì)教育的提倡
塑造完美的人格是素質(zhì)教育的目標之一,素質(zhì)教育是以提高受教育者全方面素質(zhì)為目標的教育模式,關注人的思想道德素質(zhì)、個人能力的培養(yǎng)、個性發(fā)展、身心健康的教育,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質(zhì)是素質(zhì)教育的核心內(nèi)容,已經(jīng)逐步取代傳統(tǒng)的應試教育,素質(zhì)教育下更注重對早期教育的人格培養(yǎng),早期教育是最基礎性的階段,促進素質(zhì)教育的發(fā)展,對塑造兒童健全人格有著重要的作用。
三、早期教育塑造人格的方法
(一)愛的體現(xiàn)
給予兒童溫暖,讓兒童感受到愛意,家庭的愛與老師的愛都很重要,幼兒剛出生時,撫摸他,抱著他,讓孩子感受到安全感,孩子通過接受第一次情感交流,慢慢地發(fā)展成愛,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要時刻對孩子進行愛的引導,傳達愛意,為塑造良好健全的人格打下基礎。
(二)情感體現(xiàn)
情感是后天形成的,大人可以在孩子的面前照顧老人,關心老人等,通過一定的模仿形式激發(fā)孩子對長輩以及同齡的愛,引導孩子用行動去表現(xiàn)愛,培養(yǎng)孩子的情感,一定程度上引導孩子學會從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樹立孩子的情感意識,帶領孩子去感受外部世界,體驗不一樣的感受,增強孩子的情感認知。
(三)游戲體驗
孩子在游戲中可以發(fā)揮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力,增強孩子的群體意識,培養(yǎng)孩子的意志力,為孩子提供游戲材料,讓孩子自己選擇玩耍的方式,讓孩子在游戲中掌握主動性;讓孩子進行角色扮演,履行規(guī)則義務,培養(yǎng)孩子的責任心,擴大孩子的游戲場所,不要只局限在室內(nèi),組織孩子與其他同齡階段的孩子一起去室外活動,提高孩子的交際能力;在進行游戲活動時,給孩子設立一些規(guī)則,或者由孩子自己設立規(guī)則,必須按照規(guī)則去進行游戲,有利于提高孩子的自制能力,給孩子安排一定量的競爭游戲,讓孩子體會輸贏的感受,并適當?shù)亟逃⒆虞斱A不重要的理念,游戲對于塑造孩子的人格具有很大的作用。
早期教育對于培養(yǎng)孩子的人格起著關鍵的作用,也是塑造孩子人品的重要階段,塑造孩子健全的人格,促進孩子未來的發(fā)展,人品塑造與早期教育相互作用,密切聯(lián)系。
參考文獻:
[1]高敬.早期教育機構質(zhì)量的重要性、內(nèi)涵與評價[J].學前教育研究,2011.
[2]扶躍輝,李燕.美國“以家庭為中心”的早期教育[J].外國中小學教育,2015.
[3]何聲清.靜待花開:早期教育的應然轉向:從“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說起[J].現(xiàn)代中小學教育,2013.
[4]鐘偉濤,王慶林.從中國傳統(tǒng)教育看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論依據(jù)[J].教學理論,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