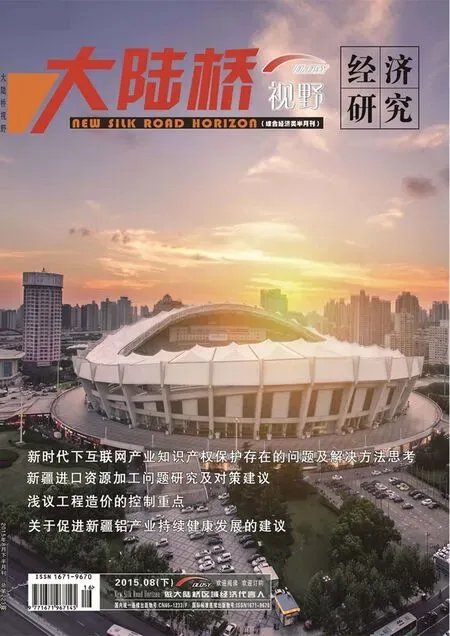對治理沙漠化的再思考
呂 稚
對治理沙漠化的再思考
呂 稚
沙漠化,是對世界農業發展的一個重大威脅。它使土地滋生能力退化,農牧生產能力降生物產量下降,可供耕地及牧場面積減少。由于沙漠化而致的水土流失、土地貧瘠,已使不少國家招致連年饑荒。本文重點研究了沙漠化現象的成因、危害以及防治對策。
沙漠化 防治對策
土地沙漠化,簡單地說土地沙漠化就是指土地退化,也叫“沙漠化”。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對荒漠化的概念作了這樣的定義:荒漠化是由于氣候變化和人類不合理的經濟活動等因素,使干旱、半干旱和具有干旱災害的半濕潤地區的土地發生了退化。沙漠化,是對世界農業發展的一個重大威脅。它使土地滋生能力退化,農牧生產能力降生物產量下降,可供耕地及牧場面積減少。由于沙漠化而致的水土流失、土地貧瘠,已使不少國家招致連年饑荒。
一、沙漠化現象的成因
沙漠化指原由植物覆蓋的土地變成不毛之地的自然災害現象。此處所指的“沙漠”多數強調土地不適合植物生長或發展農業,而非因為地域本身干燥所造成的沙漠氣候。不過,沒有植物生長的土地由于不能蒸散分配水分,結果也可能反而導致干燥氣候。
沙漠化現象可能是自然的。作為自然現象的沙漠化是因為地球干燥帶移動,所產生的氣候變化導致局部地區沙漠化。不過,今日世界各地沙漠化原因,多數歸咎于人為原因;人口急速增長,所居土地被過分耕種以及牧畜,導致土地枯竭不適合耕種。干地(定義為降水量低且降水通常由雨量小、不穩定、時間短、強度大的風暴造成的那些地區)覆蓋了全球40%的陸地面積,供養著世界上1/5的人口。這些干地的沙漠化是由于植被和可利用的水減少、作物產量下降以及土壤侵蝕引起的土地退化,它起因于人口增長、人類需求增加或者政治、經濟壓力(例如,需要經濟作物來增加外匯)造成的過度土地利用,通常由自然發生的干旱啟動或加劇。目前,沙漠化的速率是每年6萬平方千米或每年0.1%的總干地面積。這對于70%的干地(全球陸地面積的25%)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二、沙漠化的危害
沙漠化,是對世界農業發展的一個重大威脅。沙漠化是一種環境退化現象。它使土地滋生能力退化,農牧生產能力降低,生物產量下降,可供耕地及牧場面積減少。由于沙漠化而致的水土流失、土地貧瘠,已使不少國家招致連年饑荒。全球受沙漠化影響的土地已達3800萬平方千米。因沙漠化而失的土地,每年都高達5~7平方千米,幾乎每分鐘就有11頃的土地被沙漠化。
我國也是一個土地沙漠化嚴重的國家,沙化土地每年以60平方千米的速度增長。我國土地沙漠化的形成,除了因外力作用而造成沙丘前移入侵的自然因素以外,由于過度開墾、過度放牧、過度砍伐、工業交通建設等破壞植被的人為因素引起沙漠化的現象更為普遍。尤其是在新疆這個本來就缺水的省份,表現尤為突出。據統計,截止2009年底,新疆荒漠化土地總面積為107.12萬平方千米,占新疆國土總面積的64.34%。分布于伊犁州(州直屬、塔城、阿勒泰)、昌吉、吐魯番、哈密、巴音郭楞、阿克蘇、喀什、克爾克孜、博爾塔拉、和田、克拉瑪依、烏魯木齊14個地(州、市)及4個自治區直轄縣級市中的79個縣(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75個農墾團場。荒漠化土地分布范圍廣,各氣候類型區荒漠化類型齊全,且危害程度較重。因此,保護和利用好土地,封沙育草,營造防風沙林,實行林、牧、水利等的綜合開發治理,將會充分發揮植群體效應以達到退沙還土的目的。土壤是植物的母親,是綠色家園繁榮昌盛的物質基礎。保護和利用好土地,就是保護了綠色家園,保護了人類自己。
三、防治沙漠化的對策和建議
1.嚴肅法紀,懲治行政腐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規。與防治沙漠化有關的有《環境保護法》《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還制定了與這些法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規。這些法律法規之所以稱其為法律法規,是因為它們本身具有的權威性、嚴肅性和強制性。在一個法制的社會,沒有凌駕于法之上的權力。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的本身就是非法,為法所不容。因此,任何違背法律法規的行為(包括政府行為)都要依法進行懲處,并給予改正。否則,法不成法,只能助長行政腐敗,擾亂社會秩序。
2.環境問題的決策要有前瞻性和超前意識。我國保護天然林,在長江、黃河中上游首先禁伐天然林的決策是在1996年水災后作出的;而禁止采挖和銷售發菜,制止濫挖甘草和麻黃草的決策也是在2000年春季沙塵暴和揚沙天氣災害連續襲擊北京地區后作出的。這些均系亡羊補牢,是付出了慘痛代價后而痛下決心。事實上,無論是洪澇還是干旱,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學者和媒體發出了“長江有變成黃河的危險”“風沙緊逼北京城”這樣的警告。我國高層決策者也并非置若罔聞,只是由于涉及廣泛的社會利益群體,而政府的財政支持能力有限,難以當機立斷。然而,凡屬生態環境問題都有一種“疊加效益”,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能事倍功半,不可能遏制住環境加速惡化的步伐,而且將來一旦治理起來,費用也更加高昂,代價也會更加慘重,遠遠超過以生態環境為代價所換取的眼前的和暫時的利益。
3.加大防沙治沙的資金投入。中國治沙工程,由于國家長期投入不足,地方配套資金又很難落實,又因為沙區多是“老、少、邊、窮”地區,地方財力有限。相當一部分群眾尚未解決溫飽,很難拿出錢來防沙治沙。目前,在西北地區,造林一畝成本約100元,每畝治沙工程造林,則需500至600元。過去的辦法是發動農民投工投勞,以彌補造林經費的不足。在現今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計劃經濟時代的低投資水平加行政命令,硬性攤派,無償使用勞動力的辦法越來越行不通了,更何況國務院三令五申不允許加大農民的負擔,如果再不加大對治沙的投入,今后工作勢必出現滑坡。
4.嚴格控制環境的人口容量,退耕與“退人”結合起來。環境對人口的容量是制定社會發展計劃的基礎。我國西部生態極其脆弱,破壞易而恢復難,“地廣人稀”只是一種表面現象。由于環境容量十分有限,許多地區的人口已經超飽和。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北方荒漠化地區人口總數已達4億人,比建國初增加了160‰。新疆160萬平方千米土地,可供人類生存繁衍的綠洲僅有4.5%,目前農區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200~400人,同東部沿海省份的人口密度已不相上下。過墾過牧,造成風沙肆虐。西南地區山高坡陡,土壤瘠薄,植被破壞后石漠化嚴重。石漠化使土地永久喪失生產力,因此比沙漠化問題更嚴重,也更難以治理。
退耕還林還草工作要與“退人”結合起來,在生存條件惡劣的地區,逐步將超過環境容量的人口遷移出來,轉移到小城鎮,以便從根本上解決退耕后反復的問題和“靠山吃山”、繼續破壞植被的問題,給大自然以喘息之機,恢復元氣;同時,發展具有一定規模效應的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農業富余人口,也可以帶動多種產業的發展,增加群眾收入,緩和西部人口壓力與土地承載力之間的矛盾。
5.保護、恢復與重建荒漠生態系統。沙漠化形成與擴張的根本原因,就是荒漠生態系統(包括沙漠、戈壁系統、干旱、半干旱地區的草原系統、森林系統和濕地系統)的人為破壞所致,是對該系統中的水資源、生物資源和土地資源強度開發利用而導致系統內部固有的穩定與平衡失調的結果。以往,我們一手植樹種草,通過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防治沙漠化;另一只手卻在破壞荒漠生態系統,制造新的沙漠化土地。事實上,正是由于荒漠生態系統的破壞,盡管我們營造了“三北”防護林,實施了防沙治沙工程,卻仍然未能在整體上遏制住沙漠化擴張的步伐。可以說,近半個世紀來,沙暴頻發的真正原因,并非人工植被營造太少,而是天然植被破壞過甚。小環境的局部改善,抵消不了大環境的整體逆變。
監測結果顯示,能過這幾年的治理,新疆土地荒漠化、沙化整體擴張趨勢得到初步遏制,荒漠化土地持續減少,但耕地荒漠化形勢不容忽視,沙化土地在局部仍在擴展,但擴展速度持續減緩。2000—2004年,荒漠化土地面積減少14 226平方千米,2005—2009年,荒漠化土地面積減少422.53平方千米。同時,沙化土地擴展持續減緩。2000—2004年,沙化土地面積增加521平方千米,2005—2009年,沙化土地面積增加414.03平方千米。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程度減輕。與2004年相比,輕度荒漠化土地增加2.02萬平方千米,增加15.38%,中度減少0.55萬平方千米,重度增加0.18萬平方千米,極重度減少1.7萬平方千米,減少5.01%。輕度沙化土地面積增加1.24萬平方千米,中度減少0.19萬平方千米,重度減少0.8萬平方千米,極重度減少0.2萬平方千米。植被狀況進一步改善。一是新疆森林覆蓋率已由“十五”末的2.94%提高到現在的4.02%,國家重點公益林區,郁閉度平均提高0.05~0.1,植被蓋度平均提高5%~10%;二是半固定沙地增加,流動沙地減少。5年間,流動沙地減少59.23平方千米,半固定沙地增加269.46平方千米。
監測顯示,受過度放牧、濫開墾、水資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降水量偏少等綜合因素的共同影響,我區塔里木河下游等區域沙化土地處于擴展狀況,但全區整體擴展速度持續減緩。
有鑒于此,我們有必要調整防沙治沙戰略,從片面重視發展人工植被轉到積極發展人工—天然喬灌草復合植被;從單純保護綠洲轉到積極保護包括綠洲在內的整個荒漠生態系統。只有重建荒漠生態系統,才能從根本上遏制住沙漠化擴展的勢頭,扭轉防沙治沙和治理水土流失工作中的被動局面,也才能切實有效地改善我國西北地區的大生態、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