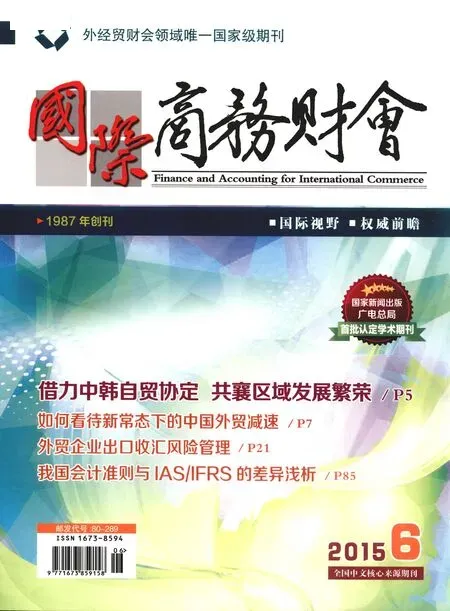如何看待新常態下的中國外貿減速
朱嵩嵩
(商務部政研室)
近年來,中國外貿連續3年低速徘徊。2012年至2014年同比分別僅增長6.2%、7.6%和3.4%,較危機前的高增速降幅明顯,引起高度關注。這背后究竟是經濟周期性波動因素使然?抑或是全球經濟結構調整下的長期性趨勢?本文認為,應立足近幾十年全球價值鏈不斷深化的時代背景,對中國外貿發展進行多維度、多指標研判。
一、從中國與全球經濟關聯視角看:中國外貿減速是中外經濟深度融合的反映
中國的外貿高速增長期,是一個占全球貿易份額不斷提升的過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外貿份額不足1%,長期以兩倍甚至三倍于世界貿易的高增速增長。目前,中國外貿份額已經高達12%,是全球120多個經濟體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在這一背景下,世界與中國經貿發展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特征更趨明顯。根據基于時間序列數據的波動匹配度指標,2000年以前中國貿易與世界貿易增長的波動匹配度約在65%左右,2000年之后則加速提升至76.9%,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波動趨勢則幾乎完全一致,世界經貿形勢變動必然在更大程度上波及中國。
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持續低迷,貿易和投資兩大引擎增長乏力。2014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下降8%,直接影響占1/3的最終品貿易及大量中間品貿易,進一步拖累貿易下降。世界貿易增速連續三年低于全球經濟增速,主要經濟體貿易形勢普遍不樂觀。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12-2013年發達經濟體年均出口增速為-0.23%,新興經濟體為0.28%;進口方面,發達經濟體年均增長-1.40%,新興經濟體為1.68%。受上述因素綜合負面影響,作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的中國必然難以獨善其身。
二、從全球價值鏈發展視角看:中國外貿減速是全球價值鏈擴張步入結構調整期的體現
中國的外貿高速增長期,伴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通過擴大開放深度參與全球垂直分工,中國帶動亞太地區成為全球價值鏈快速擴張的重要區域。經合組織(OECD)數據顯示,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從1995年的25.7提升至2009年的46.1,自身也成為貿易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形成了“大進大出”的貿易格局。這一時期,中國加工貿易從1321億美元增至2014年的1.41萬億美元,增長約10倍。一大批具有典型全球垂直分工的機電產品和信息技術產品,保持了長達20年平均30%以上的超常規增速,成為我國第一大類出口商品。
但近年來,拉動上一波世界貿易繁榮的全球價值鏈發展態勢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主要是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出現了局部調整與重塑,部分跨國公司收縮了全球供應鏈及價值鏈的布局。世界銀行研究指出,全球價值鏈在世界范圍內逐步趨于成熟,全球進口中工業品比例開始下降,2012年以來與全球價值鏈相關的貿易增速明顯落后于總體貿易增速。WTO數據也顯示,2012年世界貨物貿易進出口零增長的背景下,排名前十五的經濟體中間品貿易出口、進口同比分別下跌2%、4%。更深層次看,跨國資本流向也在發生變化。受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制造業回流、新興經濟體要素成本上漲等因素影響,新興經濟體吸引外資流入能力普遍下降,特別是制造業吸收外資增速放緩。以我國為例,制造業吸收外資連續3年負增長,導致在華外資企業出口所占份額從2005年時的峰值58.3%降至2014年的45.9%。種種跡象顯示,以大規模跨國投資驅動為特征的上一輪全球價值鏈擴張,目前正處于一個深度“結構調整期”。作為重要節點的中國,未來外貿增長勢必受到全球價值鏈發展速度、方向、路徑等因素影響,短期效應就表現為貨物貿易增速減緩。
三、從國內經濟結構調整視角看:中國外貿減速背后是質量和內涵更趨優化
中國的外貿高速增長期,也是國內經濟結構、要素資源結構、市場主體結構等發生巨變的時期。過去,衡量外貿發展常以規模、速度論英雄,因此當速度降下來時,表面上傳遞的更多是負面信息。事實上,在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的進程中,許多變量之間的關系已經悄然發生變化,理解外貿發展的內涵和質量也需要多維度評價。在近年貿易增速下滑的一些“量”的指標背后,恰恰折射出這種“質”變。
一是加工貿易占比下降,但折射出中間品本土化程度提高,單位出口增加值逐漸擴大。近年我國加工貿易增速持續低于一般貿易,占進出口總額比重已從1998年的峰值53.4%逐步下降至2014年的32.8%。有分析將其歸結為拉低中國貿易增速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實上,這一現象背后恰恰反映出中國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國內配套供應鏈日趨成熟,國內增加值穩步提升。世界銀行研究顯示,中國出口產品中進口零部件的比重由90年代中期超過60%下降到目前的35%,基本與加工貿易占比趨勢吻合。經合組織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出口產品中本土創造增加值占比由2005年的63.6%上升到了2009年的67.4%。
二是貨物貿易增速下降,但服務貿易發展方興未艾,二者聯動發展態勢加強。2008年以來,中國貨物貿易增速下滑,但服務貿易仍然保持兩位數增長,年均增速達12.6%。這一貿易結構變化的經濟帶動作用也在增強。根據全球價值鏈前沿研究,以增加值測算的中國服務出口占總出口比重超過30%,是傳統貿易統計口徑的3倍。與此同時,服務業取代制造業成為我國吸收外資新增長點,2014年占比達到55.4%。這也與全球貿易和投資發展趨勢基本一致。預計未來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互動發展效應將進一步顯現,服務競爭力提升也將促進貨物貿易轉型升級。
三是外資企業貨物出口占比下降,但本土企業競爭力增強,帶動總體貿易結構優化。在華外資企業一度占據我貨物出口半壁江山,其產品門類多數集中于具有典型價值鏈分工特征的制成品領域。大批本土企業通過代工、配套、合資等途徑,參與到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帶來了巨大的競爭效應和學習效應。2001年民營企業進出口占外貿總額比重只有6%,到2014年已經上升至36.5%,對整體進出口增量貢獻55.9%。貿易主體變化帶動產品結構優化,一些國內配套能力強、增加值含量較高的機電類裝備類產品出口提速,汽車、航空航天器、數控機床等份額顯著提升。
四、從外貿大國發展歷程看:中國外貿減速符合歷史客觀規律
2013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每年出口已占到全球貿易份額的近13%。在這樣的體量下,每增加一個點就意味著擴大近2000億美元的出口,相當于2013年非洲出口總額的1/3。縱觀近200年來的世界貿易史,體量巨大與增速放緩正如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幾乎都在貿易份額達到峰值之后經歷了增速減緩。一戰前夕,英國占世界貿易份額很長時間都超過20%,但其增速長期與世界約5%的平均增速齊平,個別年份略高。美國在二戰后問鼎第一貿易大國后,隨即也經歷了5%左右的年均貿易增速,低于當時世界平均水平。德國自1965年開始全球貿易份額穩定在7%~8%之間,但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度出現增速5%左右的“低迷期”,直到2000年之后才重新恢復到兩位數以上。日本同樣經歷了類似過程。綜上,我國貿易增速減緩,也是規模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普遍現象,符合歷史發展規律。
五、理性認識新常態下的中國外貿減速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初步形成以下幾個判斷:第一,近年來中國外貿增速下滑并非短期異常情況。背后既有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短期因素,也有全球價值鏈調整的中期變化因素,更有國內經濟結構變遷等長期因素。第二,未來一個時期中國貿易增速即使短期內可能適度領先,但此前“一枝獨秀”局面或難為繼。聯合國《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指出,中國出口短期內很難回到兩位數增速。如果按照繼續保持1.5倍于世界貿易平均增速計算,2015~2016年中國外貿將處于5%~7%的增長區間,占全球貿易份額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中長期范圍內,不排除隨著全球價值鏈深度調整,世界貿易投資出現新一波增長,帶動中國貿易重回中高增速。第三,應適度跳出中國外貿“高增速情結”,找準外貿發展步入增速換擋期之后的新定位。外貿增速減緩并不意味著其重要性的降低,作為一個經貿大國,對外貿易任何時候都是推動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引擎。應逐步轉變過去以規模和速度作為外貿主要評價指標的政策導向,將“減速”與“提質”、“轉型”結合起來,將提質增效與促進對外投資、產能合作結合起來,將傳統貨物出口與技術、服務等“全產業鏈出口”結合起來。特別是在我國經濟向“雙中高”轉型的今天,要促進傳統貿易功能從擴需求、穩增長轉向促就業、強產業,更好地發揮外貿在勞動技能提高、技術創新和效率提升方面的作用,更好地為我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躍升的新戰略目標服務,推動“大進大出”的傳統發展模式向“優進優出”模式轉化,加快我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