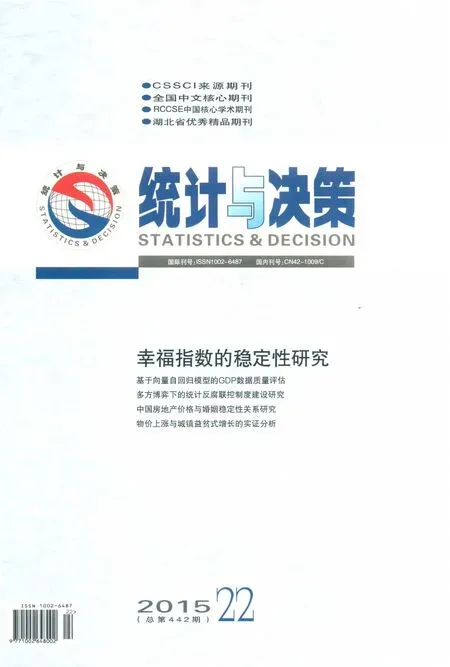基于DEA的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運行效率分析
楊文燮 ,胡漢輝 ,b
(東南大學a.經濟管理學院;b.經濟管理學院,南京 211189)
0 引言
企業孵化器這一概念的出現始于上世紀中葉,在1959年世界上第一個企業孵化器于紐約誕生后逐步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并在聯合國科技發展基金會的推動下于上世紀80年代末期進入中國。科技企業孵化器以為科技型初創企業提供公共服務、降低發展風險為目標,以提供辦公載體、財稅服務、政策對接、法律咨詢、人才引進、融資信息為主要任務,是培育創新型企業、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的重要平臺和載體。
上海、南京、杭州三市地處長三角地區的核心區,是我國科技企業孵化器分布最為密集、發展較為突出的城市,截至2013年底,滬寧杭三地共有45個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孵化基金總額超過37億元。由于經濟社會與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滬寧杭三地相對于國內其他地區而言,在科技企業孵化器的發展過程中擁有更豐富的資源以及更優質的人才,因而這三座城市的科技企業孵化器發展具有很強的前沿性與示范性。基于以上考量,課題組通過近年來詳實的數據對滬寧杭三地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的運行現狀進行分析與研究。
1 數據包絡分析模型
從方法角度出發,數據包絡分析法是一種系統分析方法,從數學角度出發,數據包絡分析法實質上是一種線性規劃的數學過程,其研究的是相對效率而非絕對效率。目前,該方法廣泛應用于管理科學與系統工程領域,適用于對多輸入多輸出對象系統的評價,其特點在于不需要事先確定評價體系中各項指標的權重及前沿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且不需要對各個指標進行統一的量綱處理。科技企業孵化器運行的投入產出中包含了多種資源的轉化,是典型的多輸入多輸出且指標量綱不統一的對象,運用數據包括分析法可以很好地研究多個科技企業孵化器運行的相對效率。
數據包絡分析中,將一個從投入到產出的生產過程看作一個決策單元(DMU),如在對科技企業孵化器績效進行數據包絡分析時,將一個有m種投入和n種產出的科技企業孵化器都看作一個DMU,其輸入用 x=(x1,x2,···,xm)T表示,輸出用 y=(y1,y2,···,yn)T表示。假設有s個 DMUj(1≤j≤s),輸入權重向量為 α=(α1,α2,···,αm)T,輸出權重向量為 β=(β1,β2,···,βn)T,當所有DMU的規模報酬不變時,對DMU進行技術效率評價可構造CCR模型,如式(1)所示:
在CCR模型中,當式(3)最優解 ω0、μ0均大于0,且μTy0=1,說明該DMU的綜合效率(或稱為技術效率)為1,即該決策單元為DEA有效;當μTy0<1時,則認為該決策單元非DEA有效。
當考慮規模報酬可變時,則可建立BCC模型計算決策單元的純技術效率,BCC線性規劃模型(Input-BCC模型)如式(4)所示。

在BCC模型中,當式(4)最優解滿足 μTy0-μ0=1,即純技術效率為1,則該決策單元純技術效率有效。將CCR模型中的綜合效率與BCC模型中的純技術效率之比定義為決策單元的規模效率,該值用來表示被評價的決策單元的規模報酬所處的狀態(遞增、遞減或不變)。
2 研究對象
本文以上海、南京、杭州三地45個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為研究對象,將統計數據不完整的孵化器排除,最終的研究對象共有41個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其中上海地區有21個,南京地區有6個,杭州地區有14個,具體如表1所示。
3 指標體系構建
選擇和構建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是研究科技企業孵化器運行效率的關鍵。本文在選取評價指標體系時遵循科學性、可行性、通用性等原則,圍繞科技企業孵化器的內涵,充分考慮數據的可采集性及可比較性。為保證研究的真實性與準確性,本文所有數據均來源于科技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編撰的2013年《中國火炬統計年鑒》,是目前最新的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統計數據。在該統計數據中,對于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的統計共包含基本情況、企業情況、人員情況、場地情況、在孵企業情況、畢業企業情況等6部分27個指標,排除“創業導師人數”、“留學回國人員”、“其他用房面積”、“承擔國家級科技計劃項目數”等8個統計數據不完整、缺乏通用可比性的統計指標,以及7個與已有統計指標顯著正相關的統計指標,最終剩余12個有效統計指標。參考張嬌(2010)對科技企業孵化器運行效率評價指標的分類,將投入指標分為人力、物力和財力3部分;從科技企業孵化器的內涵出發,將產出指標分為孵化能力、創新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具體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

表1 研究對象及其組織代號

表2 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在應用數據包絡分析法時,還需滿足以下兩點基本要求:(1)決策單元數量至少在投入、產出指標總數的兩倍以上;(2)投入指標集與產出指標集內部均要避免有較強相關性的指標同時存在。本文的研究對象是41家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即決策單元數量為41,遠超過投入、產出指標總數的兩倍。本文借助IBM SPSS Statistics 19軟件對41個決策單元的3個投入指標、4個產出指標這7組數據進行兩兩相關性檢驗,各指標間相關性檢驗t統計量顯著性概率如表3所示,當t統計量顯著性概率小于0.01時,認為兩組數據顯著正相關。從表3中數據可以看出,投入指標集與產出指標集內部均不存在有較強相關性的兩個指標,僅指標X1與Y4、X3與Y1具有顯著相關性。因此本文認為,研究中所采用的指標體系符合數據包絡分析法指標選取的一般原則。

表3 各指標間相關性檢驗t統計量顯著性概率
4 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效率及差異
本文采用投入導向型數據包絡分析模型,根據上文確定的決策單元及指標體系,計算出滬寧杭三地41個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的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以及規模效率,具體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滬寧杭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效率分析結果
為進一步了解滬寧杭三地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在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的差異,本文利用單因素方差法對表4中的研究結果進行了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結果顯示,杭州地區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的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三項指標的均值均位列三地之首,但滬寧杭三地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的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F分布的顯著性概率(Sig.)分別為0.378、0.302、0.696,均大于系統默認的顯著性概率0.05,因此可以認為滬寧杭三地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的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均沒有顯著性差異。

表5 滬寧杭三地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差異分析
4.2 總體情況分析
在數據包絡分析中,當綜合效率得分為1時,才能稱該決策單元運行效率相對有效,根據數據包絡分析原理,綜合效率為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的乘積,因此當純技術效率非有效或規模效率非有效發生時,決策單元運行效率相對非有效。從表4數據可以看出,I6、I8、I10、I13、I15、I18、I21、I23、I25、I26、I28、I29、I31、I32、I33、I38、I39等17家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三項均為1,說明這17個孵化器在2013年運行過程中以較小的投入獲得了較大的產出,運行效率相對有效,其余24個孵化器運行效率相對非有效。就各城市而言:上海21個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中,7個相對有效,14個相對非有效,相對有效率為33.3%;南京6個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中,3個相對有效,3個相對非有效,相對有效率為50%;杭州14個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中,7個相對有效,7個相對非有效,相對有效率為50%;總體上,滬寧杭三地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運行效率相對有效率達到41.5%。滬寧杭三地41個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的綜合效率均值高達0.797,僅有2個綜合效率低于0.4,分別位于上海和南京;32個綜合效率在0.6以上,占總體比例達到78.0%,其中上海地區綜合效率在0.6以上的孵化器有15個,比例為71.4%,南京地區綜合效率在0.6以上的孵化器有5個,比例為83.3%,杭州地區綜合效率在0.6以上的孵化器有13個,比例為92.9%。此外,在24個運行效率相對非有效的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中,有19個處于規模報酬遞增狀態,占運行效率相對非有效的比例達79.2%,僅有5個孵化器處于規模報酬遞減狀態。
總體來看,滬寧杭三地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整體發展較為均衡,綜合效率低于0.4的僅有兩個,三地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的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差異均不顯著;從局部來看,南京與杭州的相對有效率均達到50%,上海的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最多,但其相對有效率僅為33.3%,且綜合效率平均值在滬寧杭中處于最低位,整體運行效率遜于杭州與南京
4.3 運行效率相對非有效的情況分析
本文根據數據包絡分析原理,除了計算出各決策單元的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還計算出各運行效率相對非有效的決策單元達到相對有效所需減少的投入或增加的產出。表6為本研究中24個運行效率相對非有效的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投入冗余及產出不足情況。
(1)投入冗余問題
從表6數據中可以看出,出I30與I40兩個孵化器外,其他所有運行效率相對非有效的孵化器均在財力、人力、物力三個投入指標上出現了冗余的現象,其中孵化基金總額的冗余均值為15193.2457千元,管理機構從業人員數的冗余均值超過8人,孵化器總面積冗余均值達到7875.5242平方米。
從投入情況來看,滬寧杭三地相對非有效的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運行效率較低的原因在于沒有充分利用資源,說明在滬寧杭三地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的發展過程中,決策者更注重資源的投入,缺乏對孵化器發展的理性認識與科學規劃。

表6 相對非有效的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投入冗余及產出不足情況
(2)產出不足問題
從表6數據可以看出,29.2%的相對非有效的孵化器在孵企業人數不足,距離理想人數的平均差距約為143人,社會效益尚需提高;66.7%的相對非有效的孵化器批準知識產權數量欠缺,距離理想值的平均差距約為32個,創新能力亟待加強;29.2%的相對非有效的孵化器當年畢業企業數量稍顯偏低,距離理想值的平均差距約為1個,孵化能力仍然有上升的空間;54.2%的相對非有效的孵化器平均畢業時收入不足,距離理想值的平均差距約為213.6萬元。
從產出情況來看,滬寧杭三地相對非有效的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中66.7%獲批準知識產權數量不足,說明滬寧杭三地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整體創新能力不足,也反映出薄弱的技術創新能力逐漸成為制約科技企業孵化器發展的障礙;此外,滬寧杭三地54.2%的相對非有效的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畢業企業平均收入較低,說明畢業企業的整體實力離理想狀態尚有差距,孵化質量亟須提高。
(3)規模不匹配問題
從表6的數據中可以看出,組織代號為I30和I40的兩個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其財力、人力、物力的投入冗余量均為0,且社會效益、創新效益、孵化能力、經濟效益的產出不足也均為0,但這兩個孵化器仍然處于相對非有效狀態。究其原因,決策單元相對非有效是由于其規模和投入、產出不相匹配,根據數據包絡模型原理,I30與I40兩個孵化器的純技術效率為1,純技術效率有效,但由于其規模效率小于1,因此綜合效率小于1,運行效率相對非有效。因此,對于I30與I40而言,它們的技術水平已經發揮到最佳狀態,只有通過調整其規模、解決規模非有效性問題,才能向最優狀態發展。根據數據包絡分析結果,I30處于規模報酬遞減狀態(drs),繼續擴大規模已經不能帶來有效比例的產出,應當考慮控制規模,使規模與投入產出相匹配;而I40處于規模報酬遞增狀態(irs),應當通過進一步擴大孵化器規模,實現最優匹配模式,進而達到相對有效。而從表4中可以看出,除去I30和I40,其他DEA相對非有效的孵化器的規模報酬也均處于遞增或遞減狀態。
從規模調整情況來看,滬寧杭三地相對非有效的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中,79.2%處于規模報酬遞增狀態,說明盡管滬寧杭三地的科技企業孵化器發展水平位居全國前列,但其整體尚處于發展初級階段,多數孵化器需要進一步擴大規模,以提高孵化器規模與投入產出的契合度。
[1]Premachandra I M,Zhu J,Watson J,et al.Best-Performing US Mutual Fund Families From 1993-2008:Evidence From A Novel Two-Stage DEA Model For Efficiency Decomposition[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12,36(12).
[2]Charnes A,Cooper W W,Rhodes E.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78,2(6).
[3]Banker R D,Charnes A,Cooper W W.Some Models for Estimating Technical and Scale Inefficiencie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Management Science,1984,30(9).
[4]Chan K F,Lau T.Assessing Technology Incubator Programs in The Science Park:The Good,The Bad and The Ugly[J].Technovation,2005,25(10).
[5]Rice M P.Co-Production Of Business Assistance In Business Incubators:An Exploratory Study[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2,17(2).
[6]李振華,張煜.基于DEA的我國京津冀地區科技企業孵化器績效評價[J].標準科學ISTIC,2013(2).
[7]張嬌,殷群.我國企業孵化器運行效率差異研究——基于DEA及聚類分析方法[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