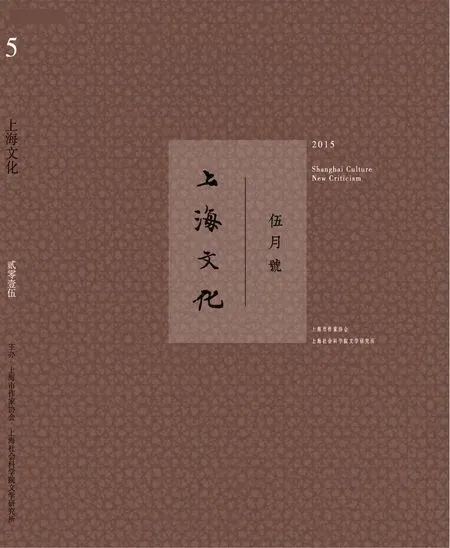在一個世界里感受,在另一個世界里命名
來穎燕
在一個世界里感受,在另一個世界里命名
來穎燕
維多利亞時代,王爾德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象征
給文學作品配插畫,如同讓兩個彼此熟悉又界限分明的陣營短兵相接。世人對這場博弈大多懷有“成見”——文學作品是獨大的主角,“配圖”的重心在“配”字上,其風格特點該忠于文學作品。多數情況確也如此。但細想這“大多數”中鮮有出挑到讓人凜然的例子,卻反而是王爾德的《莎樂美》與比亞茲萊的配圖——這個與“大多數”相悖的個案,散發出歷久彌新的光芒。
王爾德與比亞茲萊的這次合作可以稱為一次“事件”,有著跌宕起伏的情節,更具有象征意味。
維多利亞時代,王爾德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象征。他的一生飽受爭議,人們既愛他需要他又唾棄他。頹廢主義和唯美主義在他的身上深刻而自然地交融著。他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并且用一輩子的時間實踐這一主張——再沒有如王爾德的一生更能體現頹廢和唯美雙重意蘊的個案了,他真實的人生具備著超越小說的戲劇性。
就像以往的許多天才一樣,比亞茲萊的生命軌跡成為了一條“拋物線”,為《莎樂美》創作插畫成為了他人生的轉折點
在王爾德的心里,極致的美和純凈之中可以開出妖邪的小花。盡管其時對于美的定義盛行著中產階級狹隘的市儈標準,但這小花卻深深扎根在人心深處,并且招搖出最本真和赤裸的人性,他希望借此脫離現實生活的齷齪險境。于是他選擇“莎樂美”的形象來創作自己的第一部戲劇,并將莎樂美從一個聽命于母親的殺人工具析出了原作,化為一個因為愛不得而砍下愛人頭顱的美艷、性感、充滿誘惑卻殘忍至極的妖女。他妥貼并且肆意地將自己附著在莎樂美的身上——莎樂美對于愛人約翰之美的沉溺,對于約翰那無畏到變態的愛,以及對感官刺激的追求和自身欲望的放縱,是王爾德內心乃至現實人生的同構,如他在詩中寫到的,自己是“誘惑的嘴唇和被誘惑的生活”。然而,如此強烈的美和愛燃盡的那一剎那,即使死亡也難以銷蝕掉幻滅和頹廢。莎樂美的死仿佛是王爾德人生的讖語。
1893年,《莎樂美》的法文版出版后,年輕的比亞茲萊深為震動。王爾德的《莎樂美》仿佛暗合了他內心的密碼,他預感到這個劇本是顯露自己的藝術天分和生命體悟的獨特舞臺。他幾乎是不可遏制地很快就為其高潮部分創作了那幅著名的“約翰,我吻了你,我吻了你的唇”的插畫。王爾德得見之后,只覺驚鴻一瞥,大為激賞。比亞茲萊于是受邀成為了后來《莎樂美》英文版的插畫作者,系統創作了十余幅插畫。然而這一次,王爾德對比亞茲萊的工作表示了不滿,兩人的關系也急轉直下——比亞茲萊的繪畫事業和人生就此走向低谷。他因為風格獨特的《莎樂美》插畫而聲名大噪,也因為這“獨特”不為世人特別是“雇主”王爾德所接受,而落入深淵。就像以往的許多天才一樣,比亞茲萊的生命軌跡成為了一條“拋物線”,為《莎樂美》創作插畫成為了他人生的轉折點。
王爾德的不滿是有根據的。
首當其沖,王爾德認為自己的作品中充滿著鮮明的色彩感,而比亞茲萊只選擇黑白色調,二者間顯然是一種違逆。然而黑白之調并非如其表面那樣只能表達黑白兩色。中國素來有“墨分五色”之說。在比亞茲萊的處理中,簡易的色調在強調的對比之下引人遐思,反而泛出意想不到的“色彩感”。
看《莎樂美》劇本中的這段描述:
希律:“哦!你準備著赤著腳跳舞。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你的小腳兒一定會像白鴿一樣。它們一定會像在樹枝上舞蹈著的小白花兒一樣。……不,不,她準備在血上跳舞了。你看鮮血濺了這一滿地。”
比亞茲萊為這一幕配圖《肚皮舞》。畫面的下半部分以全黑色做底,莎樂美的雙腳在上面顯得異樣的雪白,以致讓人感覺到四周的黑色散發出血腥的氣息。同樣讓人遐想的還有莎樂美的唇色——那蒼白面容上的唇該充滿著怎樣烈焰般的誘惑!比亞茲萊對于莎樂美的頭飾以及鞋子上的花紋等處的細節描繪,因為用了白描手法,讓畫面色調在黑白的強烈對比之外有了一種妥協的過渡。但畫面整體自簡單中泛出的豐富,讓這個場景在妖媚中滋生出恐怖的意味。
比起直接的賦彩,在看似單調的畫面中感受色彩的過程總是更為真切而令人著迷。“珍珠白”、“血紅”或是“炭黑”,這些色彩因為有著實物的圖示為前綴才能得體到“帶感”,因為說到底,色彩的千差萬別無法窮盡,所以根底上是無法言喻的。而極繁和極簡間常有著怪異的張力,如果畫面只用黑白兩色,表面上是遮蔽了這色彩間的細微差異,實則卻是將對差異的拿捏和感受的色卡交到了觀眾的手里。比亞茲萊深諳其中之道,他的黑白二色,引誘觀者催動自身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于是,在色彩上的節制,雖然表面上違逆了王爾德的預想,卻在另一種層面激發了《莎樂美》戲劇場景的色彩感,提醒我們發現“無法言喻”之處。
比亞茲萊的畫筆將我們引向文字背后的暗角,在那里,看似與文字表面相悖的內核散發著魅惑的光。
“我們在一個世界里感受,在另一個世界里命名”(普魯斯特語)。黑與白,繪畫與文學都是涇渭分明的不同世界,卻可以互相激發、成為彼此“無法言喻”處的寄托。
比亞茲萊與王爾德何嘗不是這樣兩個相生相悖的世界。
1895年,王爾德因為同性戀的罪名入獄,比亞茲萊深受牽累。盡管此前已經不再與王爾德交好,但此刻人們似乎一下子意識到這位不受王爾德認可的插畫者的插畫,與王爾德的文學作品一樣“傷風敗俗”。
“傷風敗俗”的潛臺詞是“變態”。色情,恐怖,怪異、淫蕩……王爾德與比亞茲萊的藝術和人生似乎都浸淫在這些為“正常人”不齒的詞中。但“變態”其實只是“非常態”,從“非常態”的視角出發,往往會濾掉世間的虛偽和庸常,觸動人性深層那些驚世駭俗卻真實到底的角落。細究比亞茲萊“變態”的根由,或在于他的“病態”。這位短命的天才終生被病魔折磨,七歲時就染上了肺病,不斷咳血,最終在世間只待了二十六個年頭。但時刻憂心時日不多的心境讓比亞茲萊的生命與藝術獲得了無人企及的交融。現實中的病態深深沁入比亞茲萊的畫風——纖細,孱弱,卻有著銷魂蝕骨的妖嬈和美麗,他成為了他病態處境的化身。
而對于王爾德而言,“病態”一詞充滿悖論:“如果不是一種人們無法言說的情感和思想,那么病態是什么?大眾都是病態的,因為大眾不會表達東西。藝術家從不病態。他表達一切。他身居他的主題之外,通過主題創作出無與倫比的藝術效果”。從這個角度而言,比亞茲萊雖然身體“病態”,精神上卻擁有著可貴的“健康”——他以一種純凈大膽、無所顧忌的方式來表達自己閱讀《莎樂美》時“無法言說”的感受。“畸于人,而侔于天”(《莊子·德充符》),“病態”于此是一種赤裸裸的真摯。盡管最后連王爾德也忍受不了這樣“無所顧忌”的真摯,但看來“不合”的二人實則有著最深層的共鳴。
大眾都是病態的,因為大眾不會表達東西。藝術家從不病態。他表達一切
讓人感慨的是,最初正是這“病態”促使比亞茲萊走入了黑白畫的世界——死亡陰影的無處不在,讓比亞茲萊時刻感到一種逼仄和壓迫,他必須尋找一種能盡情并可取的方式來釋放自己的藝術天分,繪制過程繁復的畫種如油畫等顯然不是好的選擇。并且,黑白畫的特點正可隱匿起比亞茲萊在繪畫基礎和學院素養上的欠缺,要知道,在他二十歲為《亞瑟王之死》配圖之前,還只是一名銀行職員,繪畫不過是業余愛好。但正如晚年的馬蒂斯選擇剪紙而放棄其他畫種的創作的最初緣由是體力不支,但最終的事實證明,剪紙藝術的特質因為與馬蒂斯對于造型和色彩的理解相契,而成就了他新的事業高峰。同樣,比亞茲萊并非只是出于現實考慮而被動地選擇了黑白畫。
但王爾德的內心并非如他給人的感覺那樣斑斕,而是更接近“純色”
德沃夏克曾提出要理解一個時期的藝術,就要了解這個時期的精神史(參見《作為精神史的美術史》)。比亞茲萊所處的19世紀末的西方,交織著美和丑、進取和頹喪、禁欲和放縱的“世紀病”的氣息四處彌漫,光鮮的外表下根脈卻已羸弱。內心越淫蕩狂野表面卻越正經貞潔,從“缺席的”發現“在場的”,這種大環境的病態,造成了其時文學藝術上不堪一擊的“繁華”。比亞茲萊,這個沒有任何流派和淵源的初生之犢,以一己之身,觸摸到了這種特質,并且“任性”地用屬己的“黑白畫”的方式表達出來。
比亞茲萊的內心其實對于色彩極為敏感。在去世前的一個月,他還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到貝諾佐·戈佐利的畫,稱其為“最輝煌、最吸引人的畫”。這位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的作品,正是以絢爛的色彩見長。但對于比亞茲萊而言,唯有“黑白畫”能表現自己內心對于多彩世界的理解,就如同修拉用點彩的畫法、透納通過光的折射來描繪世界一樣。在表現詭異和怪誕的主題上,“黑白畫”有著天然的優勢,而細膩、纖弱而敏感的比亞茲萊更是深深地觸摸到“黑白”背后的曖昧和怪誕,賦予了其層次豐富的“病態”:黑白深處仿佛有空間無限,包裹著無數的秘聞。他的黑白畫面不僅不單調,反而有種華麗感。在色彩的世界里感受,在黑白的世界里表達,卻生成了耀人眼目的效果。“黑白畫”于比亞茲萊,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貼合了他的生命特質,繼而成為他拿捏時代精神的獨門武器。
絢爛色彩的內核,卻可能是另一種安靜和單純。比亞茲萊可以黑白繪絢爛,而王爾德則證明了反之亦然。他的許多作品,都給人以色彩濃烈之感,尤其是他的童話作品——《快樂王子》中王子塑像上那閃耀著的藍寶石眼睛和滿身的純金葉子,《夜鶯與薔薇》中那朵被夜鶯之血染紅的薔薇,一擊必中地在人心間留下印痕。但王爾德的內心并非如他給人的感覺那樣斑斕,而是更接近“純色”。
他筆下的人物大多有著極端的性格——《道林格雷》中的主人公為了美而放縱欲望,至死不改;即使轉變也會走向另一端——《自私的巨人》中的巨人一旦醒悟自己因為自私而致使春天不再降臨自己的花園,便從此慷慨仁慈。王爾德還常會將兩個反差強烈的形象并置,由此產生的鮮明對比更顯出他性格中非此即彼的特質——《快樂王子》中,王子塑像一開始光彩奪目,王子也快樂無憂,在目睹世間悲苦并施舍完身上的寶物后,塑像黯然無光,而王子也從此愁眉緊鎖。種種極端和對比,幾乎沒有中間地帶。對美極致追求,極致到對惡有著幽靈般的崇拜,令王爾德畢生都帶有“放浪”和“后退”的情緒,他的“作品稱贊這兩種情緒,平衡它們,或玩樂它們”。他表現出來的“罪惡”和“妖邪”,根源于對人性之善的渴望——其時其境,世人稱道的“善”多是“偽善”,而譴責的“惡”卻可能是赤裸裸的本真,他要揭下這溫情脈脈的教條的面紗。所以,在他從光鮮得志的風云人物,轉而成為階下囚、受盡凌辱時,在法庭上依然慷慨無畏。世人眼中的“丑聞”,在王爾德是人之本能的顯現,是對于維多利亞社會的挑戰——之前他用文字,此刻他用行動。即使在人生的最低谷,王爾德依然自我,用他的話來說:“真正的人格是由罪惡造成的。”
這樣的極端,是王爾德生命的底色,所以即使他的外在看起來多變妖冶,他的作品看起來斑斕五彩,但這種極端正是因為他的天真,他那“無所謂道德不道德”的主張,實則是出于對于人性無條件的理解和尊崇,用博爾赫斯的話來說:“王爾德盡管有惡習和不幸,卻保持著一種不可摧毀的天真。”
比亞茲萊與王爾德在對于世事的“任性”上如出一轍。十九歲時,他面見英國著名藝術家莫里斯,因為不被看好而傷心撕碎自己的畫作。就在同一年,另一位著名藝術家布里恩瓊斯卻對比亞茲萊的作品表示了高度的贊賞,他立即深受鼓舞,去往威斯敏斯特美術學校學習繪畫。他的心思如此透明,當他遇到自己仰慕的惠斯勒卻遭受冷遇后,居然一氣之下畫了畫來諷刺惠斯勒的妻子。他甚至將王爾德的形象置入了他的《莎樂美》插畫中……命途不同的二人,同樣放肆地演繹著“人生如戲”的真諦,盡管一個看起來五彩斑斕,一個看起來單調純凈。在這個意義上,比亞茲萊的黑白畫不是從視覺的直觀感受上,而是在精神內核上更切近了王爾德的本質氣息。
王爾德對于比亞茲萊插畫不滿的另一條重要理由是認為其太偏于“東方主義”。但事實上,盡管王爾德對于《莎樂美》的風格有著“拜占庭”式的預設,但他并不排斥東方風格。相反,他對于裝飾性藝術的推崇是出了名的。在《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中,他說道:“裝飾性藝術審慎地拒絕了視自然為美的理想,還拒絕了普通畫家的模仿手法,通過這種拒絕,裝飾性藝術不僅讓心靈做好了接受真正虛構作品的準備,還在心靈中培養了一種形式感,而這種形式感正是創造性成就的基石。”
藝術形式的本身具有著“言說”的本能,所以王爾德迷戀藝術在主題之外的美感。裝飾性的風格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擺脫思想的存在,卻能更直接地觸動人們的感觀。由此被激發的情感,說不清,道不明,卻是一種“本質性”的境地。
而比亞茲萊對于畫面裝飾性和扁平化的追求,正是以一種近乎鬼魅的狀態拿捏住了王爾德心中那種因為愛而走向極端甚至邪惡的感覺。
用博爾赫斯的話來說:“王爾德盡管有惡習和不幸,卻保持著一種不可摧毀的天真。”
比亞茲萊所繪的《莎樂美》中,有諸多裸體或半裸的形象,并曾有小畫被禁。他因此被認為強化了王爾德的《莎樂美》“有傷風化”的特征,在王爾德入獄之后成為眾矢之的。但比亞茲萊的插畫所產生的效果并不僅僅停留在直接的感官刺激上。因為他的裝飾性風格有別于“現實主義”,使得人們能適時地從逼真的感官刺激中抽離出來,轉而關注畫面在主題之外帶來的直觀感受。人們吵吵嚷嚷,仿佛被扯去了體面的衣服而怒不可遏,但最后發現比亞茲萊的插畫雖然充滿了“性”的主題,但沉淀下來的不是粗俗和下流,而是一種凈化后的神秘感。這種層次豐富的神秘感正是王爾德的《莎樂美》的深層底色:黑白與愛恨之間,有著某種共震,走向極致并不意味性質發生了背反,而是同一層面的兩個極端。黑白之間再無其他色調的插入,白的極致就是黑,而恨也不是愛的反面,而是因為太深刻的愛而走向了另一極端。到了王爾德筆下,恨更帶有著摧毀一切的激烈的表達方式。比亞茲萊對此所選擇的轉譯方式,顯然更為抽象,而在王爾德看來:“在抽象的理念藝術中,時代的精神可以得到最完善的表達”,這也是為何拉斐爾前派和裝飾性藝術運動會共時發生,并且直接影響到以王爾德為首的19世紀后期的唯美主義。
比亞茲萊插畫的裝飾性風格的構成中,線條也是不可或缺的重點。他那流暢靈活的線條,顯示出古希臘的瓶畫和“洛可可”時代所具有的變化而纖弱的風格。而這“纖弱”無處不在地隱匿在王爾德那放肆而偏執的欲念背后。更重要的是,比亞茲萊的線條有的詳盡細膩,有的則簡練概括。這種在細節和整體間自由游走的態勢,正契合了王爾德的《莎樂美》的神秘傾向與自然主義并重的格調。
這導致了我們慣常理解中的文學與繪畫間的關系發生了逆轉——通常,作為視覺藝術的繪畫往往被認為會將文學作品中抽象的形象具體化,其代價是限定了讀者的想象空間。王爾德也曾表示對于插畫的輕視,“因為它們沒有激起想象,卻為想象劃定了明確的界限”。但比亞茲萊的“游走”無視這些“界限”。他可以對畫中人的發絲或是發飾細致描摹,白描的手法宛如劇中人就在眼前,卻又可以在同一畫幅中大塊面地省略細節。這種對比之下產生的既具體又虛幻的效果,不僅沒有局限文字本身的空間,反而更誘發讀者們富有個性的“想象”——王爾德曾經將比亞茲萊的畫比喻成苦艾酒,散發出奇怪的罪惡的誘惑力,能誘惑出人的潛意識自我。比亞茲萊在插畫內容上同樣實現了這種在自然主義和神秘主義間的游走。他用寫實的白描來刻畫劇中人,甚至以此來塑造并不曾在王爾德的劇本中出現的魔鬼或是小丑形象。這些一看便知是虛構出來的人物,卻有著現實的細節,不再是抽象的符號。它們帶著自然的體溫,因而愈發可怖。正因此,比亞茲萊的《莎樂美》插畫,就如丟勒的《啟示錄》插畫那樣,“不但沒有弱化原作的想象力,反而強化了它”。而比亞茲萊不僅“強化”讀者的想象,同時也“強化”自己在創作插畫時所持有的主觀性。這可說明,為何比亞茲萊的插畫中會出現一些與原作無關的場景——他解讀的《莎樂美》“將記憶中有關遠古的地球和月亮女神與左右于宇宙和大地、淫猥和褻圣之間的世紀末女性命運的漫畫化聯系起來”。
“任何強烈情感的欲望,都應由其相反的情感來發泄。”無法窮盡和企及的境地,唯有以“有限”和“節制”來表現。所以,太過濃烈豐富的色彩,或許只能歸為至簡的黑白,就像從現實切入無邊無際的想象世界,才會尋找到支點而愈加寬廣。
這是文學與繪畫對彼此互不妥協的延展,也是王爾德和比亞茲萊關系的隱喻。
王爾德豐富而敏感的靈魂對于文字與繪畫之間的勾連深有感觸。在《筆桿子、畫筆和毒藥》一文中,他頗為認同英國歷史上著名的集作家、畫家和罪犯于一身的傳奇人物溫賴特的觀點:“如果一個不喜歡米開朗基羅的人談及他對彌爾頓的熱愛,他不是在欺騙自己就是在欺騙聽眾。”事實上,王爾德也坦言,自己會將莎樂美的形象和整部劇本染上華麗神秘又罪惡的氣息,是受到了19世紀法國浪漫主義畫家莫羅所作的莎樂美系列繪畫的影響。但比亞茲萊的插畫顯然將文字與繪畫之間的關系推向一種互相激發而非互為闡釋的極致。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后,中國詩人馮至因為看了比亞茲萊的畫《夢》,而創作了詩歌《蛇》。文字與繪畫間的糾纏和循環如此千回百轉。
約翰·伯恩賽德在《亡命之舞》(The Asylum Dance,2000)第四章《曠野》(Fields)的“其他生命”一部分中指出:“你打開燈時,要快/你將看到黑夜的存在/正如我父親所說/抓住/事物的其他生命/一瞥之前/深陷其中”(參見安德魯·本尼特:《文學的無知》)。
閱讀文本,就如開燈時。那一刻,“可以‘看到黑夜的存在’,因此你也可以看到或看不到任何事物。并且,更為重要的是,看不到的事物與看到的事物一樣重要”。閱讀,注定有著太多似是而非的“無法言喻”之處。對于王爾德的這部《莎樂美》,乃至他的小說、童話、散文,文字上的閱讀似乎都會導致一種殘余,用德曼的話來說:這是因為任何閱讀都不能“斷言達及了一個文本的決定性的比喻維度”。比亞茲萊的畫,在一個全新的世界里讓我們體會到了這個難點。在王爾德最初送給他的《莎樂美》簽名本扉頁上寫著:“獻給奧布里:獻給除我之外唯一一位懂得七層面紗舞是什么并能看見那常人無法看見的舞蹈的藝術家。”二人惺惺相惜,只是后來王爾德發現比亞茲萊過于獨立——他一意孤行地用自己的方式引誘了本屬于王爾德的莎樂美。兩人關系的矛盾和變數,標識出他們在靈魂深處的對接,同樣的脆弱敏感,同樣的驕傲自戀,同樣的追求完美。
正是因為骨子里的相近,王爾德注定無法忍受比亞茲萊的光芒超越自己。既然,比亞茲萊不愿為自己的劇本所束縛,那么王爾德擔心自己的作品反過來成為比亞茲萊插畫的注解而大發雷霆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在一個世界里感受,在另一個世界里命名,他們誰也沒有成為誰的附屬
在比亞茲萊死后約半個世紀,意大利藝術家瓦倫蒂安吉洛采用波斯風格,為王爾德的《莎樂美》再配插畫。畫面華麗精美,連裝幀都極為考究。雖然王爾德自己無法得見,但這一次的配圖被認為更符合王爾德作品的氣質。然而,這“貼切”的配圖卻只表明畫者要沉入王爾德世界中去的決心。但刻意地在同一世界中表達,又能抵達多少“無法言喻”處呢?無怪比亞茲萊的作品在王爾德的《莎樂美》上留下的指紋,更令人刻骨銘心——在一個世界里感受,在另一個世界里命名,他們誰也沒有成為誰的附屬。
“有時人們說藝術家生命中的悲劇在于他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但是發生在大多數藝術家身上的真正悲劇,是他們過于徹底地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因為一旦理想被實現,它也就被剝奪了奇跡和神秘感,于是就變成了它自身之外的另一理想的新出發點。”王爾德和比亞茲萊正是兩個相似卻不相交的倔強的悲劇,讓人想起歌德的話:“希望從他們頭上劃過,就像星星從天空墜落。”
???理查·艾爾曼《引言:王爾德,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王爾德全集——評論隨筆卷》,中國文學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9頁;第8頁;第10頁。
?奧斯卡·王爾德《莎樂美》,田漢譯,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57頁。
?博爾赫斯《關于奧斯卡·王爾德》,《探討別集》,浙江文藝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95頁。
?奧斯卡·王爾德《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之二)》,《謊言的衰落——王爾德藝術批評文選》,2004年3月版,第172頁。
?奧斯卡·王爾德《謊言的衰落》,《謊言的衰落——王爾德藝術批評文選》,2004年3月版,第41頁。
?參見正子《比亞茲萊的黑白傳奇》,《比亞茲萊:最后的通信》,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編輯/張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