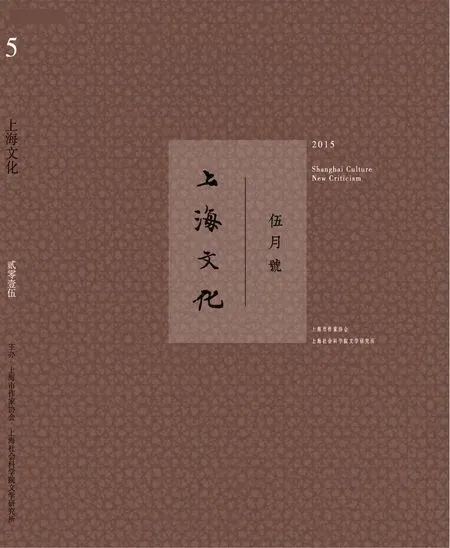在“輕”的時代里,對“重”的重估*蒂皮特《我們時代的孩子》及其演繹版本
杰蘭特·劉易斯 詹湛 譯
在“輕”的時代里,對“重”的重估蒂皮特《我們時代的孩子》及其演繹版本
杰蘭特·劉易斯 詹湛 譯
一
大約在七十五年之前,也就是1939年9月4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升起了硝煙。英國作曲家邁克爾·蒂皮特(M.Tippett,1905-1998)坐在他那架大號的鋼琴面前,沉思良久。這架超大的鋼琴讓他在薩里郡,奧克斯戴德那間小屋里的所有其他東西都相形見拙。他準備在鋼琴邊譜寫一首規模宏大的作品,寫給獨唱人聲、合唱團與管弦樂隊。因為工程異乎尋常地宏大,這一進程持續了近兩年。在大功告成之后,蒂皮特將總譜塞進了最下層的抽屜里,轉而開始譜寫室內樂,如第二弦樂四重奏。
這就是《我們時代的孩子》這部清唱劇的誕生經歷。沒有邀約、沒有出版商、沒有報酬,也沒有任何預計的演出。當然,也沒有找來合適的腳本作者——不過這也開啟了另外一段新故事。
盡管出生于1905年的倫敦,蒂皮特卻是在一座16世紀的鄉村農莊里長大的。這座農莊位于薩福克郡國境線附近,較為僻靜的村落深處,與斯托馬基特(Stowmarket)相距不遠。蒂皮特的家庭的確出過不少優秀的知識分子,不過在音樂領域似乎還沒有特別優秀的人才。兩位蒂皮特的哥哥從小開始上鋼琴課,而母親也時不時地在家里歌唱。但是,到了九歲的時候,那個最小的孩子,米夏埃爾·蒂皮特竟然立志要當一位作曲家了。事實上,就他自傳里的回憶,正是戰爭的歷史環境促使他早早地成熟,立下了一般孩子所不能及的宏志。1914年8月,參加一戰的士兵們在行軍路上所唱出的軍歌“這是到蒂珀雷里的長長道路”(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似乎飽含著歡快的情緒。那是一股模模糊糊,但頗為強大的推動力:小蒂皮特深受感動,默默記下了旋律,還跟著哼唱。據說,這段記憶竟然一直保持到了蒂皮特半個多世紀后的臨終前。
然而,關于戰爭的記憶很快就被陸續而來的陰霾所籠罩,蒂皮特與同時代其他許多天真無邪的少年一樣,在1923年都被一個個殘酷的事實所震驚。在皇家音樂學院學習的日子里,他前往倫敦的一家電影院去觀賞默片《四騎士血灑自由魂》(后在1962年重拍),很大程度是沖著默片巨星范倫鐵諾(Rudolph Valentino)而去的,他還記得當騎士們出現在熒幕上時,“充滿毀滅感”的貝多芬《科里奧蘭》序曲不失時機地奏起,可是,當他們看見千百個小小白色十字架與無數墳墓的時候,驟然間明白了影片的真正含義,這位十八歲少年的淚水奪眶而出,竟然頭也不回地從電影院沖了出去。就是在這樣的時機下,以戰爭思考為主題的作品雛形已經在他的心底生根發芽。
之后的作曲學徒期是漫長的,蒂皮特花費了十年時間才醞釀出了第一部“被認可”的正式作品——1935年的第一號弦樂四重奏,但是不可忽略的是這個發展時期里,他扎實地將各方的音樂經驗都吸取到了自己的庫存中,如去倫敦莫利學院為業余合唱團、樂隊擔任指揮等等,為他過渡到一個真正成熟的作曲家埋下了伏筆。
與許多其他作曲家的早年不同,蒂皮特是一個極有耐性的人。他不慌不忙地汲取生活帶給他的每一點養分,無論是與音樂有關的,還是無關的,而恰恰是那些看似無關的事情,決定了他數十年之后的產出。他學習德語,為的是能讀懂歌德,這一點是頗具遠見的,然而與包豪斯學派畫家威福瑞·法蘭克陷入同志感情的漩渦卻被證明是失誤的。可是這兩件事都在作曲家的藝術發展道路上起到了“變軌”的作用。1938年,他與法蘭克的關系經歷危機,最終分道揚鑣,即便這件事情也讓蒂皮特獲得了精神上的進步——他轉而投入到對榮格心理學的實踐中,而之前他只是簡單地吸取了其理論的精髓罷了。最終,蒂皮特一生的作品都受到了這一蛻變時期的影響。
還有,蒂皮特也積極地參與過政治。不過談及他的這一方面時,人們大多將其附屬于蒂皮特的其他屬性,因為他雖然從思想本質上是左翼的,行為卻大多最終導向了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最后這一切也都淡出其人生。
蒂皮特在1926年至1929年之間頻繁前往德國,因此我們可以想見,政治格局隨著1933年希特勒獲選而走向崩壞的事實,無疑影響過蒂皮特對于世界的理解。事后他回憶起當時的感受:“感到自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這一情形,感情與智力上兼有之,很快就有不得不‘為猶太人唱歌’的感覺,不過當時猶太人還并未淪至流亡者、驅逐者甚至更糟糕的境地。”
1938年9月30日,慕尼黑危機。這一事件讓蒂皮特覺得一場規模更大的、災難性的戰爭在所難免。他不由自主地坐到了書桌前,寫下了一個陰暗而緩慢的賦格主題——后來它出現在了第二弦樂四重奏里。可是,沒人想到一切猝然發生:納粹的水晶之夜打響,其導火索是被驅逐的猶太青年格林斯潘求助德國駐巴黎大使館秘書恩斯特·馮·拉特(Ernst vom Rath)未遂,格林斯潘連開三槍使恩斯特·馮·拉特死去。
這一事件與之前的慕尼黑危機不同,倒促發了蒂皮特更廣闊的靈感馳騁——興許從這個具備所有戲劇元素的政治事件中能發展出一部適合音樂廳的大型交響作品。然而,故事的要素是夠了,蒂皮特依然想賦予其一些與戲劇不一樣的東西:深思與反省。換句話說,可能糅合巴赫受難曲與亨德爾那些英國風格的清唱劇,會是一個不錯的作品,對,特別是《彌賽亞》。至于人物呢,那些替罪羊式的形象已然清清楚楚地浮現在了眼前:猶太青年格林斯潘只有十七歲,立即被投入監獄;他的叔叔與阿姨被巴黎當局審訊。蒂皮特手里的《圖片報》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而沒人能想到,這些細微的變化竟然是一場空前絕后的巨大災難的前奏。幾個月后,它席卷了整個歐洲。現在,蒂皮特所需要的,只是有人能為他尚處胚芽期的音樂寫一些合適的臺詞。
T.S.艾略特這樣的大詩人看上去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因為此時的蒂皮特尚且稚嫩,想要高攀有點困難。然而,也許是老天安排,他曾經以“不怎么出名的青年作曲家”身份在1938年的數年之前遇到過一次艾略特。那是蒂皮特在為美國出版商莫爾利的六歲孩子作臨時音樂教師時,于英國薩里與大文豪所度過的難忘時光,當時蒂皮特心中認定艾略特可以成為自己在藝術上的父輩楷模。莫爾利當時與艾略特是在倫敦Faber&Faber出版社的同事。
實際上,將蒂皮特介紹給莫爾利的人其實是另外一位大詩人W.H.奧登,他覺得蒂皮特是輔導莫爾利兒子的不錯人選。說來有趣,那位小莫爾利雖然不善言辭,卻表現出了特殊的音樂天賦,還格外喜歡在音樂會的間隙給大人玩倒立看,算是一個人見人愛的小機靈。而艾略特既然考慮到了這層交情,所以蒂皮特不失時機地詢問他是否愿意為清唱劇寫一個劇本時,多少有點松口的意思。最終,一個肯定的答復傳來,不過附帶著一份需要蒂皮特預先“做功課”的嚴格要求——提供清晰的每一樂章格式,從樂章主旨到詳盡的清唱劇內容說明,需無一遺漏。
當我們今天重新觀察蒂皮特提供給艾略特的草稿時,不難得出結論:為什么后來蒂皮特還是獨立完成了劇本的工作,而將“那些詩人們棄之一旁”——因為”他們想要用語言做到的事情,與我想要用音樂做到的事情是一樣的。“在長時間的餐桌會議”后,蒂皮特決定自己干。他細細打磨了自己的初稿,于是,當他所恐懼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終來臨時,他覺察到“音樂已經在體內噴涌而出了”,所以,正式的作曲該開始了。
只是,當時依舊有一個問題值得他反復思忖。那就是如何尋找到一種足以與巴赫宗教合唱作品等同的氣場,因為一些人們熟知的旋律倒很適合在這樣表達群體性情感的場合以新手法被演繹出來。當蒂皮特1938年不經意地從電臺里聽到了一段黑人靈歌時,他終于找到了解決方案。這么說來也許有點倉促、未經思考的感覺,卻也可以從側面印證其專注度與運用材料的天賦。
于是,在選定了五段合適的靈歌主題后,他將自己擬出的歌詞草稿呈現給了艾略特。據說,當大詩人看到音樂教師寫下的句子,吃驚地說:“這不已經太好了?”事實上,蒂皮特這五個主題也成為了他下一步拓展、加工的五根“結構支柱”,在1939年9月之后,他工作重心就此放到了在框架內對音樂及文本內容的充實上。
《我們時代的孩子》的構架如下:
第一部分:1)世界正處于黑暗的邊緣。2)人類已對天堂作了裁決。3)或許選擇魔鬼更好?4)現在輪到每一個民族了!5)放高利貸者之城,何時才終止?6)我沒有錢買面包。7)每天,我如何去維護我的同胞?8)靈歌:逃避。
第二部分:1)一顆星于隆冬之際升起。2)一個時代的降臨。3)哦,我的孩子!4)無人知曉我親眼目睹的苦難。5)一個男孩在他悲傷欲絕時將不顧死活。6)我的夢想已被徹底粉碎。7)我究竟對你──我的兒子做過些什么?8)黑暗的勢力正在升起。9)哦,再見
第三部分:1)寒冷深入骨髓。2)人類的靈魂。3)箴言正是這些字。4)我愿意知道的陰影、我的光。5)靈歌:深沉的河流。
關于蒂皮特《我們時代的孩子》,國內畫家丁方還有一副同名油畫。它的尺寸是38cm×54.5cm,布面油畫,創作于1993年。它的畫面昏黃不堪,似城非城,似路非路,然而近處的泥濘與遠方天際的光芒兩相對照時,卻有著一種悲從中來的巨大力量。據畫家本人所述,“這幅畫是在對蒂皮特的清唱劇《我們時代的孩子》的精神感領下完成的,因為蒂皮特道出了現代人類離棄信仰后淪入夜半黑暗的悲慘境況。”藝術評論家劉翔則如此將畫作與蒂皮特的清唱劇聯系在了一起:“巴赫《馬太受難曲》是蒂皮特無法不回顧的經典,但在《我們時代的孩子》宏大的合唱中,也能聽到柏遼茲的《基督的童年》那種幾乎透明的簡約。而來自亨德爾《彌賽亞》的三樂章式遞進,使這部作品能從敘事一步步退后,從更廣的角度審視人類的悲劇。此時個人的悲聲與歷史的無情對列展開,直到那首《深深的河》將靈魂推入戰栗的情感洪流……它只是一個瞬間,卻照亮了整條時間的河流。”——譯注
哪怕當我們今天第二次、第三次聆聽《我們時代的孩子》開場的獨唱女高音時,依舊會被那聲高聳入云的高音G所顫栗得不能自己,而這第一句隨即融入了合唱與樂隊的歌詠“逃避”,一切有如魔法般發生。想象一下,在1944年3月19日的倫敦艾德菲歌劇院里,瓦爾特·郭爾(也就是作曲家亞歷山大·郭爾的父親)帶領著LPO和倫敦莫利學院合唱團、倫敦區民防合唱團將《我們時代的孩子》第一次搬上了舞臺,那時的場面是難以想象的。獨唱歌手里分明有著皮爾斯、克洛斯(Joan Cross)這樣的名字,布里頓也為演出的籌備貢獻了力量。我們多么希望哪里還存留著當年的這么一盤隱秘的錄音或錄像帶!事實上,檢驗一場演出是否偉大的標準,很可能是你第一聲聽到它是否會產生脊髓發涼、毛骨悚然的感覺。而我猜測,當這第一聲靈歌在艾德菲歌劇院響起的時候,整個空間里都將充斥著一種無以言說的悲憫與哀愁。
二
1958年,《我們時代的孩子》的第一個商業錄音誕生,指揮者是蒂皮特堅定的戰友約翰·普利特查德(John Pritchard),執棒Decca旗下的皇家利物浦愛樂,獨唱者包括了艾爾西·莫里森(Elsie Morison)、帕梅拉·鮑頓(Pamela Bowden)和理查德·劉易斯(Richard Lewis),那幾位完全是“布里頓圈子”里應該出現的名字。這個錄音的優勢在于Belart廠牌逼真的轉制效果,將該演出雄辯語氣十足、動態與能量源源不斷,卻不失清晰明快的特點體現得很到位,這也應該是指揮家普利特查德一貫的長項,他1955年在柯文特花園指揮《仲夏夜的婚姻》一劇的首演也是與之相符的反映。
這個早期版本的效應是毋庸置疑的,真讓人懷念利物浦最醉人的歲月。普利特查德身為新音樂的堅定擁護者,同時也是蒂皮特的朋友,為后來的許多音樂家奠定下了《我們時代的孩子》的一個標準模板,據說已與作曲家本人的構想極其接近了。在創作出這首清唱劇之后,蒂皮特的名字可謂在大不列顛一夜飄紅,繼而有明智的出版社如美因茨的朔特(Schott)為它在歐洲大陸的普及付出了緩慢但堅定的努力,而當時的“大人物”之一卡拉揚在1953年的都靈指揮了該曲,這些都與早期錄音的完美問世脫不開聯系。現在想來,那真是作曲家魔幻級別的提升。
當然,拋開歷史文獻與美學觀念上的價值不談,這個利物浦錄音還是有不足之處的。比如男低音歌唱家斯坦頓(Richard Standen)的嗓音似乎太朦朧,就像某一位BBC播音員在一個灰蒙蒙的雨天喃喃低音,令人昏昏欲睡。
本文想推介的一共八個《我們時代的孩子》版本,其中三個都離不開輝煌的男低音約翰·謝利-夸克(John Shirley-Quirk,1931-),而同樣有三個是屬于偉大的英國指揮家科林·戴維斯的。這兩個重要人物在1975年飛利浦公司的一個錄音里有了交集。那是戴維斯帶領BBC交響樂團在溫布利鎮音樂廳的一次錄音,除了夸克外,參與其中的還有優秀的女中音珍妮·蓓克(Dame Janet Baker)與女高音杰西·諾曼。
說實話,這張唱片對于我們很多人都已經是默認的經典了。它的地位似乎無可辯駁,不過今天端詳起來并不是那么的完美。何故?戴維斯第一次和蒂皮特合作是在1950年代晚期的一次電視音樂會上,而他真正的蒂皮特作品首演還要等到1963年于愛丁堡的《樂隊協奏曲》,而且該曲很快就獲得了錄制機會。到了1975年,戴維斯的蒂皮特庫存已經頗為可觀,其中囊括了兩部歌劇、三首交響曲和與奧格東(John Ogdon)合作的鋼琴協奏曲。而他的《我們時代的孩子》實際上正是建立在這一別無二家的演出經歷(或者說傳統)之上的,何況他兢兢業業地指揮了另外幾部:《破冰》、《時代的面具》、《玫瑰湖》和那首有名的三重協奏曲。
無疑,戴維斯對蒂皮特作品有著持之以恒的熱忱,而后者的事業多少蔭佑于他巨大的支持。但是,對于戴維斯的第一版錄音,相對而言似乎缺乏一種成型感,或者說因累積而得的底氣還不夠,我們可以在音樂展開的連續性上讀出些許造作的痕跡。單拿每一個樂章出來,其步調都值得贊美,蓓克與謝利-夸克的演唱也都感人至深,可是……
不可否認,杰西·諾曼這樣的歌唱家在《我們時代的孩子》的演繹歷史上無可忽略。她從1975年開始就已經接觸該劇了,因此其錄音絕不算“突然襲擊”,而是合乎本性的抒發。她與該作品的心意相通,或者說對靈歌這一體裁特有的、高出其他聲樂同行的直覺,是她不斷在公眾演出中推廣該作品的原始動力。1979年,她在蒂皮特親自指揮下獻演于BBC Proms音樂節,算是一個經典了。唱片中她所演唱的部分,充滿著撩人的靈性,同時也證實了其無可爭議的女性靈歌權威演繹者的地位。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諾曼女士的演唱雖然能量澎湃,蔚為輝煌,卻不怎么精道于內在文本的含義。比如這句唱詞,“原因忠于自己,但惋惜打開了心靈”(Reason is true to itself,But pity breaks open the heart),在女中音杰內特·蓓克(Janet Baker)的第一聲吐字里就讓人永遠難以忘懷,這也許恰恰是蓓克所最擅長的一面,同時也是諾曼的一個小小短板。
而這張唱片里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時代的孩子”自己,即美國男高音歌唱家理查德·卡西里(Richard Cassily),他的嗓音本來就有些許的“尖厲”感,而一旦施予壓力,就有點像被扼住頭頸的那種悲鳴,反復聽著多少讓人難以承受。至于戴維斯爵士在后面的兩次(現場)錄音中能否取得長足的進展,我們稍后再說。
同樣的BBC人員加上音質醇美的英國男低音夸克1980年在皇家節日音樂廳聚首,在大指揮家羅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棒下,為BBCSO成立五十周年獻上了一場《我們時代的孩子》。幸運的是,錄音記錄下了這個精彩的夜晚。唯一的軟肋可能是英國男高音歌唱家沃拉姆(Kenneth Woollam),他的聲音有些不修邊幅,好在還算有激情。至于女高音戈麥茨(Jill Gomez)的聲音呢,有著灼熱卻易碎的特點,倒也符合作品需要。而威爾士女低音華茲(Helen Watts)簡直就是無與倫比的、梭梭屈里士夫人(Madame Sosostris,艾略特《荒原》里著名的女相士)的化身!對了,現在可以指出,這個錄音就能很清晰地體現出戴維斯爵士在現場錄音的優勢了(相對于錄音室)——這是一種所有歌手同心協力的凝聚場面,而絕非幾個單槍匹馬的個體臨時組合而成。無論在戲劇性,還是音樂性上,這部作品都太需要這種自然、開闊的氛圍了。總之,這已經是一個接近“夢幻版本”的錄音了。
不凡的男低音夸克還第三次錄制過該曲,那是1986年,可謂是一個圓夢的時刻。不過這次,感覺敏銳的普列文擔任了指揮,他們和RPO以及匈牙利籍指揮家哈爾泰(Laszlo Heltay)麾下一流的布萊頓節日合唱團,一起去阿比路錄音室完成了錄音。獨唱者中還包括了英國女高音阿姆斯特朗(Sheila Armstrong)、女中音帕爾默(Felicity Palmer)與男高音蘭格里奇(Philip Langridge)這樣響亮的名字。可以想見,這個陣容里并不存在明顯的弱點。而這個華麗的獨唱組合沒有錯過任何一個觸動人心的細節,與合唱團、樂隊天衣無縫地浹洽到了一起,讓人驚訝地承認,錄音室環境并沒有成為演出連貫性和演員自我表達欲望的障礙,反而造就了一種自然而然的雄辯力,一切細節都寬松地完成了。然而,真正令整個版本出類拔萃的,正是男高音蘭格里奇,他以每一句唱詞中微妙色彩變化的掌握成為了這張光輝演出里的主心骨。當唱出“我愿意知道的陰影和我的光,這樣我就能最終完整無缺”時,蘭格里奇簡直成為了榮格心理學理論的優秀代言(譯者注:此處應該指榮格的陰影理論,該“第二自我”存在于個人潛意識的淺層,常與自我形成一種對立,唯有當自我與陰影相互和諧時才真正有活力)。你不再懷疑,他就是全場演出最耀眼的“北極星”,該角色的意義也因此達到了巔峰。
這么說吧,如果把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錄音一個個“盲聽”過去,恐怕唯一能在一瞬間揪緊我的心,并讓呼吸凝止、淚水決堤的版本,只有它了。可惜,該錄音在市場上已幾乎斷檔了。雖然說起它所屬的自有廠牌RPO,不怎么有威名,然而請的卻是普列文本人最喜歡的一位印度裔制作人格拉布(Suvi Raj Grubb,為EMI完成過很多傳奇錄音)操刀,看在這份文獻的珍貴價值面上,我們期待它有朝一日能重新發行。
拿索斯敏銳地嗅到了機會,他們從Collins Classics廠牌那里獲得了作曲家在1991年自己指揮的一個錄音,哪怕其錄音不怎么樣,作為歷史文獻都是很珍貴的。事實上,這個錄音還是蒂皮特最后一次指揮,對于八十七歲的老人而言,這樣的大體力任務從任何意義上說都是艱難的、英雄式的。蒂皮特在完成這次任務時幾乎已經失明,即便如此,精疲力盡的他還是拒絕任何人代勞,理由是討厭別人認為自己已經不再能控制住局面。更可貴的是,這個錄音捕捉住了其他錄音里無法清晰展示的細節,比如在女低音唱段后出現的、弦樂上“secco pp”的極弱和弦。總之瑕疵很少,僅有的幾個恐怕是第二與第四段靈歌的速度有些異乎尋常的緩慢。也許,這并不是因為蒂皮特年紀大了的緣故,而是他回憶起了最原始的、深思熟慮的作曲意圖,而無視了譜面上印刷著的速度記號吧。因為當我們回顧1958年的普利德查特版時,會發現這兩首靈歌采用了同樣的慢速。反觀科林·戴維斯的棒下,這兩段就越來越快了。羅日杰斯特文斯基與普列文都選擇了中速,這一選擇在美學上也許是永遠穩妥的。
聽慣了新錄音后,蒂皮特本人的速度,聽起來總有點拖沓或垂頭喪氣的緩慢,令人不怎么適應。而該錄音另外一個技術上的不利條件在于,聲線強勁的男低音約翰·齊克(John Cheek)此時的聲音卻像是從演員休息室里傳來,而美國女高音羅賓森(Faye Robinson)與英國女中音沃爾克(Sarah Walker)即使嗓音絕妙,也總像一團似地、親昵地擠在指揮家的周圍。男高音加里森(Jon Garrison)的聲音則夾插在了她們倆之間,整體的音場是不平衡的。
根據2009年版企鵝唱片評鑒手冊,希科克斯的這個Chandos版本亦不謀而合地成為了“三星帶鑰”的首選,被譽為“溫暖而具有表現力”,同時企鵝認為,作曲家本人在Naxos的處理松軟綿厚,而科林·戴維斯的緊繃感很突出,羅日杰斯特文斯基1980年版則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特色在老版本企鵝手冊里獲得了一席之地。——譯注
在我看來,英國指揮家理查德·希科克斯(Richard Hickox)與LSO在Chandos廠牌下的錄音效果應該是我提到所有唱片里最好的一個——無論是伴奏,還是聲樂演唱,其音效簡直完美無缺。然而,他們可能出于詮釋意圖的考慮,為演出安排了四位黑膚色的歌手,但結果卻不怎么理想,起碼在聲樂藝術上還有欠缺。具體說來,懷特(Willard White)自然有著堂正威風的聲音,可是從始至終卻帶著一些情感上的矯揉造作,阻礙你去反復聆聽。
對于科林·戴維斯2003年帶領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的那個錄音,恰恰產生了一個相反的問題:情感投入雖然全場都充溢著一種感人肺腑的真誠,女低音古比希(Nora Gubisch)與男高音哈德利(Jerry Hadley)卻始終無法有足夠大的能量承擔這部作品。所以最終,這個錄音也降低到了錄音文獻,而非佳片力薦這一層面。
幸運的是,我們終于等來了一個2007年LSO的現場錄音。這次科林·戴維斯爵士終于以他對《我們時代的孩子》總譜深刻的挖掘以及全身心的投入(比如不停地哼哼暗示聲),贏得了一次精美絕倫的詮釋。整支樂隊與合唱團都似乎被其意志力所折服,忠實于他的每一次比劃與暗示。獨唱歌唱家們并非大牌:女高音托馬斯(Indra Thomas)、女中音藤村(Mihoko Fujimura)、男高音大衛斯利姆(Steve Davislim)以及男低音羅斯(Matthew Rose)。然而他們的統一協調性,足以讓音樂集聚成了不可遏制的洪流。而這一幕在1975年前后較僵硬、粗糙的錄音里是看不到的。作為戴維斯帶領LSO在巴比肯藝術中心所錄制的最后那批唱片之一,這個錄音值得我們牢記,并以此讓世人看到了一部價值不可磨滅的作品,與一位同樣偉大的英國指揮家,是如何相伴其漫漫人生,并偕老于其偉大的心靈。
編輯/張定浩
*本文譯自《Gramophone》雜志2014年7月刊,Geraint Lewis,“A Passion For Our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