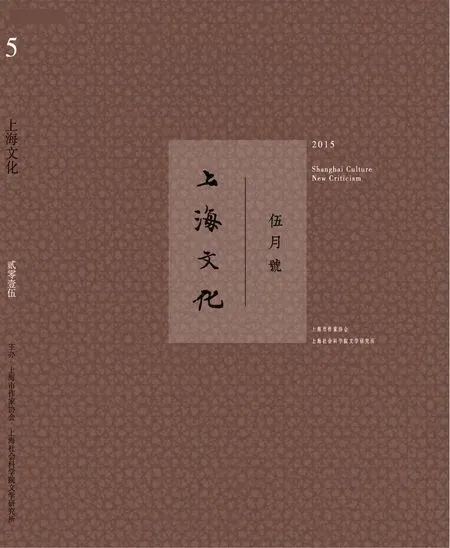再見,阿倫特*
瑪麗·麥卡錫 魏忠賢 譯
再見,阿倫特
瑪麗·麥卡錫 魏忠賢 譯
一
她的最后一本書被命名為《心智生活》,計劃當作《人的境況》(一開始叫《行動生活》(Vita Activa))的補充,在《人的境況》中,她細致審視了三個概念——勞動、工作,和行動:這三個概念分別對應著人作為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技藝人(homo faber),以及公共事件的行為者。而在《心智人生》中,她看到了心智的生活,或者說,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心智也被分為三個部分:思索、意愿,和判斷。第一部分,關于思索,早些時候已經完成。第二部分,關于意愿,在她去世前剛剛完成,完成這一部分,一定讓她輕松不少,因為她發(fā)現(xiàn)意愿是這種官能中最捉摸不定、難以把握的。第三部分,判斷,她已經有了梗概,并且寫了一些,雖然關于這一部分留下的文字很少(留下的主要是關于康德的),但是她覺得這一部分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我說“她的最后一本書”——漢娜也是這樣認為的,因為這將是她最后的工作,或者說,是她的最高成就,如果她完成了它。這本書不僅將補充(行動生活之外的)人類能力的另外一個維度,而且是人類能力最高和最無形的表現(xiàn):心靈的活動。如果她能夠活著看到這本書(兩卷,實際上)付梓,毫無疑問,她還將寫下去,因為她的天性就是思考,并表達,但同時,她也會覺得,她真正的工作已經完成了。
這種感受,對她來說,跟自我實現(xiàn)無關(自我實現(xiàn),這種想法對漢娜來說,若不是可憎的,也是可笑的),而是一種誡命,我們所有人都背負著它
二
她來到這個世界上,似乎天生就是要來完成一次侍奉或者執(zhí)行一件任務。在這個意義上,我相信,漢娜是虔誠的。她聆聽到了一個聲音,就像先知聽到圣訓,像孩童時的撒母耳,身負圣衣(linen ephod),在大祭司以利的住所,面臨圣召。你也可以以一種更世俗的方式看待這件事,認為漢娜感覺到自己身負契約,盡管束縛她的契約另一方,是她那被自然(Nature)賦予,被她的老師們——雅斯貝爾斯以及海德格爾——發(fā)展,被歷史悲劇性地強化的杰出天賦。這種感受,對她來說,跟自我實現(xiàn)無關(自我實現(xiàn),這種想法對漢娜來說,若不是可憎的,也是可笑的),而是一種誡命,我們所有人都背負著它,而不只是像那些用生命的軌跡追隨機會和命運的天才,比如詩人,追隨對繆斯的信念。阿倫特不相信讓人盲目的奴性觀念(slavish notions),比如個人“責任”那一套(這大概能夠解釋,為什么在《心智生活》的“意志”部分,她遇到了如此之多的麻煩),但是對于使命感、天職,包括公民對公共生活的效力,她卻是積極響應的。與此同時,她也是一個注重私人生活的人,我想(雖然我倆從沒談起過)《心智生活》這本書,她是用來紀念海因里希的,某種程度上,作為他們共同生活的完滿結束。
海因里希·布呂歇,她的丈夫和朋友,是她的最后一位老師。雖然他只比她大十歲,但是在他倆的智識關系中,有一種類似于父愛的東西,海因里希寵溺著她,而阿倫特像小學生一樣,熱切,并期望被認同;像她曾說過的那樣,他會一邊用憐愛的眼神看著她,一邊點頭,好像幸運女神給他送來了一位超乎想象的聰明女學生,一位非凡的向目的地進發(fā)的人(achiever),對他這位從各種意義上都屬于哲學家的人來說,他可以嘴含煙斗和雪茄,安心地不去做進發(fā)者了。他為她感到自豪,并且知道,她能夠走得很遠,走向他可以遠遠看到的高度和廣度,他可以平靜地在后面坐下,等她找到它們。
對漢娜來說,海因里希就像一副鏡片;在獲得海因里希的確認之前,她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洞見。不過,在大多數問題上,他們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只不過他的精神氣質更偏向于“純粹”哲學家,而她更關注實踐生活(vita activa),不管對于政治還是對于制造——以書和文章的形式鑄就持久之物;對于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的生物領域——家務、消費,他們都不感興趣;雖然他們都喜歡年輕人,但是他們從沒要過小孩。在他1970年年末突然去世的時候——雖然她的離去更加突然——她便孑然一身。她被朋友們包圍著,卻像一位孤獨的旅客,獨自乘坐在她的思想列車上。所以,在那黯淡的日子中開始動筆的《心智生活》,是為海因里希·布呂歇而構思,而思考,(她一定也希望和他一起寫書,)它不是一個里程碑,而是一個像閉合的三面屏風一樣的存在,中間包圍著神秘的意愿。不過話說回來,這些都是我的猜測,我也沒有機會當面問她了。
三
我剛說到了漢娜的無以比擬的成就(crowning),但是漢娜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野心(說她要創(chuàng)造個什么事業(yè),這是很荒謬的);如果說漢娜曾為一個成就(crown)努力過,那么只是在下面這種意義上:她像一個探險家,獨自完成最后一步,吃力地到達一個頂點,就是想站在這個頂點上,舉目四望。而在她眼前展開的,卻是一個黑暗時代,她作為一個猶太人,一個流離失所的人,承受并目擊著這一切: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流產;美國共和制在當下所遭遇的威脅。美國共和制,是她找到的一個新的政治歸宿,在這里,她寄予著自己一直念念不忘的自由理念——雖然越來越失望——并像測繪員一樣,鋪展開她那龐大的概念和洞見之地圖,這些概念和洞見中,有些來自悠長的哲學傳統(tǒng),有些則是她自己的發(fā)現(xiàn),它們因得自她所在的高度,所以最起碼也能讓我們看到,我們在哪兒。
在觀念領域,漢娜是一位保守主義者;她從來都不信奉那種把前人思考過的問題拋到一邊的做法。它們總會有用的;用她自己的方式,她是一個狂熱的回收者(recycler)。換種說法,思想之于她,是一種耕種,是給蠻荒的經驗賦予人性——建造房屋、鋪通道路、筑壩截流、種樹防風。因為她是才華卓越的知識分子,是她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所以降于她的大任,就是將她所處時代的每一種獨特經驗——失范(anomie)、恐怖、高科技戰(zhàn)爭、集中營、奧斯維辛、通貨膨脹、革命、學校取消種族隔離、五角大樓文件泄露、太空(space)、水門事件、教宗約翰、暴力、公民不服從——系統(tǒng)地加以思考,并且,通過它自身,以及它自己的獨特進程,最終實現(xiàn),將思想內化。
這些概念和洞見中,有些來自悠長的哲學傳統(tǒng),有些則是她自己的發(fā)現(xiàn),它們因得自她所在的高度,所以最起碼也能讓我們看到,我們在哪兒
“系統(tǒng)”這個詞,可能會造成誤解。盡管她有德國人的習慣,但漢娜可不是一個系統(tǒng)建造師。相反,她尋求對已經存在的系統(tǒng)進行檢視,系統(tǒng)固存于人作為主體與世界和自我進行互動之時。在遠古,隨著語言的誕生,不,實際上是隨著言語的誕生,這和那(比如工作和勞動,公共和私人,強迫、權力和暴力)之間的顯著區(qū)別就已經反映出,人很會分類,如果你愿意,便是“天生”的哲學家,與構建整體相比,分析(separating)的能力,敏銳的分辨力,對人這個物種來說,是更自然的。如果你對漢娜有所理解,就會認識到,漢娜更傾向于多而不是一(這也許能夠解釋,對于極權主義這一世界中的新現(xiàn)象,她為抱何以如此恐怖的認識)。她沒有尋找萬能方法或放之四海皆準的通則的意愿,如果她有所信仰,那么這信仰絕不會是一神論的。她的作品向許多方向發(fā)散,在每個方向上,都像青嫩的樹芽,抽枝延蔓,毫無疑問,這部分地要歸因于她對經院學術的喜愛,但與此同時也證明了,在世界的豐富性和強烈的獨特性面前,她那充滿敬畏的謙卑。
和其他優(yōu)秀的演講者不同,她完全不是那種雄辯的方式,而是看起來更像一座礦藏、一位悲劇演員
四
不過,在這里我不想討論漢娜的思想,我只想試著將漢娜這個人,一個活生生的存在,重現(xiàn)出來,展現(xiàn)漢娜在這個她稱之為表象世界的舞臺上的風采,如今,她已在這個舞臺上謝幕。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嫵媚、誘人、富有女人味,正因為此,我稱她是女猶太人(Jewess)——這是一個過去的術語,用來稱呼錫安人的女兒們,就像西班牙流蘇圍巾和她非常相配一樣,這個稱呼和她相得益彰。尤其是她的眼睛,如此明亮閃爍,當她高興或激動的時候,一雙明眸熠熠生輝,但她的眼睛也很深邃,黑色的眸子,深遠的目光,斂著一泊靈性。漢娜身上有某種深不可測的東西,安居于她的目光之中。
她有一雙小巧的手,迷人的腳踝,優(yōu)雅的雙足。在我認識她的這么多年里,她很喜歡鞋子,從沒虧待過她的腳。她的腿,她的腳,她的腳踝,全都透露著敏捷、決斷。只需看看她在講臺上的姿態(tài),小腿,腳踝和雙腳都好似要和她的思緒保持一致。當她講話時,她會踱來踱去,有時雙手插入口袋,像在獨自散步,沉思。允許的情況下,在講臺上踱步時,她會手拿一支裝著煙嘴的香煙,時不時吸上一口,有時候突然一回頭,好像被一個新的、未曾料想到的想法攫住。看她對臺下的人說話,那些動作和姿態(tài),好像思想的運動可以被看見了一樣。她是一個如此隨性的人,會在講課的時候突然停住,皺著眉,盯著天花板,咬著嘴唇,沉思地托著下巴。如果她是在念一篇演說稿,那么就總是會有感嘆詞,插入旁白,就像她文稿中的腳注一樣,布滿限定性的條件和附加的說明。
漢娜極富偉大女演員的氣質。我第一次在公共場合聽她發(fā)言——差不多三十年前了,在一場爭論中——她讓我想到伯恩哈特(Berhardt)或者普魯斯特的玻爾瑪(Berma),一位氣勢宏闊的歌劇女主角,活脫脫就是一位女神。不是那種夢幻的女神,而是一位神秘的或者熱烈的女神。和其他優(yōu)秀的演講者不同,她完全不是那種雄辯的方式,而是看起來更像一座礦藏、一位悲劇演員,在思想中上演戲劇,演繹著我和自己的對話,這種對話在她的書寫中常常被喚起。看著她在臺前的演講,會讓人覺得,劇場的神圣起源——古希臘的舞臺,仿佛近在眼前,作為演員或者作為受難者,她塑造的,是飽受良心和反思之沖突的人類形象,這樣的形象總是成對出現(xiàn),其中一個傾吐心聲,另一個回應或者質疑。
但實際上,漢娜也是最不愛出風頭的一個人。她從來不深思熟慮自己給別人的印象。所以,不管什么時候,只要公開演講,她都嚴重怯場,結束后,她只會問“還行吧?”(不過,在教室跟學生們講話就是例外了,這時候,她會感覺很輕松,就像在朋友們中間。)自然,她也不會在私下或者公共場合逢場作戲,即便是社交中常常需要的一點逢迎,她都不會,她不擅長假裝。雖然她總是驕傲于自己作為歐洲人,挺會說謊的,而不是像我們這些莽撞的美國人,總是把真相脫口說出,在這一點上,她有點小小的傲慢。但是,這點小小的驕傲,從來和她真正的成就沒有關系,而是表現(xiàn)在,舉個例子,她會覺得自己還挺懂烹飪的,但其實啊,她才不懂,同樣的,挺會撒謊的這一點,也是她自己以為的。在我和她成為朋友的這么長時間,我想我從沒有聽她說過一次謊,哪怕是善意的謊言,比如假托生病或者提前有約,而讓自己從一個社交窘境中解脫。如果她發(fā)現(xiàn)你寫的什么東西她覺得不好,依她的一向做法,她才不會拐彎抹角地跟你說,而是毫無例外地,把她的想法大聲地告訴你。
五
漢娜身上最有戲劇性的地方,就是當她被一個想法、一種情緒、一種預感攫住的時候,無意識中爆發(fā)的力量,這時候,就像演員,她的身體變成了它們的媒介。被這種力量占有的時候,經常是以一下睜大眼睛為開始,然后發(fā)出“啊”的一聲(這種情況發(fā)生在,她盯著一幅畫,一處建筑,或者某個惡行的時候),像被電了一下,然后意識從我們眾人中抽身出來。她那一頭充滿活力富有彈性從未變得全灰的深色短發(fā),在這股純粹力量的刺激下,也在她頭上豎了起來。
我想,所有這些,一定是一種不同尋常的天賦的一部分,我說的漂亮指的就是她的容貌和面部表情中的這些表現(xiàn)。漢娜是我見過的人里面唯一一位可以看到她思考的。她會躺在沙發(fā)或者午休床上一動不動,雙手枕在腦后,閉著眼睛,偶爾睜開盯著天花板。這種狀態(tài)能夠持續(xù)——我不知道——從十幾分鐘到半個小時。如果我們無意中走進了她躺著的屋子,我們每個人都會踮起腳尖,躡手躡腳從她身邊走過。
她是一個不那么耐心、又慷慨大度的女人,這些品質總是一同在一個人身上出現(xiàn)。比如,在一個演講或者是一篇文章中,她會想要把所有她知道的東西或者恰巧跳進她腦子里的想法都塞進去,就好像她不能集中在單一的主題上,所以她會強行給來訪者奉上各種堅果、巧克力、甜姜、茶、咖啡、金百利酒、威士忌、香煙、蛋糕、餅干、水果、奶酪,幾乎一次性奉上所有,而不去顧及慣例所安排好的順序,或者,更多地,是不去顧及是否是合適的時間。就像成堆的豐富食物,被放在節(jié)慶用的盤子和容器里,端出來,粗獷地討好口味不同的所有神靈。有人說,這是永恒的猶太媽媽的做法,但實際并不是這么回事:她并沒有打算這些食物對你有好處,實際上,這大多數食物對你來說,顯見是有壞處的,漢娜一定對此有所了解,因為她并不堅持讓你享用。
對于私人領域,包括他人的以及她自己的,她都報以尊重。我經常和她待在一起——跟她和海因里希——在河濱大道,之前是在晨邊大路的寓所,所以我能了解這一點。漢娜的生活習慣很好,比如,她喜歡的早餐,是一個煮雞蛋,一點火腿或者冷切肉,一塊抹上鳳尾魚醬的烤面包,一杯咖啡,當然了,還會有半杯新鮮的葡萄汁或者橙汁,不過有可能這新鮮果汁只有當我這個美國人在她家的時候,才會出現(xiàn)。海因里希去世后的那個夏天,她跑來緬因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讓她住在一個單獨的小套間里,在車庫的正上方。我花了一點心思為她置辦廚具——她喜歡一個人吃早餐。我想她在自己家中會用到這些東西,像速溶咖啡(我一般不會常備),這樣她就不會為咖啡濾紙而煩心。而且,能在鄉(xiāng)間小店中為她找到鳳尾魚醬,也很讓人開心。她抵達的下午,當我?guī)еタ词称饭瘢瑢χb鳳尾魚醬的小管子皺眉,好像那時一種讓人費解的外國東西。“這是什么?”我告訴她答案。“哦。”她放下它,看起來在思索,并且不知怎么搞的,好像不太高興。她沒再說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做錯了,因為我努力去討她高興。她不太希望被以這種窺探的方式,這種有限的、簡化的方式被了解。我的所做,是在向她表明,我了解她——一種愛的象征,但是并不總是這樣——從而這也證明,說到底,我根本不了解她。
她緊閉雙眼躺在棺中,她的頭發(fā)被從前額梳向腦后,要是她自己,她一定會相反,把頭發(fā)拉到前額,有時候,在演講的時候,她還會把頭發(fā)固定在前額,用來遮住車禍留在頭上的一塊傷疤——但是即便在那塊傷疤出現(xiàn)之前,她也很少露出眉毛。在她的棺中,眼瞼遮住她深不可測的雙眼,高貴的額頭上挑著某種大卷發(fā),她看起來不再像漢娜,而像帶著一副18世紀哲學家的死亡面具。在葬禮上,我沒有走近去摸摸這個高貴的陌生人,只有那脖頸,那柔軟卻布滿皺紋的脖頸,那支撐著這個公共頭腦的脖頸,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找到一個地方,跟她說,漢娜,再見。
編輯/黃德海
*這篇文章,是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1912-1989)在漢娜·阿倫特去世之后,在1976年1月,發(fā)表在《紐約書評》上的一篇紀念文章。麥卡錫是一位在美國當代文學界享有很高聲譽的作家。她擅長對婚姻、兩性關系、知識分子以及女性角色進行辛辣評論,作品備受社會各界關注。麥卡錫是“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美國“國家文學藝術研究院”院士。她曾獲得愛德華·麥克道爾獎章(1982)、美國國家文學獎章(1984)以及羅切斯特文學獎(1985)等多項獎項,被《紐約時報》贊譽為“我們時代唯一真正的女作家。”更重要的是,麥卡錫是阿倫特在美國的摯友或者說閨蜜,這段二十余年的友誼一直維持到阿倫特去世,兩人之間的通訊集已經出版,名為《Between Friends:The Correspondence of Hannah Arendt and Mary McCarthy 1949-1975》。——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