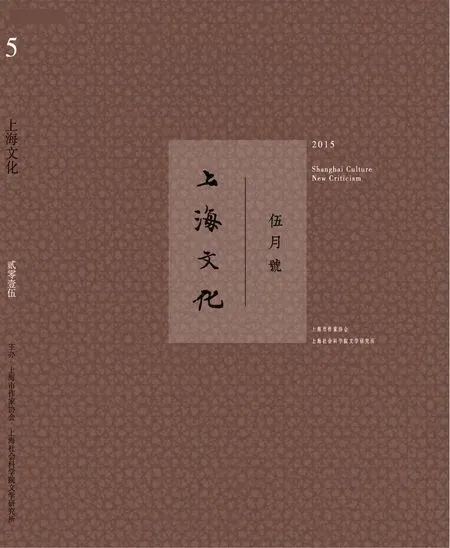為生活于現在評胡桑的詩
王健
為生活于現在評胡桑的詩
王健
受雇于一個偉大的記憶,為生活于現在。
——特朗斯特羅姆
如何將“現在”從答案重新轉化為問題,如今也變成了困擾著當代詩歌寫作的難題
為了讓詩歌能更有力的切入“現在”,詩人做著雙重驅離的嘗試,首先是在作為象征的語言層面;其次是在作為意識形態的“現在”層面。這雙重的驅離都源于“現在”流傳至今后,已變成了一個被用濫的詞匯,它因各種話語的塑造而被固化,以至于很多時候都被看做是一個不證自明的東西:或被看做是某些物理時間的截點;或被納入某些以“創新”為名的實驗之中(無論是在語言層面,還是意義層面),并繼而被一些花哨的技巧暗中所替換。“現在”的意義正在變得單一化,它仿佛變成了一種能夠被學習的知識而非一個需要被探討的問題。如何將“現在”從答案重新轉化為問題,如今也變成了困擾著當代詩歌寫作的難題。從這個角度切入來解讀胡桑的詩歌,或許我們能更容易發現他的意圖與貢獻。
在胡桑的詩歌中,兩種驅離的努力都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妨先從語言層面尋找解讀胡桑的入口,因為作為交流中介,語言總是詩人最先呈現給我們的東西。詩人總是致力將事關自身思考溫度的詞語擦亮,來承載他所體驗到的現在。在對胡桑詩歌的閱讀中,黑暗是他呈現給讀者的第一個關鍵詞。
胡桑熱衷于書寫黑暗,這個詞匯他的詩歌中時常可見:
小區深處,亮著幾盞燈,仿佛一些邀請。
一個靈魂,跨越黑暗,才能取消盲目。
——《空柵欄》,2012
只有卑微的人們接納了我們的眼淚
最大的勇氣是,在別人的羨慕中承認失敗。
或者從自己的夢境之中走出來,
和烈日中的黑暗相遇,和危險相遇。
——《與鄭小瓊聊天》,2012
旅行使我變得漫長,我試圖傳達黑暗的時刻,
它們卻離我而去,如難產的燕子。
言辭的疾苦,毀壞了事物誕生時的快感。
——《命名》,2011
黑暗構成了胡桑的“對手”,以及他的詩歌所要探索的方向。這個詞在胡桑詩歌中的意義非常靈動,它似乎是一個難以被容納的點,游離于燈盞的邀請、夢境的融合和言辭的表達之外,卻又需要“光明”(無論是以燈、烈日,還是言辭)的映照才能產生意義。在胡桑的詩歌里,黑暗毋寧說是一種潛在的意義幽靈,它更多被當作“光明”的界限來使用。也正是借助著這個幽靈,胡桑從被一一對應的象征關系所緊束的語言意義中驅離,從而擴大了其詩歌的表述視角:因為他不僅要對暴露在“現在”的光亮之下的東西進行描述,還要將視角投向這些光亮之外,對被它所隱匿的黑暗進行探索與表達。這探索的層面展開會有很多,它可以是現實生活中理性與盲目之間界限的探索、是在與他者的關系中羨慕與失敗之間糾葛的理清,也可以是用語言表達生活的過程中誕生與毀壞之間關系的觸碰等等,“現在”于是就成了這些光明與黑暗之間的結合體,同時容納著無數的已知與未知。
在這種“現在”的時間之中,語言是具有著增值功效的。胡桑將自己的語言從象征的神話中驅離,旨在將語言面對未知世界進行的言說功能重新呼喚出來。這世界因其流動性的邊界而被軟化,詩歌對現實的言說于是就指向了一種對生活的未知層面進行探索的現實行為,因此黑暗就變成了一種有待開發的潛能,從它之中探尋的實則是構筑當下的活動,如阿甘本所論:“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現在回到關于當代性之黑暗的主題上,這種黑暗就不應該被當作一種惰性的或消極的形式。相反,黑暗表達了一種活動或一種獨特的能力。在我們的情形里,這種能力等于對時代之光明的中和;中和是為了發現時代的晦暗,其特殊的黑暗——黑暗是可以與光明相分離的。”這種作為活動的黑暗或許也是胡桑所想要的。
黑暗指向構筑當下的活動,而在胡桑的詩歌中,這些活動又具有著高度的復雜性,他所想要的探索是迂回和徘徊著的,而不是一種略帶魯莽的勇往直前。黑暗中蘊含的是一種光明的不完滿性,如他詩中表現的“盲目”、“危險”與“疾苦”等,胡桑需要這種不完滿性來平復“光明”所帶來的傲慢,讓行動變得有節制。但這不完滿性同時也呼喚著行動的勇氣,界限在被設定的同時也會設定著突破界限、抵達光明的欲望,如同阿甘本所闡述的“當代人”那樣:“要在現時的黑暗中覺察這種努力駛向我們但又無法抵達我們的光明——這意味著成為當代的人。因此,當代的人是稀少的。出于這個原因,做一個當代的人,首要的就是一個勇氣的問題,因為它不僅意味著能夠堅守對時代之黑暗的凝視,也意味著能夠在這種黑暗中覺察一種距離我們無限之遠、一直駛向我們的光明。換言之,成為當代的人就像等待一場注定要錯失的約定。”黑暗中所蘊含的潛能為欲望提供了一個通往無限與圓滿的目標,也讓這目標變成了一個持續的過程,正是在這來來回回的糾葛中,胡桑的詩抵達了混沌的“現在”入口。
在胡桑這里,黑暗具備了蘊藏潛能、保持謙遜和呼喚勇氣的三重意義,它的存在并非為了營造一種詩意的愁思,而是切切實實地指向對被隱匿的秩序和被遺忘的體驗的持續探索
在胡桑這里,黑暗具備了蘊藏潛能、保持謙遜和呼喚勇氣的三重意義,它的存在并非為了營造一種詩意的愁思,而是切切實實地指向對被隱匿的秩序和被遺忘的體驗的持續探索。因此,黑暗并不會蹈向虛無,后者的意義更具形而上的特點。胡桑的詩歌中也有“虛無”一詞,只是它出現的相對較少,它僅僅作為一個意義的通道,胡桑需要透過它去觸摸詞與物的裂隙,以抵達被隱藏的黑暗的部分,從而讓自己的語言持續陷入到混沌之中,使其包含更多意義的褶皺,帶出生活的廢墟。胡桑所要展現的,并不是隱藏在有之下的無,而是隱藏在一之下的多。
如果將如何對黑暗進行探索的問題往下落實,又會涉及到很多的層面,詩歌在這里只是在語言表述層面的一種嘗試。與此相應的問題是,究竟應當如何去表達那些有待書寫、有待表達之物,從而讓文字變得性感起來?面對這個問題,胡桑的詩歌找到了“沉默”這個契點,但他的沉默并不是放棄言辭,而更像是用文字對待黑暗的一種態度,它與我們上文所說的勇氣相關,也伴隨著語言對黑暗的難以表達。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胡桑有關“沉默”的一些詩歌:
房間里的沉默,已無法應付警醒的白晝,
空氣中充滿力量。地平線在遠處守候。
那永遠的休憩近在咫尺,又遙不可及,
逐漸地,他放松了肌肉,等待命運的注射器。
——《失蹤者素描》,2013
那時候,我們需要打開自己進入生活,
命運卻超過了我們,禁止贖回那些沉默。
——《那些年》,2012
烏鴉的叫聲掘開一個封閉的異鄉,
言辭并不多余,不能由沉默代替。
——《空柵欄》,2012
作為一種無聲的經驗,沉默處于語言表達停止的地方。在胡桑的詩歌中,沉默被各種壓力所塑性,諸如“警醒的白晝”、“封閉的異鄉”與作為生活的“命運”,它是一種柔性的姿態,包含著無奈與接受。但柔順不是逆來順受,因為它同樣會以詢問與反思的方式召喚著語言的賦形,“言辭并不多余,不能由沉默代替”。沉默之于胡桑,其實是為語言留有余地的一種態度,這也讓蘊含著沉默的言說具有了傾聽的能力,能夠接受他者的進入。胡桑并不想把黑暗容納到了自己的文字之中來,而是希望借此打開語言的枷鎖,讓其能夠持續地對黑暗持開放態度。與此態度相關的是,胡桑并不輕信于自己的語言,他會在語言的使用中同時安置語言的界限,從而將意義指向語言之外——因為要在語言中找出沉默,并對其為什么會沉默作出思考,這顯然超越了語言所能承載的,至少超越了詩歌的語言所能承載的。詩歌能做的只是將意義指向這些沉默,從而讓自身變得及物。與此觀點相應的是,胡桑并不熱衷于在自己的詩中搞各種文字實驗,在當代詩壇,他的詩歌在形式和文字層面都不算獨特,因為對他而言,語言顯然并非詩歌所要重視的唯一內容,也正因為如此,也讓他的詩歌能遠離了當代詩壇“語言的天花”(歐陽江河語)疾病的傳染。
胡桑讓詩歌變得及物,從另一側面也是對詩歌對話功能的恢復。詩歌之于他不再是一個以審美為核心的文字自足體,而是成為了與他者相互關系中的一種題贈與交流的方式。這種交流首先體現在胡桑詩歌的篇名與題記之中,在這里常會出現所贈之人的名字,如《云——給金霽雯》、《葉小鸞——致蘇野,兼贈茱萸、葉丹》、《與鄭小瓊聊天》、《與藏馬對飲衡山路至晨》等等,這既可以被理解是他對傳統詩歌酬唱傳統的嫁接,也可以理解是他力圖讓詩歌變得及物的努力;其次體現胡桑在詩歌中對“疼痛”一詞的使用,他者(包括黑暗)以疼痛的方式被納入記憶,我們可以看幾組他的詩歌:
數個世紀的灰燼,坍塌于歲末的心臟。
一枚無法被時代消化的結石,停留在思想的
膽汁里,無法令空氣中的影子寧靜下來,
所謂犧牲,就是見證疊加在一起的疼痛。
——《疊影儀》,2011
表達提前到來,甚至不能感知,但它必須
被刺破。沒有疼痛,就沒有閃現的過去。
——《褶皺書》,2009
疼痛一詞在胡桑這里,是一個能夠容納現實感受力的容器。感到疼痛即意味著自身的打開,就書寫黑暗的層面而言,如果說沉默是在語言層面的打開,那么疼痛就位于這層打開之后,通過語言指向對現實感受力的恢復。感到疼痛伴隨著對邊界的觸碰,無論是以“無法被時代消化的結石”的方式、還是“閃現的過去”,它的另一端都襟連的是未知的區域,可以是對人,也可以是對事件,對每一個未知他者的觸碰都會帶來一種新鮮的感受力。沉默是讓語言接受異質,而疼痛則是讓生活感觸到他人。然則胡桑并沒有把現實中與他者的關系看做是詩歌表現的終極,而是把它也當做一個維度被納入到了文字之中。他所要召喚的疼痛是與“思想”、“表達”、“過去”等詞語相連接的,這也使疼痛具有了粘合的功能,它可以被看做是在時間、語言與現實等問題之間尋找新的結合點的嘗試。此舉也進一步打開了胡桑詩歌的疆域,同時讓他的特點更加明顯:即不囿于語言、不拘于現實,亦不礙于時間,而是將一切思考都推向邊界,從邊界審視周圍各種關系中難以理清的糾葛,如光明與黑暗、可見與不可見、言說與沉默、語言與現實等等。
胡桑致力于用詩歌將其中的各個層面的邊界磨得更加纖細與鋒利,因為只有當邊界更加纖細之后,位于它身邊更多的側面才能被展現出來,其視野也會變得更寬,能夠欣賞到菱形各個層面折射出的美麗。他致力于擺脫每一個單面意義的囚禁,從而與其他被隱匿在黑暗之中的可能性相遇,這種寫作的方式是包容性的,它總是朝向未知,并不把自己所開掘出的任何一面看做是意義的唯一基礎。因此,胡桑的詩歌總是向外張望著的,他的命名并不賦予意義,而總是指向隱藏在命名底下的意義糾葛,指向他自己為這些意義進行命名的惶然的態度與過程。然而這種向外張望也是辯證的,它在給了胡桑惶然的同時也給了他能夠分辨的視角與能夠書寫的勇氣,如他自己在詩中所表達的那般:
已經習慣于被囚的處境了,但仍要
向內張望,索引不可見的事物,離開此地,
就是永遠棲居于此地,窮盡它的可能性,
在瞬間抵達永恒,用清晰的繩子綁住混亂。
——《反諷街》,2011
胡桑借助于對黑暗的探索切入混沌的“現在”時間之中,但這種混沌的“現在”時間畢竟還是過于抽象,它需要被外化于一系列我們現代人所接觸到的生活意象來表達出來。而當代詩,無論中西,都塑造出了一大批的當代意象出來,而這些意象也成為了當代詩之所以能稱為“當代”的例證所在。在胡桑的詩歌里,這些當代意象亦是比比皆是,但不同的是,他會捻取很多當代詩人極少使用的意象入詩,比如抽水馬桶、(公園中的)菖蒲、自行車、超市、菜市場、街區等等。意象截取的不同也能看出詩人對“現在”不同的探索方向,許多現代詩人會在工廠、商業街、麥當勞等意象上著力良多,因為相比于其他,這些意象更能代表我們所處的“現在”環境。這種截取蘊帶著一種典型化的努力,而胡桑似乎并不想去追求這種典型化的東西,他所截取的意象更加生活化,因為這些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會遇到的東西。這種截取方式在當代詩歌中算不上是非常罕見,卻算得上是非常冒險,因為稍不留神就會變成索然無味的口水詩。
但胡桑的寫作畢竟與口水詩有著參商之隔,他并不像后者那般對一切宏大的東西深惡痛絕,在胡桑的詩歌里一些宏大詞匯也時常可見,諸如命運、世界等等。胡桑似乎并不想如口水詩人那般陶醉于某些破碎的現代意象之中,在宏大詞匯的碎片之中宣泄著狂歡的情緒。如上所述,在胡桑這里,詩歌的角色并非是個書記官(無論它所面對的名曰“內在”還是“外在”),而是去探摸邊界的一雙手,而界限所意味的并非只是驅離,更是另一種方式的連接。胡桑致力于在散碎的意象和宏大的詞匯之間搭橋,用文字去承載這小與大之間的震蕩。因此,他的詩歌帶有著鮮明的哲學意味,從而區別開了口水詩對生活的濫用。我們可以先看胡桑的一首詩:
研究老人,比如性欲與自殺,禮物和
秩序。也許,我們并不相信
真的有傲慢。你看,時間只教會了順從。
不過,這到底是平和,還是無奈的妥協?
命運如同癌癥迫使一個人努力變老,
是啊,窘迫的生存讓一切變得多余。
不需要憐憫,我們無須變成自足的哀悼者,
只有徹底陷入生活,才觸摸它殘忍的裂隙。
請向自己問更多的問題,讓生活超越我們。
此時,每一條微信都在懷疑自己,
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失蹤在希望的門口。
我愿意做一個熟睡的人,等待被陽光喚醒。
——《閑談》,2012
或許在一些口水詩人看來,這首詩的立意本身就過于宏大,但這恰恰是胡桑詩歌寫作風格的一個體現。這首詩的切口其實非常微小,就是在日常的聊天中,詩人和朋友談及對老人的看法,然后在這細微的事件中與宏大相遇,即命運、生活與希望。在這里,命運是作為生活中窘迫一面的載體出現的,它包含著不得不如此的“無奈的妥協”,對此,胡桑期待的是一種“理解之同情”(王國維語),目的是要“陷入生活”并使“讓生活超越我們”,以便讓生活去穿越不得不如此的窘迫而去叩敲希望之門——這就為普通而細微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質感,這是一片堅硬卻并非不可改變、希望深駐卻又不易開掘的區域,因此,命運不再因僵硬而變得讓人厭惡,希望也不再因空虛而變得廉價。命運將生存者拋入生活之內,而希望又使他對生活有所游離,而“生活”就處于二者的張力之間,也讓此二者變成了一對相互生成的鏡像。也正是因為對“命運”的重視,“生活”與“希望”在胡桑的詩歌中脫離了宏大詞匯所帶來的說教感,而是以問題的出現,并在這些詢問中探訪新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的細微和詞語意義的宏大之間,胡桑用不間斷的探訪與徘徊的方式完成了對二者的連接,這也讓他的詩歌充滿了內在的警覺。
這也是一種通過“陷入生活”為“現在”提供質感的嘗試,胡桑并非僅僅是要為讀者還原出一片所謂“真實”的生活樣態,而是想將他們邀請進混沌的世界之中去,并嘗試為生活中那片未知的區域賦形。宏大詞匯也正是來源于這賦形的過程之中,它是借詞語為混沌的生活擺上希望的路標。混沌的“現在”需要這希望賦予意義,以便為我們被命運所糾纏的日常生活復魅。也因此,詩歌便與賦形的行為變得相關,而不僅僅只是個語言事件。從胡桑詩歌中,我們也能看出一個書寫重心轉移的過程,即從“觸摸語言的質感”到“傳達黑暗的時刻”,這個轉變也蘊含著他所要發出的一個信息,即:“來,讓我們討論如何能夠更好的生活。”
對于“詩歌如何書寫現在”的問題,胡桑的詩歌并未提供答案,因為在他看來,自己詩歌中所呈現的黑暗、沉默與生活等諸多樣態,都只是構成“現在”的一些不同的側面,而“現在”本身卻是混沌未知的。而正是因為“現在”本身的混沌未知,需要對這些未知區域進行拓展,才會讓“詩歌如何書寫現在”的問題變成了“在現實中如何生活”的問題。詩歌并不負責為生活提供答案,它只是將存在感變得更重。因此可以說,面對“詩歌如何書寫現在”的問題,胡桑的貢獻并不在于為問題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答案,而是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指向,從而讓這個詢問變得更加深入。
?Giorgio Agamben:NUDITI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3-14.
?Giorgio Agamben:NUDITI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4-15.
編輯/張定浩
在日常生活的細微和詞語意義的宏大之間,胡桑用不間斷的探訪與徘徊的方式完成了對二者的連接,這也讓他的詩歌充滿了內在的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