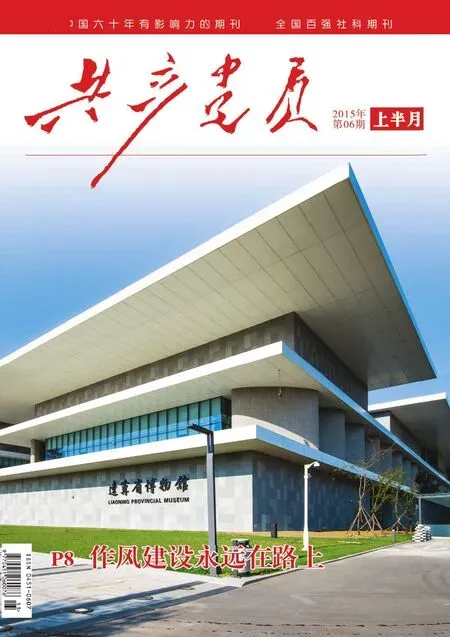“炎黃”之崇高
文/岸石
20多年來,張紀清捐款金額只有3萬多元,數目難稱巨大,但他只做好事不留名的崇高行為,卻是充滿正能量的巨大精神財富。令人倍感欣喜的是,越來越多的人爭做“炎黃”,接過了傳遞正能量的接力棒。

張紀清高舉“感動中國”2014年度人物獎杯
2015年2月下旬,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2014年度人物評選揭曉,江蘇無錫江陰市的退休老人張紀清高票當選。張紀清74歲了,改革開放初期,他在鄉里從事養殖,靠辛勤勞動成為小有名氣的萬元戶。算不上大富大貴的他熱衷捐款,樂善好施而又不愿揚名,“潛伏”行善。1987年6月,他以“炎黃”的名字匯款1000元,資助正在籌建的江陰祝塘敬老院,這筆錢當時是一個普通打工者一年的收入。此后,他年年以“炎黃”等名字向祝塘敬老院匯款,還給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捐錢,資助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的孩子上學。
20多年來,張紀清累計捐款3萬多元。僅從數字看并不算多,但衡量善心也不應光看數字,更要看捐獻者奉獻的心力、體現的精神。張紀清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走過青年、中年,進入了老年,“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丁”,普普通通一個人。但這位普通人有寬廣的胸懷和高遠的精神境界。為什么做好事卻隱姓埋名?張紀清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我們都是炎黃子孫,不敢以恩人自居。”張紀清的精神境界有著美學意義的崇高,別人欣賞,肅然起敬;他自己在默默奉獻中,也自我肯定、自我實現,感受到了信念的價值和生活的樂趣。
隱身的傳奇
張紀清經常化名“炎黃”捐款,“炎黃”的名聲愈來愈大,他自己倒有點默默無聞。20多年前,署名“炎黃”的捐款就引起了注意,有位熱心的鄉干部曾按匯款人的地址尋找,可街、路找到了,門牌號竟子虛烏有。此后,“炎黃”的捐款時有出現,“炎黃”的身份卻成了一個謎。“炎黃”不停做好事,越來越受人們尊敬,人們熱切盼望找出真人。為了弘揚這種奉獻愛心、幫助他人的精神,上世紀90年代,祝塘鎮就建立了“炎黃”陳列館。2007年,“炎黃”陳列館搬遷到祝塘鎮文化服務中心,當時許多人都希望尋找了多時的“炎黃”能在陳列館落成典禮上現身。可張紀清很沉得住氣,沒承認自己是大家尋找的“炎黃”。他曾以“炎黃”的名義用公用電話聯系過《江陰日報》,稱自己只是普通人,做了應該做的事,大家的好意他領了,希望大家不要再繼續尋找他,他會繼續這樣做下去。在陳列館不大的空間里,記錄了人們尋找“炎黃”的歷程。一張寄自云南迪慶的明信片上這樣寫道:“‘炎黃’叔叔,你好!收到你的資助款,我如魚得水在知識海洋里遨游,我現在代表全家向你表示萬分感謝。因為家里貧窮,無力供我再學,多虧你給了我一次上學的機會,使我重新回到學校續學。”與明信片一起寄來的還有一張孩子的照片。這樣的感謝信,陳列館里收藏了厚厚一疊。從1998年起,“炎黃”陳列館就成為江陰市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年都有不少人來這里聽“‘炎黃’故事”,學“‘炎黃’精神”。
張紀清本不打算現身了,他的初衷也不是先隱蔽一段,再來個真相大白;他也沒有準備一旦身份暴露,面對鋪天蓋地的好奇心,該怎樣應對。然而,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2014年11月,張紀清在給云南魯甸災區匯去1000元善款后,突發腦梗暈倒在郵政儲蓄銀行。人們救助時發現他身上有三張寫著“炎黃”和“黃炎民”字樣的匯款單據,這個讓人們感動和牽掛的好心人“炎黃”,終于曝光了。這讓張紀清懊惱不已。當時天氣很悶,他坐出租車時就有些不適,到銀行匯完款就感覺支撐不住了,而錢包里沒有“歸檔”的三張匯款單竟由此成為民警發現“炎黃”身份繼而聯系其家人的線索。
“眾里尋他千百度”,病愈出院的張紀清,自然成了媒體追逐采訪的對象。說起用化名和假地址,張紀清解釋說,是怕讓人找到。既然選擇了幫助人,就別想著留名,這樣也就不會給被資助人造成心理負擔了。
一個平凡人,熱衷做好事而不圖回報,不想揚名于世,不為私利,不滿足私欲,精神世界多么寬廣!人們欽佩這樣的高尚。當然,看問題不應絕對化,高尚也有不同的風格。建功立業可以崇高,高調行善也可以崇高。張紀清在內心世界體味崇高,不求社會聞達,自有其審美的愉悅。他說自己“做的都是些小事,無非是堅持的時間長一點而已”。社會的正氣和因緣際遇使他感動了中國。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如果不是湊巧,“炎黃”的光彩也不一定落到70多歲老人身上。如果永遠埋沒,張紀清虧不虧呢?張紀清的行為早就解答了這個疑問。做好事而不留名,內心自有境界高遠,欣賞自己、肯定自己的情懷。在與熱切尋找“炎黃”的官方、群眾的互動中,也自有崇高的感覺。有名望是一種崇高,隱在人群中體味自己精神世界的博大,也是一種崇高!
博大的精神
站在頒獎現場,張紀清敘述自己幾個月大時就失去親生母親,由祖母和繼母養大。她們雖然沒上過幾年學,但懂得中國傳統文化,經常教導他兩句話:“長大以后好好做人,好好做事。”“我是放牛娃出身,吃過的苦我心里最清楚,是國家和社會讓我過上了好日子,我想把這種感恩化作實實在在的行動。”在這次“感動中國”人物評選頒獎典禮上,老人誠懇地發出呼吁:“千萬不要忘掉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后代,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一定不能丟!”
改革開放初期,張紀清頭腦靈活,搞起了地鱉蟲養殖。孵化幼蟲、喂養飼料,成熟后曬干、銷售,既要付出辛勞,也得有點技術。富起來了,他既感激當時的富民政策,又對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點不滿,很多人一心向錢看,為掙錢甚至不擇手段。他熱衷捐款,就是要以行動告訴人們:“不要眼睛只盯著錢。”
張紀清在家里保留著厚厚的一疊匯款單據和包裹單,上面大多寫著“炎黃”“黃炎民”等姓名。不僅捐款捐物,熱心助人的“傻事”,張紀清也隨時隨地都做。有一次他到上海出差,碰到了落魄的殘疾人夏福根。一番攀談,張紀清聽說夏福根家里還有個雙目失明的老父親靠他供養,這次到上海是專程看風濕病的,可又缺錢又沒地方住。張紀清聽了他的遭遇后,就帶他到江陰找著名中醫治療。夏福根來到江陰,在張紀清家里住了一個星期,病情好轉了。張紀清和夏福根成了摯友,后來夏福根家里建新房,張紀清匯去了5000元。
張紀清退休后,每月收入微薄,但捐款捐物還不停,錢從哪來?就得靠全家人的支持:每年春節,子女都會孝敬他幾千元;老伴的退休工資也被他支取了不少。家人也知道他經常做善事,卻不知道“炎黃”就是他。幾十年來,他捐款做好事,積蓄少了,從大房子搬進了小房子。張紀清覺得自己的付出非常值得。“以前我是‘萬元戶’,但不少人還不富裕,我有能力幫助別人;現在我把賺來的錢差不多都捐掉了,成了‘無元戶’,但看看周圍,大家都富裕了,這樣的‘無元戶’我做得也高興!”
俄國19世紀的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過:“要是一個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獻給一種道德追求,要是他擁有這樣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這方面和這個人相比起來都顯得渺小的時候,那我們在這個人的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張紀清幾十年追求民族精神文化的崇高,行為細小而目標遠大,不圖揚名而默默體味奉獻的崇高和莊嚴,這是很令人欣賞、向往的人生!
高尚的能量
多年來,江陰曾數次興起尋找“炎黃”的熱潮。上世紀90年代中期,江陰專門進行了為期數月的大討論。“炎黃”的事跡曾被不少媒體聚焦,中央電視臺《走遍中國》欄目曾專程到江陰拍攝了專題片《誰是“炎黃”?》。江陰人幾度尋找“炎黃”無果,他們逐漸讀懂了“炎黃”不愿拋頭露面的心思,尊重其意愿,不再刻意尋找,紛紛把尋找“炎黃”變成了學習“炎黃”的自覺行動。“炎黃”的善行,吹起了這座城市慈善事業的一縷清風,越來越多的普通市民成了“炎黃”的同路人。樂善好施不留姓名的“新炎黃”在當地層出不窮,江陰也因10萬青年志愿者遍布各地而被譽為“志愿者之鄉”。祝塘敬老院是“炎黃”首個捐款資助的單位,在敬老院的賬本上,記載著歷年捐款捐物的數字。除了“炎黃”、黃炎民這兩個張紀清化名捐款的記錄外,還有署名“炎黃姑娘”“另炎黃”等受“‘炎黃’精神”影響的愛心人士捐款。學“炎黃”、當“炎黃”的風尚在江陰蔚然成風。從2008年至今,江陰市紅十字會共收到匿名捐款80筆,總額12.8萬元。在市慈善總會的日常捐贈本上,僅去年的記錄中就有15筆為“隱捐”。
越來越多的人做善事、好事不留名,只求奉獻于民族、社會,看到“炎黃”代表的正能量被社會認可,張紀清頗感欣慰:“我也是為了拋磚引玉,想著能有更多的人關注做好事而不是我這人。”生活需要物質財富,張紀清也并非不食人間煙火,但他崇尚儉樸,衣食無憂,成為他能熱心捐助的前提。在化身“炎黃”的年年歲歲中,張紀清開拓了自己的精神境界。他不求多么富裕,卻追求精神的浩大廣遠,體驗崇高的神圣和莊嚴。他的人生價值體現在對社會風氣、民族精神的一份貢獻,其崇高自會震撼人心,令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