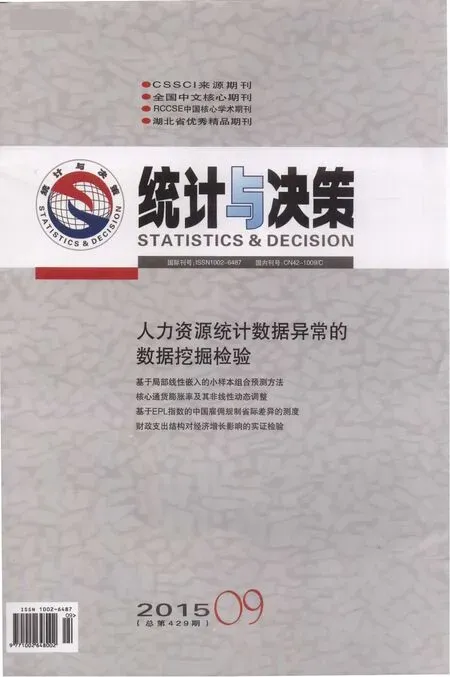關于不確定情形下多種選擇模式并存的解釋
孫 磊,林婧媛,2
(1.北京大學 匯豐商學院,廣東 深圳 518055;2.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北京 100005)
0 引言
期望效用理論和前景理論由于能夠解釋實驗和實證中的眾多現象而被廣泛接受和應用。但是,這兩種理論是基于解釋主流選擇模式而提出的。盡管有時可以通過改變模型參數等方式解釋其他選擇模式,但更為普遍適用的模型應當在解釋每種選擇模式的同時,能夠解釋多種選擇模式并存這一現象。特別是在多種選擇模式穩定出現在人群中,且占比不可忽略時。從這個角度來說,傳統模型具備改進空間。
本文將通過區分經濟參照點和心理參照點,構建同時包含這兩類參照點的雙重參照模型來描述人們對具有一定概率分布形式的前景的預期效用。
為了證實在具有預期的不確定情形下,雙重參照模型對選擇模式描述更為準確,本文通過實驗來檢驗當未預期部分固定而真實收益或損失變化時人們的選擇偏好模式。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容易觀察到兩個因素之間的權衡現象和人們的選擇傾向:更注重經濟收益或損失的人群傾向選擇經濟狀態變動最大的選項為最愉悅(收益情形)或最郁悶(損失情形);更注重心理落差的人群則更傾向選擇經濟狀態變動最小的選項為最愉悅(收益情形)或最郁悶(損失情形)。因為當未預期部分固定時,最小真實收益或損失意味著未預期部分占比最大。當觀察到多種選擇模式以不可忽略的比例出現時,前景理論和期望效用理論都無法解釋,而如下的雙重參照模型可以解釋此情形下的多選擇并存現象。
為了更容易觀察到人們的選擇模式,實驗采取了最簡單的情形:即預期為單點分布的情形。通過直接告訴被試他們的預期,避免不同被試對情境的不同解讀。盡管如此,實驗的結論可以推廣到預期是其他分布形式的情境。由于本模型效用函數可以抽象為:

其中V是總效用,pi是xi實現的概率,v是預期為x而實際實現為 xi的效用,x是關于(pi, xi;pj, xj;…)的函數。這里為了簡單起見,我們用相應的概率直接作為權重。可以看出,盡管更為普遍的情形是事件預期呈多點分布或連續分布,總效用仍可以表示為v(xi,x)的加權求和形式。因此,一旦闡釋清楚單點分布的情形,模型可以容易推廣到更為普遍的情形。
1 模型和理論
參照點是前景理論中的核心概念,最終結果通過與參照點對比而出現收益或損失,從而產生效用。然而前景理論并沒有系統闡明參照點是如何確定的。雖然參照點的確定或多或少與具體的情境有關,但是傳統理論潛在假設是一個事件中只有一個參照點。在這樣的假設下,人們應當具有相同的選擇模式,而這與絕大多數實驗是相悖的。即便是Bowman和Bell的模型及基于此的一些變形,由于使用了絕對落差來度量心理效用,從而無法解釋:當絕對落差一致時(如上述例子中均為500),對數值尺度不同的多種情境(如上述例子中的1500和5500)進行選擇時,為何會出現不同的選擇模式。
1.1 經濟參照點和心理參照點概述
經濟參照點為度量經濟狀態的變化提供參照標準,通過最終經濟狀態(比如財富值)與初始經濟狀態(即經濟參照點)的比較來衡量經濟狀態改變帶來的感受。典型的經濟參照點是前景理論中的“現狀”和期望效用理論中的“零財富狀態”。我們通常選擇事件發生以前某個時點的客觀經濟狀態作為經濟參照點,由此得出的經濟效用是指對得到、失去或者持有金錢的感受。
心理參照點通常指對一件事情結果的預期。當所得或所失超過預期時,會增強感受;當所得或所失低于預期時,會削弱甚至反轉感受。增強、削弱和反轉的效果的強弱是由未預期部分占真實結果的比例來衡量的。心理參照點可以是真實存在或者想象的,但有一點假設很重要:心理效用不能脫離經濟效用而單獨存在,一旦經濟效用為零,不再討論心理效用。該假設并不認為經濟狀態不改變的時候人們就毫無情緒變化。該假設僅僅意味著此時人們的感覺不再與經濟相關,因此不是本文所討論的范疇。
經濟效用和心理效用的區別不僅體現在概念(分別與經濟參照點和心理參照點進行比對)和作用機制(絕對數值大小和相對比例大小)的不同,也體現在作用時效的差異。Levy和Wiener指出:當初始財富為w且某事件帶來x的財富增加,則效用函數為U(w ,x)=U(w)+Vw(x),其中U(w)刻畫的是長期效用,而Vw(x)刻畫的是短期突然的或未預期到的效用。Ryder和Heal(1973)指出參照點rt=αct-1+(1-α)rt-1,α∈(0,1),即預期消費水平rt是由上一期的預期消費水平rt-1和實際消費水平ct-1決定的,α刻畫了參照點調整的快慢程度。可見,長期而言我們的參照點會不斷修正以接近真實情況,從而心理效用的作用會逐漸減弱。在雙重參照模型中,我們也認為經濟效用是相對長期、穩定的效用;而心理效用描述的是相對短期、易于變遷的效用。
1.2 基本情形:可能出現的結果為單點分布
首先關注最簡單的情形:可能出現的結果是單點分布的。假設:預期事件發生后會產生x單位的財富變化(x>0時,收益;x<0時,損失);事件真實發生后的財富變化為(x+a),其中a是最終結果和預期的差距。此種情形在現實中非常普遍,因為我們難以準確預計未來發生的事件,同時現實和預期的差異會影響效用。
根據現實經驗和實驗結果,假設有兩方面的因素會對效用產生重要影響:經濟狀態的真實變化(x+a);未預期到的變化a與真實實現的變化(x+a)的相對大小,即比值a/(x+a)。這兩個因素也是最終真實結果同兩個參照點之間的對比結果。正如上文所述,這兩個因素的作用是不同的:前者衡量的是經濟效用,是感知的基礎;后者衡量的是心理因素的影響,是經濟效用的放大(或縮小甚至反轉)因子。據此,我們提出的效用函數是:

其中v(x ,a)函數衡量的是總效用,v2(x+a)函數衡量的是真實經濟狀態變化的效用,而v1(a/(x+a))函數衡量的是心理效用部分對經濟效用的影響。顯然,當未預期部分a相同時,真實結果(x +a)越大的時候,經濟收益越大,從而經濟效用v2(x +a)將越大。但同時心理變化a/(x+a)將越小,心理效用越不顯著,從而v1(a/(x+a))越小。由于不同人對這兩個因素的相對重視程度不同,因而在該模型框架下,人群可能出現的不同選擇模式。
v1(a/(x+a))函數刻畫了未預期部分對經濟效用影響的方向和程度。當(x+a)為定值而|a|增加時,即實際實現的結果固定,而結果中的未預期部分增加時,心理效用的增強作用會變大,從而v1(a/(x+a))是增函數,以下分定義域區間討論v1(a/(x+a))的值域。
(1)0<a/(x+a)<1( 即 x,a>0或 者 x,a<0)時 ,v1(a/(x+a))>1。所得或所失超過預期,從而心理效用v1(a/(x+a))會同向增強經濟效用v2(x+a)。
(2)a/(x+a)=0(即a=0,x≠0)時,v1(a /(x+a))=1。這是傳統的前景理論描述的情形,預期與真實結果完全一致。因此總效用取決于經濟效用部分的大小,心理效用對經濟效用沒有放大或縮小等扭曲作用。
(3)a/(x+a)>1(即 ax<0,|x|<|a|)時 ,v1(a/(x+a))>v1(1)。預計有收益而實際為損失,或預計有損失而實際為收益。此時心理效用會對經濟效用產生增強效果。
(4)a/(x+a)<0(即ax<0,|x|>|a|)時,v1(a /(x+a)) <1。所得或所失少于預期,當a/(x+a)與0比較接近時,心理效用會削弱經濟效用,但并不會反轉經濟效用的方向。當|a/(x+a)|足夠大時,心理效用產生的作用超過經濟作用,從而在收益情況下出現負效用,損失情況下出現正效用。
(5)a/(x+a)=1(即x=0,a≠0),在毫無預期的情況下獲得收益或遭受損失。這是a/(x+a)正向和負向趨近1時的極限情況,v1(a/(x+a))函數在此處連續。

圖1 心理效用函數v1(a/(x+a))示意圖
v2(x+a)函數衡量的是實際經濟狀態的變化產生的效用。由于前景理論在處理不確定情形下人們的選擇模式方面有更廣泛的應用,且雙重參照模型中明確區分了收益和損失的情形,我們認為v2(x+a)函數與前景理論(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效用函數一致。

擴展模型:可能出現的結果為一般分布
可能出現的結果為單點分布是非常普遍且簡單的情形,但更為一般的情況是可能出現的結果呈現多點分布或連續分 布 。 對 于 前景(x1, p;x2, q;x3, 1-p-q),假 設x1≤x2≤x3并且最終實現的結果是x2,則當將x2與x1作比較時會感到愉悅,而將x2與x3作比較時會感到郁悶。當p增加的時候,開心程度增加;而(1-p-q)增加的時候,郁悶程度會增加。可見每一個可能結果及其概率均會影響最終效用。
假設每一個結果及其概率是通過影響對事件的整體預期而影響最終效用的。由該假設可知:可能結果為多點分 布 (x1, p1;x2, p2;…;xn, pn)時 ,形成的預期為x預期=x預期(x1, p1;x2, p2;…;xn, pn);可能結果為連續分布時,假設可能結果x∈(m,n)且其概率密度函數為g(x),則形成預期為x預期=x預期(x,g(x)|x∈(m,n) ),結果xi真實發生時的效用為:

以上兩種情形衡量的是事件發生后的效用。但是當對不同前景進行選擇的時候,要對效用進行預測。在事件發生前,若事件可能結果呈多點分布,為簡單起,我們使用對應的概率直接作為權重,則預期的效用是:

如果事件可能結果呈連續分布,則預期的效用是:

2 實驗和結果
2.1 實驗思路和樣本質量
我們期望通過實驗來驗證當固定未預期部分a而變動最終實現的結果(x+a)時,人們對心理效用和經濟效用存在權衡現象。從而證明這兩方面因素會對效用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選擇模式。同時,實驗調查了被試的基本屬性(如年齡、性別、職業、教育程度、月收入、月消費等),以探究不同組別選擇模式的差異。
為控制樣本質量,問卷發布在全國最大的在線調查平臺之一問卷星上。調查共收回205份完整問卷,且被試報告在此之前從來沒有做過任何類似問卷。被試的男女比例為1.11:1,83.9%的被試在20-40歲之間,69.76%的被試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且被試的月收入及消費水平處于正常分布。
2.2 實驗過程
實驗包含21個問題,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調查被試的基本個人信息(年齡、性別、職業、教育程度、月收入、月消費);第二部分是主體實驗部分,被試在這一部分將對不同選項按照愉悅或郁悶程度的不同而排序;第三部分驗證被試在第二部分是否正確理解題意并認真作答。
第二部分的主體實驗部分包含四個問題,關注最簡單的二重參照情形:可能結果為單點分布且ax≥0。一方面在這種情形下更容易探究被試關注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這是其他復雜情形的基礎。我們通過固定a而變動(x+a),使得a/(x+a)和(x+a)反向變動,而v1(a/(x+a))和v2(x+a)均是全定義域上的增函數,從而v1(a/(x+a))和v2(x+a)會反向變動,由此可以觀察人們是否存在不同選擇模式,驗證模型的準確性。
第三部分首先讓被試識別在第二部分選擇時,是否受到最終真實結果、未預期部分與真實結果的比值這兩個因素的影響,我們將此過程稱為訓練過程。如果被試完全理解題目關注的是事件的整體效用,則這兩個回答是肯定的。經過訓練過程以后,被試能夠注意到這兩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從而我們再次詢問與第二部分完全一樣的問題,如果被試對各選項的排序有變而在訓練過程中報告注意到了兩方面的因素,則第二部分的排序缺乏可信度(因為沒有理由在完全理解題意而認真作答的情況下,迅速改變答案):或者他們在訓練過程給了非真實答案,或者他們在第二部分沒有認真作答。通過這一部分控制問卷質量,剔除未完全理解題意或隨意作答的問卷。
2.3 結果
2.3.1 總樣本結果
如上所述問卷的核心部分是包含四個問題的第二部分,包括收益情形和損失情形各兩個問題,為避免選項順序的干擾,問卷設置了選項順序隨機出現。以下展示收益情形的兩個問題,損失情形與之完全對應,僅將“得到”改為“損失”,將“愉悅”改為“郁悶”。后續結果及處理部分如未作說明,使用的都是訓練前后對應問題選擇或排序完全一致,且在訓練過程中報告注意到兩方面差異的子樣本。
問題7:請假設以下四種情形真實發生在你身上,請就事件的整體愉悅程度(注意是整體而非單指變化過程的愉悅程度)從高(相對最愉悅)到低(相對最不愉悅)排序:
A你得到了500元錢(你原本預計得不到任何錢);
B你得到了1500元錢(你原本預計得到1000元錢);
C你得到了2500元錢(你原本預計得到2000元錢);
D你得到了5500元錢(你原本預計得到5000元錢)。
問題8:上題四個選項讓你產生的愉悅程度有無差異?
A有差異;
B無差異。

表1 三種主流選擇ABCD、DCBA和ADCB的主導因素
對于選擇“四個選項有差異”的人群,存在24種可能出現的排序方式,其中ABCD、DCBA和ADCB是占優且穩健的。特別是在結果最為可靠的訓練前后選擇模式一致且注意到雙因素的子樣本中,這三種選擇模式在所有報告四選項有差異人群中的總占比在收益情形和損失情形下分別為92.68%和97.33%。同時,被試在關于選擇原因的開放問題中提到未預期部分占總體的比例以及總體數額的大小這兩個因素最多。可見不論是選擇模式的統計數據還是被試的選擇原因都支持模型中的雙因素是主導人群選擇模式的關鍵因素。
對訓練前后選擇模式一致且注意到雙因素的人群進行Pearson卡方檢驗,統計值為6.04,低于臨界值7.78(α=0.1)。但仍可觀察到DCBA和ABCD人群占比在損失組中高于收益組,分別提高了6.10和4.07個百分點。此結果顯示相較于數值尺度相同的收益情形,損失情形更容易引起對不同結果的不同感受,且選擇模式更加向兩個主導因素分化(即ABCD和DCBA選擇模式)。

表2 “訓練前后選擇一致且注意到雙因素”組的選擇模式
2.3.2 分屬性結果
具體分析分樣本結果前,需特別注意的是,選擇模式的差異可能由兩類原因導致:對金錢的偏好程度;對意外事件的接受程度。任何組間差異是兩方面因素作用的綜合結果,我們僅能比較不同組別對兩方面因素的相對重視程度(即相較于因素1,組1比組2更加重視因素2),而不能比較針對其中單一因素不同組別的反應差異(即相較于組2,組1更加重視因素2)。
實驗結果顯示,除具體情境對人們選擇模式會產生重要影響,被試的個人屬性也會對選擇模式產生影響。為了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可比性,以下分析仍然采用“訓練前后選擇一致且注意到雙因素”組進行分析。同時,由于A選項非常特殊,在進行分析的時候,選擇對比BCD和DCB兩種選擇模式具有更普遍的意義。
男性在收益情境下選擇BCD、DCB的占比分別為52.50%、27.50%,損失情境下的占比分別為68.75%、28.13%。女性在收益情境下選擇BCD、DCB的占比分別為44.90%、44.90%,損失情境下的占比分別為42.31%、38.57%。相較男性,女性在收益和損失情境下的選擇模式更為一致;相較于經濟狀態的改變,男性組比女性組更在意未預期到的變化,這一差異在損失情境下更為明顯。

表3 分性別人群的選擇模式占比比較
30歲以上組在收益情境下選擇BCD、DCB的占比分別為57.89%、31.58%,損失情境下的占比分別為65.00%、27.50%。30歲及以下組在收益情境下選擇BCD、DCB的占比分別為41.18%、41.18%,損失情境下的占比分別為40.91%、40.91%。相較30歲以上組,30歲及以下組在收益和損失情境下的選擇模式更為一致;另一方面,相較于經濟狀態的改變,30歲以上組比30歲及以下組更在意未預期到的變化,這一差異在損失情境下更為明顯。
月收入和月消費代表被試經濟實力和消費傾向,注意到被試中12.20%人群是學生,因此月消費更能真實地反映被試的經濟狀態。同時,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817元/月,我們選擇2000元/月的月消費作為分組標準。較低收入人群在收益和損失情境下選擇BCD的比例為46.15%和47.73%,較高收入人群這一比例分別為51.35%和57.50%。雖然這一差異相較其他因素導致的差異并不明顯,但仍可見相較經濟狀態的改變,高收入組比低收入組更在意未預期到的變化,并且在損失情境下這一差距更為明顯。

表5 分月消費人群的選擇模式占比比較
以上描述性分析闡述了人群屬性對選擇模式的影響,但不能區分各屬性對選擇模式差異的貢獻程度。以下通過計量分析,對各屬性效果分拆。由于ABCD、DCBA和DABC占人群90%以上,我們僅分析樣本中的該部分人群。

表6 回歸模型中的變量及描述
總體回歸結果中,年齡(age)、教育(edu)和相對消費(Rconsumption)的系數不顯著,說明女性人群選擇模式與年齡無關,總人群選擇模式與教育程度及消費水平無關。年齡性別交叉項(ag)系數顯著,損失和收益情境下分別為0.0458和0.0663;損失情境下性別項(gender)系數顯著,為-1.684。即收益情境下男性相較女性傾向選擇BCD,且隨著年齡增大該性別差異更加大。損失情境下,在非常年輕的人群中,女性比男性更傾向選擇BCD。而當年齡超過25歲(1.684/0.0663)以后,該趨勢反轉,男性更傾向選擇BCD。這些結果與描述性分析是一致的:女性選擇行為在各年齡、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下一致性高;損失情境下,男性在25歲以前比女性更加注重經濟變化,在25歲以后更在意未預期變化的影響;收益情境下,各年齡男性均更在意未預期變化的影響,且隨著年齡增長這一趨勢更為明顯。

表7 回歸結果匯總表
分性別回歸結果與總體回歸結果一致,男性組的年齡項系數顯著且為正:進一步驗證了不同年齡組的男性選擇模式存在差異,隨著年齡增加男性更傾向選擇BCD。且這一傾向在損失情境下更為明顯。而女性各年齡段之間的選擇無差異。另外,損失情境下學歷對男性的選擇模式有影響:大學及以上男性相較大學以下男性更傾向選擇DCB,可能由于教育讓男性對未預料事件的承受能力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男性組損失情境下的回歸擬合優度為0.313以外,其他組回歸的擬合優度相對較低,特別是女性組的回歸擬合優度很低。這一方面說明女性的選擇模式比較統一,另一方面也說明除了這些可度量的屬性以外,還有其他因素深刻影響人群的選擇模式(可能的因素:成長經歷、價值觀念、家庭等)。
3 結論
本文通過對經濟參照點和心理參照點概念和作用機制進行闡述,區分了經濟效用和心理效用的不同:經濟效用是通過最終經濟狀態與初始經濟狀態進行對比而產生,衡量的是關于真實經濟狀態改變帶來的效用;心理效用是通過最終經濟狀態與心理預期進行對比而產生,衡量的是未預期到的變化對經濟效用的放大、縮小或反轉作用。心理效用大小和方向取決于未預期的變化占總體變化的比例。
本文提出心理效用與經濟效用通過相乘而非加和的方式得到總效用。這是因為心理效用不能夠獨立于經濟效用而存在,心理效用通過放大、縮小或反轉經濟效用而對總效用產生影響。并且僅在經濟效用不為零(即發生經濟狀態的真實變化)的情況下,心理效用才有討論價值。
本文由預期單點分布的雙重參照模型框架下的效用函數推導出可能結果呈多點分布和連續分布下的效用函數,使得模型一般化。
在實驗部分,通過人群基本屬性、主體實驗、訓練過程和驗證實驗,證實了在存在預期的情形下,被試基于真實經濟狀態變化和心理預期落差兩個因素做出選擇。多重選擇模式穩定出現在人群中驗證了總效用是兩方面因素權衡的結果。
在分屬性人群選擇模式分析中,我們發現女性人群中選擇模式不隨年齡、學歷、月消費等屬性的變化而出現顯著變化;而男性人群年齡越大,對未預期事件的反應越強烈,且這一傾向在損失情境中更為明顯。在年輕人群中,女性相較男性對未預期損失的反應更強烈,但這一差異隨著人群年齡增長而變弱并在25歲左右出現反轉。相較心理效用,男性大學及以上學歷者相較大學以下學歷者更注重經濟效用。在計量分析中月消費水平對人群選擇模式沒有顯著影響,但在描述分析中提示月消費2000元及以下群體在收益和損失情境下的選擇模式變化很小,且更注重經濟效用;而月收入2000元以上群體更注重心理效用,且在損失情境下更加明顯。這些結果提示我們男性、年齡較長、高收入的人群更加注重對事件預測的準確程度,特別是在損失情境下更加厭惡意外損失。
本文給出了模型中效用函數的一般形式和相關的實驗證實,但是沒有給出函數的具體形式,從而無法對效用函數的性質進行量化討論。同時本文的證據主要來自于實驗,缺乏實證分析。
[1]Tversky A,Kahneman D.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J].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1992,(5).
[2]Kahnemanand D,Tversky A.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a,1979,47(2).
[3]Bowman D,Minehart D,Rabin M.Loss Aversion in a Consumption-Savings Model[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1999,38.
[4]Bell DE.Disappointment in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J].Operations Research,1985,33.
[5]Stigler G.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
[6]Levy H,Zvi Wiener Z.Prospect Theory and Utility Theory:Temporary versus Permanent Attitude towards Risk[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2013,68.
[7]Helson H.Adaptation Level Theory:An Experimental and Systematic Approach to Behavior[M].Harper and Row:New York,1964.
[8]Rabin M.Psychology and Economic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8,36(1).
[9]Heal G M,Ryder H E.Optimal Growth with Intertemporally Dependent Preference[J].Rev.Econ.Stud,1973,40(1).
[10]Von Neumann J,Morgenstern O.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