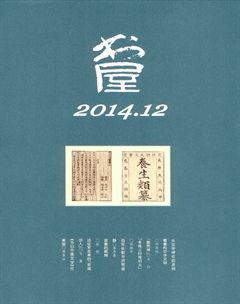老鼠與黃犬
夏立君
《史記·李斯列傳》開(kāi)篇寫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shí),為郡小吏,見(jiàn)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shù)驚恐之。斯入倉(cāng),觀倉(cāng)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jiàn)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結(jié)尾處如此寫丞相李斯之死:“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yáng)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zhí),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fù)牽黃犬,俱出上蔡?hào)|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秦朝是沒(méi)有詩(shī)意的,秦人是反抒情的,所有詩(shī)意都已被始皇、李斯們?nèi)∠6钋榈乃抉R遷還是給李斯保留了一點(diǎn)詩(shī)意——成功后又徹底失敗的李斯,死到臨頭唯一可再說(shuō)一說(shuō)的就是無(wú)法回去的田園生活。
為秦帝國(guó)也為一己生存奮勇搏殺的李斯,面對(duì)一幕又一幕兔起鶻落的驚險(xiǎn),有時(shí)會(huì)涌起故園之思,念起昔日楚國(guó)上蔡的田園生活,念起率領(lǐng)小兒、黃犬出上蔡?hào)|門追逐狡兔的情景。
回望來(lái)路,是如此清晰,但李斯明白,此生是回不去了。
那是一個(gè)取消一切回旋余地的時(shí)代。不僅有形的田園被取消,無(wú)形的精神田園也被徹底取消了;老鼠與黃犬,以它們靈敏的趾爪,爬搔過(guò)李斯的一生,使盡了鼠輩伎倆的李斯最終卻連黃犬田園也成妄想。
荀子有兩個(gè)著名學(xué)生:李斯、韓非。李斯助嬴政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成為千古一相;韓非將法家學(xué)說(shuō)推向極端,在秦朝幾乎被奉為圣人。荀子的這兩個(gè)弟子,有能量、能折騰。荀子以高壽善終,兩個(gè)弟子卻皆以慘烈方式謝幕。
荀子以人性惡為立論出發(fā)點(diǎn)。“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偽,即人為;人性是惡的,善是禮樂(lè)教化人為努力的結(jié)果。并且他說(shuō)“途之人皆可為禹”,只要設(shè)計(jì)好制惡路徑,人性雖惡,而善是可以期待的。荀子比主張性善的孟子多些對(duì)人性的洞悉,卻仍然信任人性。李斯、韓非那里,顯然把老師支撐門戶的某種東西弄丟了。
李斯那顆雄心,時(shí)時(shí)呼應(yīng)著騷動(dòng)不安的戰(zhàn)國(guó)天下。生死存亡是逼到列國(guó)眼前的現(xiàn)實(shí),激烈的思想交鋒令最后的士人坐立不安。荀子堅(jiān)持他的溫厚言辭,李斯心靈里卻早已戈戟森嚴(yán)。這個(gè)一無(wú)所有只有一顆雄心的士,念叨著“得時(shí)無(wú)怠、得時(shí)無(wú)怠”,急吼吼奔赴秦國(guó)去了。
荀子對(duì)這個(gè)弟子早就心存憂慮。《荀子·議兵》篇記載這樣一段師徒論辯。李斯說(shuō):“秦四世有勝,兵強(qiáng)海內(nèi),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李斯把秦朝累世強(qiáng)盛的原因,歸結(jié)為秦能做到“以便從事”,即怎么有利就怎么去做,只講目的,不擇手段。荀子大約生氣了:“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tǒng)也。……今汝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亂也。”荀子明言李斯重功利輕仁義是本末倒置,尖銳指出不可一世的秦兵其實(shí)是“末世之兵”。荀子看到,這個(gè)吱吱嘎嘎張牙舞爪的強(qiáng)國(guó),缺少支撐其遠(yuǎn)行的“軟件”,荀子能想到的軟件當(dāng)然只能是孔儒。聯(lián)系后來(lái)李斯及秦帝國(guó)的命運(yùn),不能不感嘆思想家的溫厚與深刻。空喊仁義道德的確常常無(wú)用,但將其公開(kāi)拋棄踐踏羞辱卻可能導(dǎo)致災(zāi)難性后果。
李斯、韓非正好就是這么干的。
嬴政極易傾向刻薄殘忍,可視為列祖列宗的“造化”及宮廷生活的培養(yǎng)。
有了李斯這顆“文膽”之助,嬴政對(duì)“武功”也更具信心,統(tǒng)一天下步伐大大加快了。從公元前230年滅韓,至公元前221年滅齊,十年滅六國(guó),滅人之國(guó)渾如探囊取物。一個(gè)空前的大帝國(guó)從六國(guó)廢墟上挺立了起來(lái)。可是,這是一個(gè)缺少潤(rùn)滑劑的帝國(guó),一邁步便吱吱嘎嘎。嬴政和李斯都不容易或來(lái)不及想到,帝國(guó)是需要“軟件”的。
能簡(jiǎn)化統(tǒng)一的都簡(jiǎn)化統(tǒng)一了,各項(xiàng)“事業(yè)”都在向始皇所追求的極致推進(jìn)。李斯適時(shí)登場(chǎng)了。“臣請(qǐng)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shī)書百家語(yǔ)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yǔ)詩(shī)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jiàn)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shù)之書。若欲有學(xué)法令,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jì)》)。與《諫逐客書》為外客士人張目的偉岸姿態(tài)相反,此“奏折”呈現(xiàn)的完全是刀筆吏嘴臉。作為實(shí)現(xiàn)輿論一律的根本措施,黑暗的“焚書坑儒”事件出現(xiàn)了。
統(tǒng)一不久,李斯晉升為丞相,是為千古一相,他所恐懼的卑賤之位被徹底擺脫。
始皇巡幸梁山宮,遠(yuǎn)遠(yuǎn)望見(jiàn)眾多車馬簇?fù)砝钏菇?jīng)過(guò)山腳,不高興了。宮中有人打小報(bào)告給李斯,李斯立即減少了車馬數(shù)量,自然又有人向始皇打小報(bào)告。始皇追查泄密者,查來(lái)查去無(wú)結(jié)果,便殺掉了當(dāng)時(shí)所有在場(chǎng)近侍。始皇無(wú)懼鬼神,惟迷信暴力。在這個(gè)血腥淋漓的帝國(guó),留下誰(shuí)、碾碎誰(shuí),看上去實(shí)在是一件偶然的事。李斯知道自己這個(gè)帝國(guó)二號(hào)人物是多么渺小了。
“黃犬之嘆”,那是司馬遷想象中的李斯的家園之嘆。
這真是一個(gè)“與傳統(tǒng)觀念徹底決裂”的時(shí)代。李斯、韓非,其思維就是斬草除根式思維。在秦朝,從體制到個(gè)人都絕無(wú)自省反省。這是一個(gè)廣泛閹割的時(shí)代。在極權(quán)統(tǒng)治者眼里,世界必須是一個(gè)閹割過(guò)的干干凈凈的世界,一張白紙沒(méi)有負(fù)擔(dān)的世界。韓非就極力想成為帝王閹割天下的手術(shù)刀,他因此先把自己徹底閹割。韓非之前,人是有逃避之路可走的。老莊是一種逃避,儒家獨(dú)善其身是一種逃避,退處巖穴也是逃避。貫徹韓非理論,所有人便欲逃無(wú)地。韓非對(duì)巖穴之士也大張撻伐,認(rèn)為那是對(duì)君王權(quán)威的蔑視挑戰(zhàn)。一個(gè)不許任何人有任何精神堅(jiān)守的體制,竟然迅速挺立在大地上,寒光凜冽,巍然赫然。沒(méi)有人能把當(dāng)作家園,它也不許任何人有屬于自己的家園。
沒(méi)有家園,只有叢林。英國(guó)人托馬斯·霍布斯于1651年所出版的《利維坦》一書中首次提出“叢林法則”概念。叢林法則下的社會(huì),弱肉強(qiáng)食,贏者通吃,沒(méi)有道德,沒(méi)有憐憫,只有冷冰冰的食物鏈,所有人都不惜以他人為犧牲。在秦朝,通吃是做到了,但傳之萬(wàn)世的通吃是不存在的。強(qiáng)者并沒(méi)有進(jìn)天堂。約在1515年,意大利人馬基雅維利將其叢林法則意味極濃的《君王論》一書獻(xiàn)給權(quán)貴,為了能讓統(tǒng)治者攫取、鞏固權(quán)力,馬氏可謂處心積慮。對(duì)比閱讀,卻不能不承認(rèn),《君王論》雖具無(wú)恥傾向,但其人文色彩、人性溫度遠(yuǎn)遠(yuǎn)高于《韓非子》。
不讀歷史,感到二千年很遠(yuǎn);讀了歷史,感到二千年很近。短促又悲慘的秦朝,像個(gè)驚嘆號(hào)一樣矗立在數(shù)千年皇權(quán)歷史的起點(diǎn)。接過(guò)皇帝稱號(hào)、秦氏體制甚覺(jué)受用的歷代帝王,卻無(wú)人能正視始皇和他的功業(yè),總是將他罵一罵、貶一貶以示自己正確。
黃犬,家園里的那條忠誠(chéng)的狗,你還記得你那位年輕的主人嗎?很可能,丞相過(guò)得還不如一條狗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