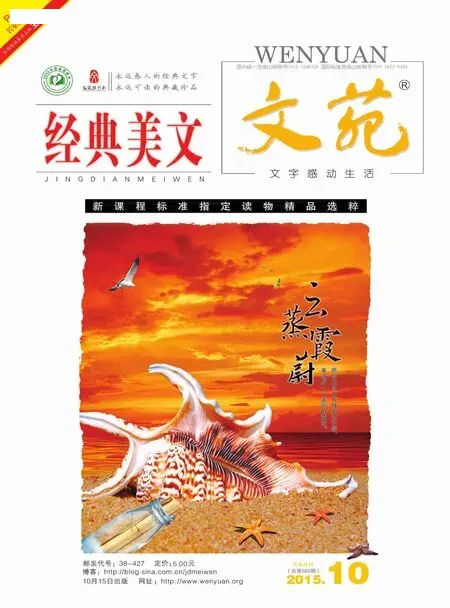魔書
[周 曼]
魔書
[周 曼]

奧本肖教授一直致力于心靈現象的研究。有一天上午,他對他的朋友法瑟·布朗神父說:“我是一個相信科學的人,我要用科學解釋一切心靈現象。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一封信,說一個人神秘地失蹤了。現在,我要用科學來解釋人的失蹤,這還是一個新課題。”教授若有所思地看了神父一眼,接著又說,“這封信是一位名叫普仁格爾的傳教士寫來的。他今天上午要來辦公室看我,中午請你和我們一起共進午餐,我把這件事的結果告訴你。”
“謝謝,我一定來。”神父說。
他們道別了。教授轉過身朝辦公室走去。辦公室不大,只有他的秘書布里奇和他在一起工作。當教授走進辦公室時,布里奇正在校對教授的打印報告。在這份報告里,教授正試著用科學解釋神秘的心靈現象。
“普仁格爾先生打來過電話嗎?”教授問。
“沒有,先生。”秘書機械般地回答道,然后又機械般地繼續做他的事。
教授面對著書房,說:“啊!對了,布里奇,要是普仁格爾先生來了的話,請直接把他領到我書房去,然后繼續做你的事,我想你最好今晚把我這份報告校對完畢。如果我明天來晚了,請你把它放在我的辦公桌上。”
教授走進書房,普仁格爾在信上說的事在他的腦海里浮現,他坐在舒適的大靠背椅上,拿出傳教士的信又讀了一遍。傳教士在信上說他知道教授對此類事件頗感興趣,并提出前來與教授進行探討。
教授抬起頭時,發現傳教士已來到了書房。
“您的秘書告訴我可以直接進來。”傳教士笑嘻嘻地說。很快,這種笑消失在他那濃密的、淺灰色的胡子里。他的鼻梁長得略扁,眼睛給人一種真誠友好之感。教授是一位相當有偵探能力的人,他一眼就可以看出一個人是老實人還是騙子。他仔細打量著這位來訪者,看他是個什么樣的人。但從普仁格爾面相上看,他沒有發現什么可懷疑的跡象。事實上,他很喜歡他眼睛里流露出的那種友好的微笑,因為在真正騙子的眼睛里是絕對見不到這樣一種微笑的。
“教授,我希望您不要認為我是在開您的玩笑,我只是把我的所見所聞告訴您,因為這是真實的,這一切都不是開玩笑,而是悲劇。我不必多說了,事情是這樣的:那時,我是森林茂密的非洲西部地區的傳教士。這個地區由一白人官員威爾斯船長管轄,我和他非常友好。我們短暫離別后的一天,他回到了我的帳篷,說有事要告訴我。他手里拿著一本舊書,旁邊放著他的左輪手槍和劍。他說這本書是船上一個人的,那個人說任何人不得翻開書,看其內容。誰要是翻開了,魔鬼會奪去他的生命或失蹤。威爾斯對那人說,這是胡言亂語。后來他們發生了爭吵,結果是那人翻開了書,看了里面的內容,然后就朝船邊直直地走去……”
“等一等。”教授說,“那個人是否告訴過威爾斯,他從什么地方得到這本書,或者這本書以前是誰的?”
“告訴過。”普仁格爾認真地說,“好像說是從一位名叫漢凱的東方旅行者那里弄來的。這本書以前也是他的。他就居住在此地。他也警告過那人不要翻開書;結果,這本書的魔力被他得到了證實——直直地走到船邊,失蹤了。”
“你自己相信此事嗎?”教授沉默一會兒,問道。
“相信。”普仁格爾回答說,“我信的理由有兩個:一是威爾斯船長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再者他還講述了那個失蹤者某些神奇的細節。他說那天風平浪靜,那人走到船邊,掉進水里,而水上沒有濺起一絲水花。”
教授看了一下筆記,說:“那你相信的另一理由呢?”
“是我自己親自看見的事實。”傳教士說。
又是一陣沉默。傳教士以和剛才同樣鎮靜的口吻接著說:“我告訴過你,威爾斯把書放在劍的旁邊。我的帳篷開有一個門。我站在里面,眼睛望著森林,背對著他。他站在桌子旁邊說這真是豈有此理!在這二十世紀的今天,還害怕翻開一本書,真傻,他說,我自己為什么不翻開它呢?這時,一種本能使我勸他最好不要輕舉妄動,把書還給漢凱。但他不聽我的勸告,仍不停地說,這究竟有什么危險?這時我問道:‘你船上的朋友怎么啦?’他沒有回答,其實我也不知道他該怎樣回答。‘你能解釋船上發生的事件嗎?’他仍沒有回答。當我轉過身來時,發現他不在這里了。帳篷空空的,書還在桌上,只是封面翻開了,顯然他還往下翻看了內容。左輪手槍還在那兒,但劍放在帳篷另一邊的地上。帳篷布有一大洞,很明顯是用劍劃破的,看上去有人從這里走過去了。從那天起,我再也沒有看見威爾斯船長。我小心翼翼地把書合上,不讓自己看見其內容,然后就把它用牛皮紙包好,準備送給漢凱先生。但當我在科學雜志上看到您關于對此事的設想一文時,我改變了主意,決定來找您。”
教授放下了手中的筆,又仔細地打量起傳教士來。他想:這個人是騙子嗎?他發瘋了嗎?教授準備把他所說的一切看作是謊言。是的,最好的假設是說這些是謊言。他和其他騙子一樣,看起來不大誠實。但是,就是因為他說的這些不太令人相信的事,似乎他只是誠實的。
教授突然說:“普仁格爾先生,這本書現在放在哪里?”
起初的那種笑容又出現在傳教士那長滿胡須的臉上。他說:“我把它放在辦公室里,我是說外面的辦公室,我知道這更危險,也許……”
“你這是什么意思,為什么不直接把它帶到我這里來?”教授問道。
“因為我想在我告訴您發生的這些事情之前,您一看到它,就會翻開的。所以我現在告訴您別輕舉妄動。”傳教士停頓了一會兒,接著又說,“那里只有您那位誠實又呆笨的秘書在工作。”
“呵,是布里奇。”教授笑著說,“你的魔書放在那里較安全,他只不過是一臺校對機。像他這樣的人——如果你把他叫作人的話,是從不會想到要去翻開別人用牛皮紙包著的書。我們現在去把書拿來吧!我坦白地告訴你,我也不知道我們現在在這里把書翻開,還是把它送到漢凱那里去。”
他們兩人一起向辦公室走去。當他們走進辦公室時,普仁格爾驚叫一聲,連忙向秘書的辦公桌走去。秘書失蹤了,書仍放在桌上,顯然,書是打開后又合上的。秘書的辦公桌對著窗戶,朝著大街,窗子被砸了個大洞,似乎有人從這里躍過去了,布里奇無影無蹤了。
他倆像塑像一樣一動不動地站著。教授先挪動了一下身子,把手伸向傳教士,說:“普仁格爾先生,請你原諒我有這樣一種想法:我想這是你虛構的吧!因為任何一個相信科學的人都不會相信你說的那種事。”
“教授,你不相信的話,那么我們最好給他家打個電話,看他是否回家了。”
“我不知道他家是否裝有電話。他好像是住在漢普斯特德路,我也不清楚。不過我想如果他不在家或在朋友那里的話。肯定有人要來詢問的。”教授說。
“如果警察來了,我們能夠向警察對他進行描述嗎?”普仁格爾問。
“向警察……描述……那他……和我們每個人一樣。他總是戴著變色鏡,臉面修得干干凈凈。如果警察真的來了,這本瘋狂的書,我們怎么辦?”
“我有辦法。”傳教士堅定地說,“我把書直接送到漢凱那里去,問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就住在此地不遠,我很快就回來,把他所說的事轉告你。”
“那好極了。”教授坐下來說。此時,他心里感到很高興,因為他擺脫了一種責任,傳教士的腳步聲漸漸消失在街上后,教授靜靜地坐著,眼睛盯著墻上,好像在想什么。
傳教士兩手空空地回來了。教授還坐在那里。普仁格爾說:“漢凱先生要我把書留下,讓他好好想想,然后他說要我們一小時后去拜訪他,他能向我們解釋清楚。他希望教授能和我一起去。”
教授沉默了一會兒,突然說:“漢凱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魔鬼?”
普仁格爾笑著說:“你是說他是一個魔鬼,不!他和你一樣,是一個相信科學的人。他在印度住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潛心研究當地的魔法。也許他在此地還不太出名。他是黃種人,身體較瘦,有一腿跛,脾氣暴躁。其他方面我也不知道。”
奧本肖教授慢慢地站了起來,走到電話旁邊,給法瑟·布朗神父打電話,邀他來一起吃晚飯,然后與他共同驗證這些神秘的怪事。
法瑟·布朗應邀來到了飯店。他在前廳等了許久,才見教授和普仁格爾匆匆而來。顯然,教授對這些神秘事件感到異常興奮。
教授和普仁格爾來到了漢凱的家,他們發現門上鑲有一塊銅牌,上面寫著J.D.漢凱。但是他們沒有見到他本人。他們發現這本可怕的書在桌上放著,書有人看過了。他們還發現后門敞開著,地上有幾個腳印,很明顯是漢凱留下的。他們再也沒有發現漢凱的任何痕跡了。可以肯定,漢凱看了書,去迎接他的命運了。
他們來到飯店的前廳時,普仁格爾突然將書往桌上一擱,好像它燒手一樣。神父出于好奇心,粗略地看了一下書,發現扉頁上印有一首兩行詩:
“誰要是看了此書,
飛行的魔鬼將紛至沓來,
注定他要遭到厄運。”
在詩的下面,有其希臘文、拉丁文及法文的翻譯。
教授對傳教士說:“我希望你能和我們一起進餐。”但他搖了搖頭,說:“很遺憾,我不能,我太興奮了,我想和書在一起單獨待一會兒。我能借用你的辦公室嗎?只要一個小時。”
“我想……門鎖了吧!”教授驚奇地說。
“您忘了窗上有個洞。”傳教士說,他咧開嘴笑了笑,隨即消失在街上的黑夜里。
“真是一個怪家伙!”教授說,教授轉向法瑟·布朗時,奇怪地發現他正和端來雞尾酒的服務員在談話。談的話題是服務員的小孩病了,現在脫離了危險。
“你是怎么認識這個人的?”教授問。
“啊,我常在這里吃飯,經常與他攀談。”
教授也曾在這里吃了五六次飯,可從未想到要與這里的人談話。
這時,電話鈴響了,是普仁格爾打來的。他要找教授說話。他說:“教授,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要看這本書;我現在在你辦公室,書就放在我面前。如果我發生了什么意外,這就是告別了。不要阻止我了,我現在翻開書了。我……”
奧本肖聽到了一種奇怪的聲音,好像是砸窗的聲音。一會兒什么都聽不見了。教授還不斷地叫喚著普仁格爾的名字。他放下了話筒,輕輕地回到了餐桌旁,然后沉著地把這些夢魘般的事件告訴了法瑟·布朗。他說:“已有五人這樣失蹤了,這實在太奇怪了,尤其是我的秘書布里奇,他可是世界上最老實的人啊!”
“是的,真是太奇怪了,他處處都異常小心,辦公室里不屬于他的東西,他是從不亂動的。我相信沒有人知道他還是一個十足的幽默家。”
教授大聲說:“你在說什么,你是說布里奇?你是怎么認識他的?”
“呵,我就像認識這位服務員一樣,常在辦公室等你,并和可憐的布里奇度過了一天的時光。我發現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也可以說他很古怪。”
“我不明白你說的意思,即使我的秘書是古怪的,這不能說明他失蹤的事件,也不能說明其他人失蹤的事件。”教授說。
“什么其他人失蹤的事件?”神父問道。
教授盯著他,像對小孩說話一樣,慢條斯理地說:“我親愛的布朗先生,有五人失蹤了。”
“我親愛的教授,根本沒有人失蹤!”法瑟·布朗盯著教授,慢慢地、大聲地說:“我是說沒有人失蹤!”沉默一陣后,他又接著說,“我想現在最難征明是0加0等于0。”
“你這是什么意思?”教授問。
“你又沒有見誰失蹤;沒有看到船上那個人失蹤,也沒有看見帳篷的那個人失蹤,你只聽普仁格爾先生這么說。我相信如果你的秘書沒有失蹤的話,你就不會相信他說的那些了。”
“對,”教授點著頭說,“如果布里奇沒有失蹤的話,你說的是正確的。但我的確親自看見我的秘書失蹤了,布里奇真的失蹤了。”
“不,恰恰相反。”法瑟·布朗說。
“你這是什么意思?”
“我是說他從沒有失蹤過。” 教授盯著神父,神父接著說:“他在你的書房里。是他喬裝成長著濃密、淺灰色胡子的普仁格爾先生。你平時沒有密切關注你的秘書,以至于他稍一化妝,你就認不出來了。”
“但你聽……”教授開始說。
神父連忙問:“你能向警察描述他嗎?不能。你只知道他的臉面刮得干干凈凈,戴著變色眼鏡。其實,摘下眼鏡便是很好的化妝。你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的眼睛及其微笑。他把他的那本‘魔書’放在辦公室桌上,然后輕輕地把窗子弄破,戴上假胡子,走進了你的書房。他知道你絕不會認出他的,因為你從來沒有仔細地看過他。”
“那他為什么要跟我開這樣瘋狂的玩笑?”教授問。
“因為你把他稱為校對機,也要他像校對機那樣工作。你從來沒有發現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也沒有發現他對你及你的理論也有看法。你認為你能看穿每一個人,但你沒有看出他想證明你連自己的秘書都認不出的瘋狂愿望。他像捏造了威爾斯船長這個人物一樣,輕而易舉地捏造了漢凱先生,他在自己家門上安上一個銅牌,上面寫著漢凱的名字……”
“你是說我們剛才去的那個地方是他的家?”教授問。
“你知道他的家——或他家的地址嗎?”神父問道,“教授,我很欣賞你的理論,我也知道你識破了不少騙子。但我們不應僅僅只會識破騙子,而且也要注意誠實的人,比如說這位服務員。”
“現在布里奇在哪里?”長時間的沉默后,教授問道。
“我相信他還在你的辦公室,就是剛才他打電話來說要翻書的時候,回到辦公室的。”
又是長時間的沉默。教授笑了,他好像在嘲笑一個偉人由于過于偉大而顯得太渺小似的,然后他說:“這是因為我沒有注意我身邊的助手造成的,不過我想這根本嚇不了人。你受驚了嗎?”
“啊,當我看到書放在那兒時,我翻開看了,里面是白紙。”神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