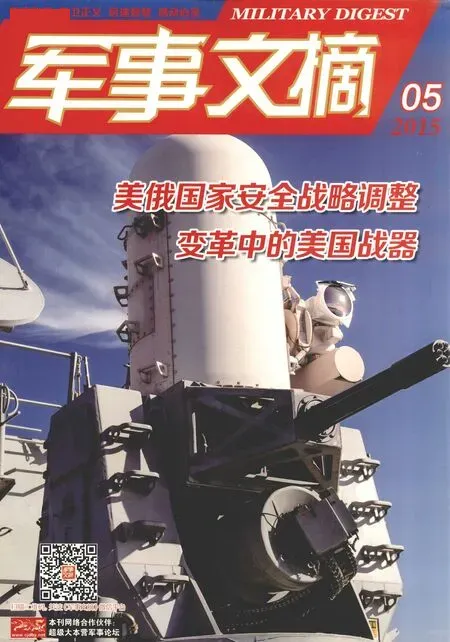中國(guó)近代海軍部長(zhǎng)第一人—醇親王小傳
顧偉欣
中國(guó)近代海軍部長(zhǎng)第一人—醇親王小傳
顧偉欣

醇親王奕譞
愛(ài)新覺(jué)羅·奕譞,清宣宗道光皇帝第七個(gè)兒子,四哥奕詝是清代出名的“苦命天子”清文宗咸豐皇帝,六哥是晚清乃至中國(guó)近代史上都赫赫有名的“鬼子六”恭親王奕訢,兩位四嫂是大名鼎鼎的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嫡福晉葉赫那拉·婉貞是慈禧太后的親妹妹,次子載湉是在清穆宗同治皇帝載淳駕崩后被抱入宮中承繼大統(tǒng)的清德宗光緒皇帝,第五子載灃為清末代皇帝溥儀的生父、大清王朝最后的攝政王,第六子載洵和第七子載濤在清末政壇中也占據(jù)著重要的實(shí)權(quán)地位。擁有這么多的重量級(jí)親人,奕譞不想在歷史上留名也難。
作為近支皇族,奕譞的榮寵不可謂不高:四哥咸豐皇帝即位后,對(duì)六弟奕訢既用又防,但對(duì)七弟奕譞卻十分夠意思,封其為醇郡王,準(zhǔn)在內(nèi)廷行走;他的大侄子同治皇帝即位尤其是親政后,對(duì)這位七叔也是敬重有加,下旨免去了設(shè)宴招見(jiàn)時(shí)的叩拜、奏事可以不書姓名,又先后授予都統(tǒng)、御前大臣、領(lǐng)侍衛(wèi)內(nèi)大臣、管理神機(jī)營(yíng)等職務(wù);同治三年,奕譞被加封親王銜,雖仍是郡王但享受親王待遇;同治四年,小皇帝開蒙、入弘德殿讀書,兩位四嫂—兩宮太后又任命其為弘德殿行走,稽查皇帝的課程;同治十一年,行將親政的同治皇帝加封七叔為醇親王。
縱使擁有如此深厚的家族背景,但若沒(méi)有鴉片戰(zhàn)爭(zhēng)帶來(lái)“中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奕譞也不過(guò)作為一個(gè)親王在錦衣玉食和吟詩(shī)作對(duì)的狀態(tài)下碌碌無(wú)為。但是歷史機(jī)緣巧合,偏偏讓奕譞的人生遠(yuǎn)比他的大多數(shù)同輩宗親更加豐富多彩。
走向前臺(tái)
與聰明外露、果決剛毅的六哥恭親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親王似乎多了些“老氣”,表現(xiàn)得更為低調(diào),更為綿里藏針,也更為大智若愚。
在打倒肅順、端華等八位顧命大臣的“祺祥政變”中,醇親王奕譞的功績(jī)往往被掩蓋在慈禧和恭親王的光環(huán)背后:正是他帶兵將肅順和端華從熱被窩中抓住,完成了政變中最艱難、最有風(fēng)險(xiǎn)、也是最為關(guān)鍵的任務(wù)。在之后的“叔嫂共和”體制中,他執(zhí)掌首都衛(wèi)戍部隊(duì)的主力神機(jī)營(yíng)長(zhǎng)達(dá)30多年,實(shí)際上形成了恭親王掌握外交、醇親王掌握軍事的基本格局。
大清帝國(guó)的這個(gè)“叔嫂共和”的特征是“垂簾聽(tīng)政”和“親王輔政”兩制并存,“親王輔政”是滿清親貴們能接受“垂簾聽(tīng)政”的條件和前提。而醇親王不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數(shù)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這無(wú)疑也是對(duì)恭親王的一種制衡。醇親王早期比較保守、排外,他對(duì)恭親王倡導(dǎo)“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政策嗤之以鼻,建議太后“擯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兩次秘密上書,建議削弱恭親王的權(quán)力,野史中說(shuō)他“疾其兄之專權(quán),久有眈眈之意。”

恭親王奕訢
不過(guò)到了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由于清軍在越南經(jīng)歷了北寧慘敗,恭親王領(lǐng)銜的軍機(jī)處被慈禧太后通過(guò)突然發(fā)動(dòng)的“甲申易樞”政變而連根拔起,由禮親王世鐸領(lǐng)銜的軍機(jī)處班子地位不穩(wěn),慈禧太后特命禮親王“軍機(jī)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huì)同醇親王奕譞商辦”。因此,醇親王雖然因?yàn)楸芟樱ㄋ枪饩w皇帝的生父)而沒(méi)能位列軍機(jī),但此時(shí)已儼然成了軍機(jī)處的真正幕后掌控者。
之前以高調(diào)“憤青”面貌出現(xiàn)的醇親王,此時(shí)一旦主政,便180度大回轉(zhuǎn),不僅完全繼承了他此前批判恭親王的“投降路線”,甚至走得更遠(yuǎn)。恭親王十分倚重的洋務(wù)重臣李鴻章同樣得到了醇親王的器重,在醇親王的強(qiáng)力支持下,清廷批準(zhǔn)了旨在結(jié)束中法敵對(duì)狀態(tài)的《中法新約》。曾經(jīng)痛批過(guò)六哥“投降路線”的醇親王竟也毫不猶豫地做出了對(duì)外和戎之舉,實(shí)在令人跌破眼鏡。
中法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后,清政府痛定思痛,掀起了一輪海防建設(shè)的新高潮。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大治水師”的舉措不僅包括向英德兩國(guó)購(gòu)買新式軍艦,同時(shí)更大的手筆也已經(jīng)醞釀已久、呼之欲出。
總理海軍事務(wù)
自從鎮(zhèn)壓太平天國(guó)運(yùn)動(dòng)領(lǐng)略到了蒸汽軍艦的好處后,清政府通過(guò)對(duì)外購(gòu)買,以及通過(guò)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兩大造船廠的自建獲得了一批蒸汽軍艦,形成了一定規(guī)模的裝備數(shù)量,但歸根結(jié)底不過(guò)是換湯不換藥。沿海雖組建有若干水師,但并沒(méi)有建成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艦隊(duì),全國(guó)也并沒(méi)有統(tǒng)一的組織指揮機(jī)構(gòu)來(lái)統(tǒng)領(lǐng)分散在沿海各港口的水師力量。

醇親王和幫辦海軍大臣善慶、會(huì)辦海軍大臣李鴻章
1874年末,李鴻章曾上洋洋萬(wàn)言的《籌議海防折》,清廷開始較以往重視海軍建設(shè),開始北洋海軍的初創(chuàng),但重視程度顯然不夠,所以海軍發(fā)展很不理想,除北洋海軍外,其余南洋、福建、廣東三支水師發(fā)展極其緩慢。由于全國(guó)沒(méi)有一個(gè)統(tǒng)一的海軍指揮機(jī)關(guān),各支水師皆由當(dāng)?shù)囟綋峁茌牐揪秃茈y協(xié)同作戰(zhàn),而各督撫更將水師看作是自己的私產(chǎn),更難調(diào)遣。例如,福建屬南洋管轄,南洋大臣名義上有對(duì)福建水師的節(jié)制權(quán),可當(dāng)1879年5月兩江總督兼南洋海防大臣沈葆楨奏請(qǐng)將南洋各省兵輪每?jī)稍抡{(diào)至吳淞口會(huì)操一次,以便彼此協(xié)調(diào),遇到緊急情況才能更好地互相支援作戰(zhàn)時(shí),時(shí)任福州將軍慶春、閩浙總督何璟竟以種種理由推托。
更大的阻力來(lái)自于陳舊的觀念,朝野許多人都認(rèn)為不應(yīng)建立一個(gè)中國(guó)傳統(tǒng)“六部”(吏、戶、工、禮、刑、兵)所沒(méi)有、只有“狄夷”才有的新機(jī)構(gòu),可笑的是,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主流知識(shí)分子的心目中,洋人根本就不算人,而只是通了點(diǎn)人氣的“鬼類”而已(湖南名士王闿運(yùn)語(yǔ))。任何學(xué)習(xí)西方的舉措意味著會(huì)被社會(huì)輿論扣上“以夷變夏”的大帽子,約略相當(dāng)于今天可能會(huì)被指為“西化”的罪過(guò)。
中法戰(zhàn)爭(zhēng)后,清王朝鑒于現(xiàn)有水師力量分散,戰(zhàn)時(shí)難以形成統(tǒng)一指揮而導(dǎo)致海戰(zhàn)失利的教訓(xùn)(中法戰(zhàn)爭(zhēng)中南洋水師雖然在朝廷的三令五申下派出了5艘巡洋艦?zāi)舷轮г环ㄅ瀲У呐_(tái)灣地區(qū),但由于朝廷并不能直接指揮援臺(tái)艦隊(duì),使得援臺(tái)艦隊(duì)在離開吳淞口后就畏首畏尾、觀望徘徊,致使援臺(tái)的目的完全沒(méi)有達(dá)到),慈禧太后、醇親王以及海軍建設(shè)的最大倡導(dǎo)者—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在創(chuàng)建海軍、組建海軍中樞機(jī)構(gòu)問(wèn)題上很快取得共識(shí)。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慈禧發(fā)布懿旨:“海防善后事宜關(guān)系重大,著派醇親王奕譞總理海軍事務(wù),所有沿海水師,悉歸節(jié)制調(diào)遣,并派慶郡王奕劻、大學(xué)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會(huì)同辦理。正紅旗漢軍統(tǒng)領(lǐng)善慶、兵部右侍郎曾紀(jì)澤幫同辦理。現(xiàn)當(dāng)北洋練軍伊始,即責(zé)成李鴻章專司其事。其應(yīng)行創(chuàng)設(shè)籌議各事宜,統(tǒng)由該王大臣等詳慎規(guī)畫,擬立章程,奏明次第興辦。”
根據(jù)這道任命,醇親王奕譞等一改以往推諉、觀望之態(tài),僅用12天即籌劃完畢,于九月十七日上奏請(qǐng)求批準(zhǔn)設(shè)立“總理海軍事務(wù)衙門”。心有靈犀的慈禧太后當(dāng)天就下懿旨允準(zhǔn)。其速度之快,在清代歷史上頗屬罕見(jiàn),堪稱神速。從此,由中央政府直接運(yùn)籌中國(guó)海防力量的新格局就此形成。
1886年5月14日,奕譞以總理海軍大臣的名義,在李鴻章的陪同下登上了輪船招商局“海晏”號(hào)客輪,由天津出發(fā)巡閱旅順、威海等地,并檢閱了業(yè)已回國(guó)成軍的北洋海軍鐵甲艦“定遠(yuǎn)”“鎮(zhèn)遠(yuǎn)”,眼看海軍建設(shè)初具規(guī)模,醇親王激動(dòng)之情溢于言表,這次檢閱成了醇親王政治生涯中最為輝煌的時(shí)刻。

懷抱載洵、牽著載灃的醇親王
當(dāng)然,慈禧太后的懿旨還隱藏著一個(gè)深層次的政治目的,總理海軍事務(wù)衙門被賦予的權(quán)責(zé)相當(dāng)廣泛,除了海軍艦隊(duì)以及沿海防御炮臺(tái)外,新興的電報(bào)、煤礦、鋼鐵、造船、西式書局、新式學(xué)堂,但凡能和海軍沾點(diǎn)邊的領(lǐng)域全都?xì)w到了海軍衙門的權(quán)責(zé)之內(nèi),而這些事務(wù)原本都是總理衙門的分內(nèi)之事。聯(lián)想到恭親王雖然因?yàn)椤凹咨暌讟小倍屡_(tái),但是總理衙門畢竟是他經(jīng)營(yíng)已久的“自留地”,恭親王的影響在總理衙門也不是一時(shí)半會(huì)兒能夠消除的。因此,精于權(quán)謀的慈禧太后通過(guò)對(duì)總理海軍事務(wù)衙門以及醇親王奕譞本人的大力支持,成功地達(dá)到了分化原屬總理衙門權(quán)責(zé)范圍內(nèi)的事務(wù),從而削弱總理衙門的目的。但不管怎么樣,總理海軍事務(wù)衙門的建立對(duì)于中國(guó)近代海軍建設(shè)的積極意義還是不言而喻的。
對(duì)于醇親王奕譞本人而言,雖然在才識(shí)上尤其是海軍建設(shè)上認(rèn)識(shí)有限,但是考慮到兒子光緒帝的未來(lái)和大清王朝鞏固的需要,醇親王還是將創(chuàng)建海軍、加強(qiáng)海防作為盡忠報(bào)國(guó)的畢生事業(yè),將極大的精力和熱情傾注其中。受命之后,奕譞敢于放下親王的架子,對(duì)于并不熟悉的海軍事務(wù)能夠虛心向洋務(wù)派(主要是李鴻章)請(qǐng)教,并以其特殊地位爭(zhēng)取慈禧太后的同情與支持,為推進(jìn)以海軍建設(shè)為中心的近代化事業(yè)創(chuàng)造了有利環(huán)境。也正因?yàn)槿绱耍偫砗\娛聞?wù)衙門取代了總理衙門成為指導(dǎo)后期洋務(wù)運(yùn)動(dòng)的中心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中國(guó)第一支近代海軍—北洋海軍能于1888年成軍,并取得國(guó)家經(jīng)制海軍的地位,作為北洋海軍堅(jiān)定支持者之一的醇親王和他主持的海軍事務(wù)衙門功不可沒(méi)。
榮耀中的無(wú)奈
榮耀的背后往往伴隨著悲哀。雖然奕譞為人處處低調(diào),小心謹(jǐn)慎,但是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性—當(dāng)今天子的生父,這自然成了某些好事之徒攻訐的絕好靶標(biāo)。六哥奕訢大起大落的遭遇也使他終日惶恐,生怕哪一天也像恭親王那樣被一腳踢下政壇,對(duì)慈禧太后也是謹(jǐn)小慎微、無(wú)敢僭越。
1889年,光緒皇帝大婚在即,大婚意味著皇帝已經(jīng)成年應(yīng)該親政了,按照祖制—當(dāng)年因皇帝年幼而垂簾聽(tīng)政的慈禧太后須歸政皇帝。對(duì)此慈禧太后并無(wú)異議,只是提出要有個(gè)養(yǎng)老的去處(紫禁城冬冷夏熱,實(shí)在不是什么適合居住的地方),幾經(jīng)商議,最終在翁同龢等人的建議下,光緒皇帝決定將乾隆年間興建、后荒廢已久的清漪園加以修繕,充作慈禧太后的養(yǎng)老之所。為了讓兒子能盡早親政,奕譞主動(dòng)承攬下了清漪園修繕工程的資金籌措差事,不僅從海軍衙門的經(jīng)費(fèi)中時(shí)常拆借銀子給具體承辦園子修繕工程的內(nèi)務(wù)府(前后拆借出數(shù)百萬(wàn)兩,但這些錢內(nèi)務(wù)府在短期內(nèi)都還清了),還以海軍事務(wù)衙門的名義出面向各省督撫攤派“海防捐”,在直隸總督李鴻章的積極協(xié)調(diào)奔走下總共募得白銀260萬(wàn)兩,全部存入銀行生息,以利息貼補(bǔ)清漪園工程(本金經(jīng)慈禧太后允準(zhǔn),預(yù)備在她六十大壽過(guò)后充作北洋海軍購(gòu)艦購(gòu)炮的經(jīng)費(fèi))。因此,1889年后的總理海軍事務(wù)衙門在某種意義上成了清漪園工程的“造辦處”和“提款機(jī)”,這也成了奕譞最為后人所詬病的所謂“污點(diǎn)”。

兩代醇親王—奕譞、載灃父子
但是平心而論,在晚清年間,奕譞的所作所為也是可以理解的,且不說(shuō)慈禧太后作為中國(guó)近代海軍在朝中最堅(jiān)定有力的支持者(筆者認(rèn)為將“中國(guó)近代海軍之母”的稱號(hào)授予慈禧太后亦不為過(guò)),她的懿旨是不能輕易忤逆的,畢竟萬(wàn)一失去了她的支持,原本就不容于主流社會(huì)、舉步維艱的海軍建設(shè)必將受到重挫。同時(shí),慈禧太后早一天入住修繕完畢的清漪園,兒子光緒皇帝就將早一天“扶正”,成為大清國(guó)真正的統(tǒng)治者。可憐天下父母心,哪個(gè)父親不希望兒子能出人頭地?所以即便醇親王在這件事情上表現(xiàn)出了某種私心,若用一個(gè)詞概括他的動(dòng)機(jī)的話,那就是“父愛(ài)”。
遺憾的休止符
終日生活在操勞、憂慮和小心翼翼之下,醇親王的健康每況愈下,他的生命最終停止在了1891年1月1日。在彌留之際,奕譞見(jiàn)到了前來(lái)探視的光緒皇帝,并告誡兒子不要忘記海軍。
他留給承襲醇親王爵位的第五子載灃一段遺言:“財(cái)也大,產(chǎn)也大,后來(lái)子孫禍也大,若問(wèn)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財(cái)也小,產(chǎn)也小,后來(lái)子孫禍也小,若問(wèn)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少膽也小,此微產(chǎn)業(yè)知自保,儉使儉用也過(guò)了。”
聽(tīng)聞醇親王去世,北洋海軍各艦以西式海軍禮節(jié)降半旗10日,以此表達(dá)對(duì)這位曾給予他們莫大支持的親王的哀悼之情。而自此之后,由于另一重要支持者慈禧太后的歸政,光緒皇帝被敵視北洋的“帝黨”所左右,北洋海軍逐漸被中樞所漠視,直到甲午之?dāng)〉耐蝗唤蹬R—隨著北洋海軍在劉公島灰飛煙滅,總理海軍事務(wù)衙門旋即也被裁撤。一代中興之臣籌建近代海軍的努力最終失敗,成為過(guò)往云煙,留下的除了唏噓慨嘆外還有什么呢?
責(zé)任編輯:安翠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