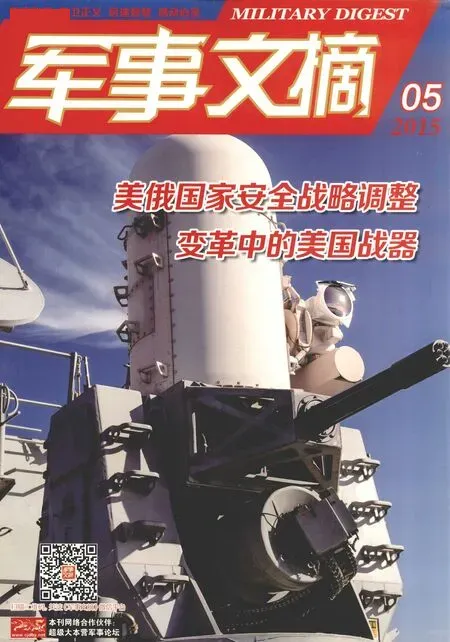魚雷艇沉沒 肯尼迪起步
鴻 漸
魚雷艇沉沒 肯尼迪起步
鴻 漸

肯尼迪從海軍學校畢業時的正裝照
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是一個傳奇。作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當選總統,肯尼迪曾經是大部分美國人心目中理想的領導人,也是許多人心目中理想的丈夫和父親。盡管他的人生之路于1963年11月22日在達拉斯的兩聲槍響中結束,但是那次刺殺事件本身又成了一個廣受關注的疑團。肯尼迪是在二戰結束后的1946年正式從政的,而他傳奇的起點,則要從二戰中期說起。
志愿加入PT艇部隊
1941年9月25日,24歲的肯尼迪接到了美國海軍的委任書,這讓這名瘦弱的年輕人非常高興。他的健康情況一直不是很好,多種先天性的慢性疾病始終糾纏著他,正因如此,陸軍在上一年就拒絕他入伍。當時的肯尼迪已是小有名氣—他以自己在哈佛大學的論文為基礎推出的《英國為何沉睡》一書出版后頗為暢銷,不過他仍然渴望參軍。
在將志愿轉向海軍后,肯尼迪的父親老約瑟夫·肯尼迪開始發揮作用。老約瑟夫是百萬富翁、波士頓銀行總裁、前任美國駐英國大使、肯尼迪家族的締造者,他有能力讓自己的兒子得償所愿。果然,海軍的大門向小肯尼迪敞開了,不過暫時是文職崗位。
入伍后不久,肯尼迪就背痛發作,家族的私人醫生建議他休養六個月并準備做手術,而海軍軍醫認為這是小題大做,他們判斷肯尼迪是肌肉損傷,不過也應該至少休息兩個月。恰巧在此期間,美國海軍贏得了珊瑚海海戰和中途島海戰的勝利,這讓肯尼迪產生了上陣沖殺贏取榮譽的沖動,于是他再一次通過父親的關系,于1942年7月開始進入海軍軍校深造。
兩個月后,在軍校舉行的一場演講,改變了肯尼迪的軍旅生涯。到校演說的乃是PT艇第三中隊的中隊長約翰·巴克利少校。此前的1942年3月11日夜里,還是中尉的巴克利在菲律賓行將陷落之前,成功地用PT艇將麥克阿瑟將軍及其家人、菲律賓總統奎松等人送離巴丹,使他們逃出日軍的虎口。這次救援行動在美國轟動一時,被美國史學家稱作“世界范圍內魚雷艇自誕生以來所承擔的一次最為重大的戰略性使命”,而巴克利本人在回國后躍級晉升為少校,并從羅斯福總統手中接過了一枚國會榮譽勛章。
在那之后,PT艇這種本不起眼的小型艇種的地位驟然得到提升,在有作家詳細了解巴克利的事跡后寫成《他們是犧牲者》一書出版后,更使得PT艇及其服役人員成了全美范圍內廣受關注的對象。而在海軍中,許多官佐士兵們都改變了以往對PT艇的輕視態度,紛紛自愿要求加入PT艇部隊,這種情況同樣存在于預備役人員和軍校學生當中。

在PT魚雷艇上的肯尼迪
巴克利于9月在海軍學校發表演講之際,正逢上述熱鬧背景,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當這位少校在演講即將結束時宣布要征招50名PT艇志愿服役者之后,他發現自己帶的報名表完全不夠用—在場聽他演講的1024名軍校學員差不多全部表達了申請意愿,而肯尼迪就是其中之一。最后,在被“幸運”選中的50余人的名單中,也有肯尼迪的名字。有一種說法是,就在幾個星期之前,老約瑟夫剛剛和巴克利共進午餐。
暗夜行動
肯尼迪很快就去了位于羅德島的PT艇學校報到。在那里,他看到了這種受到美國公眾持續關注的小艇的真身,他對PT艇的印象是“非常脆弱”。教官告訴他們,PT艇的戰場生存力很低,因此“白天絕對不能離港活動”;其所發射的魚雷最快只能跑到28節,比大部分日本巡洋艦和驅逐艦都要慢,因此在進攻時得小心選好位置。受訓一段時間后,肯尼迪遇見了寫下《他們是犧牲者》一書的作者,便對他調侃道,“你的書名應該改成《他們是無用者》!”
上戰場的日子不久后到來,1943年4月14日,肯尼迪趕赴太平洋戰場的圖拉吉島報到,并在15天后成為PT-109艇的艇長。經過一段時間的例行巡航任務,肯尼迪在接手PT-109三個月后奉命帶艇前出到中所羅門群島的盧姆巴里泊地,參與阻止日軍向激戰中的新幾內亞島補充兵員的作戰。
PT-109在接下來的兩周時間里執行了多次夜間阻擊任務,肯尼迪和他的艇員們都變得疲憊不堪。在夜晚行動的日軍運輸船隊被稱作“東京快車”,其中的駁船雖然速度慢,但配置的多門火炮足以將PT艇撕碎,因此這種阻擊時時充滿著風險。
有一個晚上,PT-109被一架日軍的水上飛機尾隨攻擊,后者投下的炸彈幾乎命中艇身,爆炸造成艇上兩人受傷。經過“發瘋般的高速行駛”,并且“一度幾乎飛離了水面”,肯尼迪才帶著他的快艇逃回了基地。經過這次歷險,他決心為自己的艇加強火力,他很快弄來一門37毫米火炮裝到前甲板上,而為了給火炮騰地方,肯尼迪卸掉了PT艇上的救生舟。
幾天后,盧姆巴里的指揮官沃菲爾德接到情報,有一列“東京快車”正從臘包爾駛來,需要緊急攔截。于是沃菲爾德在當晚派出包括PT-109在內的15艘PT艇實施阻擊。PT艇的額定編制是12人,不過當晚另有一位艇長巴尼·羅斯因為自己的艇出了故障而登上了PT-109,這樣就使得這艘小艇一共載著13個人—這對海員來說可是個不吉利的數字。
所有快艇在18時30分離港,前往吉澤島和科隆班加拉島之間的布萊克特海峽,據稱日軍運輸船的目的地就是科隆班加拉島的最南端。駛入海峽后,這些PT艇分成了四個小隊,而當8月2日午夜剛過沒多久,PT-109所在小隊的領頭快艇通過雷達發現了目標,隨即打破無線電靜默并展開攻擊。
由于事發倉促,只有兩艘PT艇沖向敵人,而在駛近后,他們才驚訝地發現那些目標并非駁船,而是驅逐艦。在敵艦猛烈的彈雨下,這兩艘PT艇勉強發射了魚雷,然后就加速逃離。在此過程中,落在后面的PT-109一直無所作為。不過PT艇在當晚的整體表現都很差,15艘PT艇總共發射了30枚魚雷,但無一命中。
接下來,“東京快車”順利完成了卸貨,隨后在2日凌晨1時45分開始向海峽北端駛返。這時,肯尼迪決定采取行動,他指揮著PT-109駛入漆黑的海峽,打算要攔截那些踏上歸途的日本軍艦。

PT-109艇員們的合影
敵艦出現
肯尼迪的快艇在夜色里行駛著,他一直沒有看到敵人,但是有人看到了。2時30分,PT-169觀察到了驅逐艦拖出的尾跡,隨即通過無線電向各艇發出警報。不過在PT-109上,依舊沒有一絲危險將至的征兆,肯尼迪的無線電操作員正和他留在指揮室里,而PT-109也繼續保持著無線電靜默,所以無法接收任何警告。而在甲板下方的艙室里,有兩名艇員正在睡覺,另外兩個人剛剛躺下。
突然間,在前炮塔上執勤的哈羅德·馬尼看到了一個略帶光亮的輪廓,它從黑暗中突然于PT-109的右舷現身,距離大概只有300米并且正在快速接近中。馬尼驚叫起來:“有軍艦在2點鐘方向!”來者是日軍的“天霧”號驅逐艦,在參加了此前的維拉灣夜戰后,該艦于6日成功地避開了美軍的空襲,得以投入到這一輪的“東京快車”之中。
在聽到馬尼驚呼的瞬間,肯尼迪下意識地覺得來的是另一艘PT艇,但幾秒鐘之后他就肯定那是敵艦,于是大聲發出指令:“發動機全速前進!”肯尼迪指望靠PT艇的速度躲開如刀鋒般劃過來的敵艦艦首,誰曾想自己的發動機居然在這種關鍵時刻熄火了,這使得PT-109成了漂在水面上的一只“靜止的鴨子”。
緊接著,排水量為20 0 0余噸、艦長為PT-109四倍有余的“天霧”號便以40節的速度一頭撞上了PT-109的右舷。撞擊瞬間擠扁了魚雷艇的前炮塔,頓時殺死了在那里的馬尼和另一位艇員安德魯·科爾斯基。PT-109的艇身很快一分兩段,從燃料箱噴出的汽油開始燃燒,在指揮室里的肯尼迪后來回憶道,“那一刻還以為死期已至了。”
撞擊幾乎沒有給“天霧”號造成什么損失,“天霧”號揚長而去了。而反應過來的肯尼迪下令棄艇,他和另外10名還活著的部屬跳入了海水中,包括已經被嚴重燒傷的輪機員麥克馬洪。
“出色的艇長”
PT-109斷成了兩截,幸運的是,大火在不久后熄滅了,于是大家紛紛游向漂浮著的艇體,開始隨波逐流。天蒙蒙亮時,肯尼迪發覺情況不妙,半傾的艇體正在漂向日軍控制下的科隆班加拉島,于是他指著遠處的一個無人小島說,讓我們游到那兒去。
這場海上泅渡從8月2日13時30分開始,這些人為了活命而奮力游泳。被燒傷的麥克馬洪已非常虛弱,這時,曾是哈佛校游泳隊一員的肯尼迪展示了實力,他用牙齒咬住麥克馬洪救生衣的束帶,拖著他一起前行。整整5小時后,肯尼迪帶著麥克馬洪率先到達小島的岸邊,那時他已經完全站不起來了。

靜泊中的PT-109
日落時分,不顧艇員們苦勸的肯尼迪又獨自游入海峽,指望著能夠碰上恰好路過的PT艇,但他一無所獲。第二天,肯尼迪又接連好幾次獨自下水,但都毫無發現。不過,艇長過人的勇氣倒是喚起了部下們對活下去的希望。
這些人在島上靠椰子充饑,等到可食用的椰子差不多吃完后,他們又游去了附近的另一個小島,再一次地,肯尼迪還是拖著麥克馬洪游泳。在這個島上,肯尼迪等人被打漁的土著發現了,于是到了8日黎明—在PT-109沉沒6天之后,這一行11人被帶回了盧姆巴里基地。
海軍隨后指派比隆·懷特中尉調查PT-109的沉沒事件,此人恰好是肯尼迪的朋友。在他出具的調查報告中,主要篇幅都是肯定肯尼迪的求救壯舉,至于沉沒過程則比較簡單,沉沒原因基本屬于是“不可抗力”。
盡管官方認定肯尼迪無需對沉艇負責,但是艇隊里的人可不這么看,他們現在稱肯尼迪為“撞擊杰克”。他的上司沃菲爾德評價道:“肯尼迪并不是一個出色的艇長。”而他的繼任者杰克·吉布森更是直言不諱:“正是因為對艇員松懈的管理,肯尼迪才失掉了他的PT-109,到他落水之前,他所做的事情都是錯的。”艇長們說,當試圖突然將PT艇的發動機推至最高出力時,往往會導致引擎“死機”,對艇長來說這本是一個常識。
面對著這樣的評價,肯尼迪希望改變自己的形象,他拒絕了父親為自己回國而做的努力,在10月成為第一批接手新式PT艇的艇長。從10月下旬到11月初,他帶著自己的新艇PT-59從位于科隆班加拉島西北面的新基地多次出擊,自愿參加那些最危險的任務,“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他的一名艇員說,“天哪,這個人是不是想帶著我們大家一起去死啊?”
11月2日,一則求助訊息發來,有一批美軍的登陸艇遇險,急需支援。這時PT-59剛剛執行完一次任務歸來,只剩下了半箱油,但是肯尼迪下令立即出發。冒著敵軍的炮火,PT-59成功地靠上1艘快要沉沒的登陸艇,把那上面的50名陸戰隊員全都轉移過來,然后以超負荷的危險狀態駛回基地。有人評價說,肯尼迪之所以表現出這種勇猛到近乎玩命的勁頭,是因為他深知自己對PT-109的沉沒負有責任,他對兩名部下的送命感到深深的內疚。
傳奇的起點
奮力的搏殺消耗著肯尼迪的體能與精力,他那本就不太健康的身體難堪這樣的重負,軍醫隨后確認他已不適合出海行動,肯尼迪遂于當年12月14日被調回國內,從而結束了在太平洋戰場為期并不長的服役。

肯尼迪最終因為沉艇后的表現獲得了勛章
失去了在戰場上證明自己機會的肯尼迪顯得有些消沉,他不知道,PT-109沉沒事件的“逆襲”即將在國內上演,而他在此事件中的形象也將發生重大的顛覆。
在剛得知失蹤的兒子生還后不久,肯尼迪的父親就已經通過自己的關系在《紐約時報》刊發了相關報道,這則配有《百萬富翁兼外交官約瑟夫·肯尼迪的兒子在太平洋的壯舉》標題的文章,初步對肯尼迪在落水后的表現進行了渲染。
在那之后,老肯尼迪又在海軍高層中活動,希望為兒子贏得表彰戰斗突出人員的銀星勛章。海軍最終同意向肯尼迪發勛章,但只是一枚非戰斗勛章,而且,海軍部長弗蘭克·諾克斯還一直將頒獎證“留中不發”。直到諾克斯于1944年4月死于心臟病,詹姆斯·福萊斯特成為新任海軍部長后,才向肯尼迪簽發了頒獎證。附帶一提,這位新部長也是約瑟夫·肯尼迪的摯友。
與此同時,肯尼迪在一次聚會中遇到了作家約翰·赫賽,后者提議將PT-109的故事寫下來,投給《生活》雜志。赫賽是一位以小說贏得普利策獎的人物,他同樣打算用小說筆法來還原PT-109的故事,照他的說法就是,“艇員們都如同小說人物一般生動”。這篇文章很快完成,其中對于主角肯尼迪在落水后的經歷有如下的描述,“他的思緒似乎漸漸漂離了他的身體,無盡的黑暗和流逝的時間擠占了他軀殼內的思索空間。”
鑒于文章這種過于強烈的文學性,《生活》雜志做了退稿處理。所幸另一份雜志《紐約客》覺得文章挺不錯,遂于1944年6月將其發表。《紐約客》的發行量不大,不過老肯尼迪另有“高招”,他成功地說動《讀者文摘》發表了一篇精簡版的文章,從而令肯尼迪在大海和荒島中的“高大形象”廣為傳誦,成為了數百萬美國人茶余飯后的談資。
戰時的美國需要英雄,而美國公眾愛極了肯尼迪的這個故事,于是,“真正的肯尼迪和赫賽筆下的肯尼迪融為一體,化為公眾心目中神話般的存在”。這個轉折甚至讓肯尼迪的屬下們都有些難以接受,出事當晚在PT-109上的“第13人”巴尼·羅斯就表示:“我們大家一直都覺得很羞愧,都認定這是一場災難,不料國內的故事卻讓它成了英雄壯舉,這真有點像是敦刻爾克大撤退。”
肯尼迪的兄長約瑟夫·肯尼迪二世,一名高大英俊而且體魄出眾的轟炸機飛行員,在《讀者文摘》熱銷之際給弟弟寫信。他在信中發問:“我真正想搞明白的是,當驅逐艦出現在視野里時你究竟在做什么?又發出了什么應對指令?”弟弟從未發出自己的回信。
不管怎樣,《紐約客》和《讀者文摘》所報道的PT-109故事幫助肯尼迪站到了政治生涯的起跑線上。1946年,肯尼迪正式從政,在他第一次競選議員時,大量印發的《讀者文摘》影印本就為他爭取到了無數選票。PT-109沉沒了,卻成了肯尼迪傳奇“真正的起點”。
責任編輯:何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