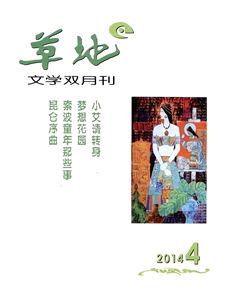大草原,它的名字叫“紅”
伍松喬
成都離雪山草地之近,出乎外地人的想象。向西、向北、向南,幾小時的路程,便可以親近那令人心動的高峰之白與遼闊之綠。實際上,即便在市區,大詩人杜甫在他那草堂寫下的“窗含西嶺千秋雪”。也是紀實而非虛構。如今雨后初晴,成都人還能偶爾享受到唐朝詩人筆下的雪峰佳境。
雖然如此,中國的城市病誰都不能幸免。因此,不難想象,當人們馳出塵埃遍地、霧霾彌漫的都市,一頭撲進無比清新的原生態的草原環境,該會是何等的欣喜。
這里是中國五大草原之一的川西北大草原的核心區,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部的紅原大草原。
這是深秋時節,沿“天府之國”的母親河岷江上游逆行,從都江堰、汶川、茂縣、黑水經過,我們親臨感受著地形景觀由平原、山地至高原的神秘變化,不可名狀的興奮指數隨海拔高度的增高一路攀升。
當我們終于踏上紅原平均海撥3600米以上的草地,人們都不禁“哇”了起來,有種煥然一新、重新做人的“轉世”之感。每一處放眼,都是絕佳的關圖:藍天穹頂,白云緩緩飄逸,綿延的雪山給撒野的草原鑲著白色的花邊。遠遠近近、曲線優雅的溪流。在燦爛陽光下閃灼波光,別看它們淺水緩流,確都分屬長江、黃河兩大水系,是滋養神州的母親河之源。即便青草的芬芳混合著淡淡的牦牛糞氣味,也依然是清香的。
或許所有的草原皆有共同的美麗,但這一片天然牧場面積達1200萬畝。這是離西部中心大城市成都最近的一個草原縣,它有著卓爾不群的獨具魅力,它的名字叫“紅”。
我曾經多次來過這里,最初也和今天的新來者一樣困惑,綠的草、黃的花,草原的冬天會蓋上了皚皚白雪。怎么會是紅的呢?
它的名字,來源于1930年代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那條“紅飄帶”。1934年至1936年,那支帽徽上貼著紅五星、以“紅軍”作名字的隊伍,堅忍不拔,徒步跋涉。二萬五千里的腳印,在地球上畫出了這條奇跡般的紅飄帶。這條紅飄帶最曲折的一個結,就是今天我們腳下的大草原。
悲壯的歷史銘刻在距離紅原縣城四十二公里的日干喬大沼澤。大沼澤的前端矗立著一塊刻有周恩來總理題詞的石碑,“紅軍長征走過的大草地”十個大字,在藍天白云的映襯下,記錄著一段可歌可泣、驚天動地的歷史。1960年,周恩來總理親自將這一片土地的行政設置命名為“紅原”縣。
紅原,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中三過草地的地方。
1935年8月21日,紅軍開始過草地,分左右兩路平行前進。紅軍在這里前后駐留長達半年之久,每一寸草地都深印著紅軍的足跡。《紅原縣志》記載,紅軍進入縣境后,曾在龍日壩地區遭遇敵人數千騎兵的阻擊,傷亡嚴重。紅軍進入草地后,則因饑餓、陷入沼澤泥潭、劇烈的高原反應等而犧牲的紅軍無數。
日干喬大沼澤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濕地之一,當年的紅軍,為了迅速擺脫敵軍,以為可以不繞道山脊而走捷徑,直奔草原的腹心地帶,陷入了看似平坦卻險象叢生的泥潭深淵。茫茫澤國的死亡大陷阱,吞沒千軍萬馬也不會留下痕跡。
紅軍過草地時到底有多少人犧牲?至今沒有確切的答案。在幾乎所有關于這段歷史的記載中,都會用到“難以計數”這個詞語。阿壩州黨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紅軍三大主力過草地時非戰斗減員的人數在萬人以上。
過草地對于紅軍來說,幾乎是“滅頂之災”。如果沒有高原的牦牛、青稞救援,紅軍完全有可能象蔣介石斷言的那樣走向滅亡。在草地水天一色的茫茫雨霧中,根本就無路可走,只有牦牛知道牧民踏出來的小路藏在水下何處。因此,毛澤東當時感慨萬分地把紅軍抓住牦牛尾巴過草地,叫做“牦牛革命”。
巴西會議使得黨和紅軍擺脫了政治困境,包座戰役打通了北上的道路。過完草地,紅軍起死回生。
東西方向的紅飄帶轉而北上,紅軍的歷史融入世界反法西斯較量的大搏斗,由此開始了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的鳳凰涅架。
草原陷阱今何在?
追尋當年紅軍在草地的遺蹤,有人試著用腳去踏那些水草地里的草蹬。眾多紅軍回憶錄說,草蹬周圍的泥土通常“軟得像豆腐,不僅滑,而且像膠一樣粘。一旦掉進去,就越陷越深,越掙扎陷得越快。掉進沼澤里的人,伙伴還沒來得及拉上他們,便消失了。”今天的游人,難以進入濕地深處體驗到沼澤的兇險莫測,自然難以相信小學課本里《七根火柴》和《金色魚釣》的真實。
今天的草原經過了數十年的風雨變遷,草原生態有了很大的變化,受近代新構造運動和氣候變化的影響,沼澤已趨于自然疏干,有的已經成為牧場。
從紅原到若爾蓋的路上,開始沙化的草地和草坡不斷掠過。作為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征服”沼澤、海灘、草原的所謂“三大進軍”之一,當地長期大面積開溝排水,大部分濕地變成了牧場,生態環境嚴重惡化。慶幸的是,兩縣從1999年開始堵溝蓄水,恢復濕地,曾經消失的若干珍稀動植物,又漸漸出現。
晚上與紅原的干部相聚,問起當年曾經采訪過的瓦切鄉草原老紅軍侯德明,不料兩年前他已經去世。至此,“紅原縣的最后一位老紅軍也走了。”
侯德明原籍湖南長沙。他的人生極富傳奇色彩。1935年,他們三代9口,舉家跟隨賀龍部隊參加了紅軍,經歷漫漫長征路,最后只有3人活了下來。在還差100多公里就走出草地之際,年僅12歲的侯德明雙腳潰爛,實在走不動了,被寄養在當地一個叫格西阿谷的藏民家里,取名羅爾吾(意思是“寶貝”),從此流落藏區70余年,連漢話也不會說了。
2005年,我在日干喬大沼澤不遠處的瓦切鄉下哈拉瑪村見到了侯德明,他早已成家立業,兒女也作為土生土長的牧民長大成人。2004年,領到失散紅軍證后,歷經艱辛,他還是找到了老家親人,由兒子陪著終于回到了他魂牽夢繞70余載的故土。
縣宣傳部的人還講,因為政府的“牧民定居計劃”,侯德明生前和他的兒女們都住進了牧民新村,有了自己白墻紅瓦的藏式小樓。
一路上,像侯德明家一樣的牧民定居點,在草原上不時出現,政府給每家牧民補助2.5萬元建新房,以前用紅柳條和牛糞搭建的房子已經少見。隨著退牧還草和輪牧制的推行,每家一年還會有1000多元的補助。牦牛、牧犬與衛星“鍋”、太陽能熱水器交融,成為草原上新的景觀。endprint
獲得了“中國紅色經典生態旅游勝地”稱號的紅原,雖與著名的九寨溝、黃龍、四姑娘山、米亞羅風景區毗鄰,但與它們的旅游開發差距甚大,壓力重重。隨著省、州著力推進的“大九寨”國際旅游區計劃,使處于其核心區的紅原有了中心開花、后來居上、與鄰共生共贏的歷史機遇。而已經建成的紅原機場,無疑將成為引爆當地跨越式發展的導火索。一年前,深思熟慮的《紅原大草原國家公園旅游產業發展總體規劃》出臺,而在路上所見機場附近的村莊、牧家。明顯提升了建筑的檔次,那些都是牧民的家庭旅館和“牧家樂”。政府與民間的同心合力,可見一斑。
從紅原到黃龍、九寨溝,必經松潘縣川主寺鎮。紅軍長征紀念碑園背倚雪山遠景,前瞻草地白云,主碑、大型花崗石群雕、陳列室組成的風景,向人們舒展著一幅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的恢宏畫卷。
每每晨暉或者夕照,陽光聚焦,主碑流金溢彩,熠熠生輝,光芒四射。牧民將這一景觀視為“神跡”,說是長征精神永存,紅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長征沿途11個省,共有1300余處大大小小的紀念建筑。總碑顯然不同于某一事件、某一戰斗的紀念建筑,它不在長征出發地江西瑞金,不在長征勝利會師地甘肅會寧,也不在革命圣地陜西延安,選擇四川,自有原因。——紅軍長征行程二萬五千里,其中一萬五千里在四川,歷時一年零八個月;途經近70個縣。是經過的11個省中,自然環境最險惡、敵我戰斗最慘烈、黨內斗爭最激烈的省份:留下了四渡赤水河、跨越嘉陵江、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穿越大草地等輝煌戰績。不僅如此,就連“長征”二字,也是在四川第一次提出的,1935年5月20日,朱德總司令在四川冕寧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中,首次使用了“長征”一詞。
尤具象征意義的是,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先后跨越草地,最終三軍集結,“確立北上方針,奔赴抗日前線”。藍天白云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線圖》的行軍標示上,“紅軍長征走過的大草原”是一個清晰的轉折。
紅軍長征與四川血肉相連,魚水難分。三個方面軍10多萬人,先后在四川一年零八個月,每天食用的糧食便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長征入川,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達14次之多,這些會議如同一個個紅色的箭頭,明晰地標示出中國革命進程的迂回、挫折與前進。
四川,能不憶長征?長征,最憶四川紅!
該怎樣來描繪這可歌可泣的風云激蕩,是畫還是歌?
鐵馬金戈應有詩。
萬里長征,早已被一個人寫進了詩,寫成了史詩。
它的題目:《七律·長征》,作者:毛澤東。
“三軍過后”,毛澤東懷著一路征戰的豪情離開四川,吟著詩走進了陜北吳起鎮。《長征》沒有寫犧牲,沒有寫流血,沒有寫從八萬人到八千人這一懸殊遞減中的痛苦和哀傷。在自然艱險中,詩人獨具慧眼地發現了自然之秀美,在自然之秀美中,發現了紅軍將士征服天險、戰勝敵人之壯美。
長征為什么會勝利?要義之一,是大無畏的英雄主義氣概和必勝的樂觀主義精神。毛澤東的詩歌,是長征精神的寫照與升華。
再到紅原,這一次來的季節遠不是它的最美。
紅原大草原最關的季節在春、夏。五、六月,會有漫山遍野的野花,七、八月,無邊無際的蒼翠綠茵,簇擁著藏族男兒賽馬、女兒起舞。
一片生機在紅原。
我們還會再來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