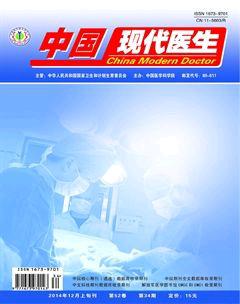醫生文化對醫院行為醫學學科建設的影響
高天 馬效恩 王晉 宋雨瀟 李曉紅
[摘要] 本研究通過一家綜合性醫院發展行為醫學學科過程中的行動研究,探索了醫生文化對行為醫學學科建設的影響。研究指出,醫生文化對行為醫學學科建設有重要的影響。行為醫學學科建設實踐的主體是醫院的醫生,必須設法獲得醫生的理解、支持與參與。
[關鍵詞] 行為醫學;文化;醫院;職業
[中圖分類號] R197.1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4)34-0106-03
行為醫學是近十幾年來得以快速發展起來的綜合行為科學和生物醫學多學科知識的交叉性學科, 被廣泛應用于保健、疾病的診治、預防與康復[1-8]。國內外研究顯示,通過行為醫學干預可減少藥物使用,顯著降低醫療成本[3-7]。由于行為醫學的發展有助于切實解決“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難題,在國家探索進行醫改的背景下,探索綜合性醫院行為醫學學科建設和服務模式有深遠現實意義。盡管行為醫學的重要性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行為醫學作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目前國內也只有為數不多的醫院開展了行為醫學的臨床應用服務。在綜合性醫院發展一個新的學科,是一種創新或者變革,將會面臨很多挑戰[9-13]。專業技術人員,尤其醫生,是綜合性醫院臨床學科建設的主體。
由于職業的特點,醫生形成了獨有特色的職業文化。醫生在醫療服務中扮演了領導的角色,比如,其直接影響超過80%的醫療支出[7]。致力于改善醫院的醫療質量、績效、成本/效率的努力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醫生的態度[15]。一般而言,醫生是自治的個體,是自我管理的、不合作的,不愿意接受任何改變,保持臨床自治和高專業水準在其實踐中是十分重要的[16]。在一個積極的醫生文化下,醫生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享受一個健康的、有競爭的內在活力的氛圍,知道他們在提供高質量的醫療[17,18]。如果醫生愿意投入或參與進來,他們將期待強的績效和好的結果。本研究以一家綜合性醫院發展行為醫學學科為例,探索醫生文化對醫院學科建設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本研究采用了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19,20]進行。行動研究是一種質性研究方法,以解決問題為核心、適用于特定的條件,應用十分靈活,可以解決理論研究與實踐之間的脫節問題[21]。在國際上,該方法已經被廣泛地應用在管理研究及臨床研究中[21]。本研究覆蓋了一所綜合性三甲醫院應用平衡記分卡進行行為醫學學科建設與提供行為醫學臨床服務的規劃及實施的24個月的過程。
該院是市屬局級綜合性三級甲等醫院,是山東大學附屬醫院,也是市紅十字中心醫院、老年病研究所、國際SOS合作醫院、市國際醫療保健中心所在地,擔負著當地及外地的醫療、教學、急救、預防、康復、保健、科研、社區衛生服務等任務。在本研究中我們先后與5個臨床科室的主任、醫護人員進行了21次專題討論和會議,另外在實施學科規劃中對醫生的工作進行觀察,來了解并回答研究問題、醫生文化對醫院學科建設實施的影響。
1.2 方法
本研究采用參與性觀察、對話、會議和深度訪談等方法采集數據,并應用概念圖、SWOT 分析、邏輯性分析、問題分析等方法對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
2 結果
在對該院的學科現狀進行了分析后,我們選擇了神經內科、兒童保健科、神經外科、康復科、心理咨詢門診等專業作為發展行為醫學專業的目標科室。具體原因如下。
神經內科是該院最大的臨床科室,目前的一項優勢業務腦卒中單元是以介入診斷治療、藥物治療及康復治療為一體的醫療模式,其深刻認識到非藥物治療的優勢,在此基礎上,能比較容易接受發展行為醫學。神經外科的患者也需要及時的康復治療,如果能與神經內科基于行為醫學基礎上進行業務合作有助于提高其患者治療效果,促進其業務發展。神經內外科的業務合作也有助于新的以患者為中心醫療模式的發展。兒童保健科目前已經開設了兒童感統訓練、心理測試等項目,其在兒童行為干預治療方面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心理咨詢門診是濟南市級唯一的心理專科門診,但患者數量不多,如能借助行為醫學平臺,加強跨專科合作,業務將有較大發展空間。康復醫學科已經開展的腦卒中患者的干預治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于其科主任也兼任神經內科主任,因此在開展行為醫學治療方面有很大潛力。
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組建跨專業的松散的行為醫學專業平臺,也就是構成新學科的各專業之間沒有行政隸屬關系,只是業務合作關系。以腦神經科學為龍頭,依靠其病員,吸收兒童保健、心理咨詢及康復專業,為患者提供基于行為醫學的一體化診斷治療平臺。組成松散平臺而不是緊密的平臺的原因是避免一開始就打破原有的行政架構,造成對新學科發展的阻力。
在明確上述思路后,我們開始征求相關科室主任的意見。在溝通中發現上述科室的科主任們對行為醫學了解不多,僅有1人聽說過行為醫學。我們介紹了行為醫學的基本概念及業務范圍,重點介紹了發展行為醫學專業對其現有專業業務的發展可能帶來的促進。另外我們還介紹了建立松散合作的行為醫學學科架構的設想。所有專業的主任對發展行為醫學專業表現了一定興趣。有3個專業的科主任表示愿意參與行為醫學學科的建設,1個專業的主任認為目前無法和神經內科進行合作,因為平時兩個專業的交叉業務比如介入診斷治療方面存在沖突,無法合作。盡管兒童保健科主任很愿意發展兒童行為干預治療,但由于醫生數量不足,表示下一步再考慮加入行為醫學學科平臺建設。隨后就行為醫學學科的發展與3個愿意參與行為醫學學科建設的學科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溝通。從最初設想的以疾病為中心建立跨5個專業的平臺縮減為以神經內科為主體、康復醫學科和心理咨詢門診配合的業務平臺。經過多次討論,最終明確了行為醫學學科發展愿景:“整合醫院資源,以行為醫學為平臺,發展腦神經科學優勢學科群,發揮學科群優勢,為患者提供正確的神經學及行為醫學診斷與治療,促進醫院臨床業務及科研的發展。”endprint
行為醫學學科建設的實施,需要改變醫生的診療行為。比如,神經專業傳統的診療往往只給患者藥物或手術治療,在新的行為醫學診療平臺下,醫生需要根據患者的情況,組織跨專業的會診,比如對睡眠障礙患者不僅是提供藥物治療,而且提供綜合心理、康復治療、行為干預為一體的治療方案。對醫生而言這加大了工作量。因此實施一開始醫生對此并不以為然。隨著其對行為醫學了解的加深,了解到同時開展行為醫學科學研究對其專業發展的價值,逐漸改變了認識,愿意接受這一變化。
該院于2014年6月實現了神經及行為醫學門診的開診,盡管目前患者還不多,但行為醫學診療模式已開始為越來越多的醫生所接受。由于目前該院行為醫學業務還剛起步,醫生文化對該學科建設的影響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
3 討論
因為專業人員通常不愿意接受變革,因此盡管有良好的意圖,在醫療行業的變革也是可能會失敗的[22]。與醫院的其他群體相比,更有可能出現懷疑和抵制變革的群體是醫生[23]。研究表明,醫生與其他專業技術人員相比有更少的意愿接受組織變革[24]。因此在成功的醫院變革中,醫生對變革的態度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25]。本研究中由于神經外科主任對跨學科的合作存在疑問,最終該專業沒有參與行為醫學學科的建設就是一個例子。
這主要是因為醫院是以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為主要使命的,而醫療服務首先是由醫生來為患者做出診斷,然后設計治療方案,護士協助醫生完成對患者的醫療服務的。由此在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的過程中,醫生扮演了核心角色[15]。鑒于醫生在醫院運營中扮演的主要角色,醫院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醫生的配合與支持。作為一個特殊的職業群體,由于其所受的追求客觀證據的醫學教育以及需要相對獨立做出對患者的診斷治療方案的工作模式影響,醫生有其獨特的職業文化,一般認為醫生是自治的、不愿意接受改變的[16],挑戰醫生的自治可導致其對創新的抵制。因此一項新的理論或技術能否在醫院臨床中得到應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臨床醫生對其的認可程度。
從本研究中行為醫學學科方向的縮減上可看出這一影響的重要性。當本研究提出可以疾病為中心建立與神經內科與神經外科的協作機制時,神經外科主任提到了兩個專業在交叉業務治療方面的沖突,并沒有接受這一建議。這種學科之間的沖突實際上是醫生職業文化中對專業壟斷性要求的表現。因為神經外科主任認為神經內科的業務對其有威脅,影響其業務發展,實際上威脅了其業務自治。
但醫生文化本身,是尊重事實和科學邏輯的,對于所需作出的改變,只要這種改變有其合理性,在良好溝通的前提下,他們還是愿意接受這種改變要求的。比如,盡管神經外科主任沒有接受神經內科主任合作的橄欖枝,神經外科副主任表示愿意就合作進行溝通,因為他有很強的發展新業務的愿望。其開展的幾個新項目需要更多的患者,而與神經內科的合作能擴大其患者來源。
另外醫生的職業文化使其對專業發展十分重視。如果其專業發展不能得到保障,很難保證他們能積極投入到工作中。比如在某醫院實施平衡記分卡的實踐中發現,由于某科室醫生專業發展方向不明確,導致人員流動性大,影響了該科業務水平的提高。而實施記分卡后,明確了學科的發展目標,解決了該科醫生的專業發展方向的后顧之憂,促進了該專業業務的快速發展,人員穩定性得到明顯提高,其醫療質量、效率及患者滿意度都得到較大改善[21]。
本研究中,行為醫學科的最終成立也反映了醫生對專業發展的重視。比如,開始時盡管對行為醫學并不了解,當聽到行為醫學能擴大其當前學科專業發展的好處,使其不僅在業務上還是在學術上都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時,大部分科主任們還是對行為醫學這一新概念表現了濃厚的興趣,并接受了發展行為醫學業務的建議,最終開始行為醫學的臨床實踐。讓醫生明白行為醫學對醫生專業發展的重要意義是在綜合性醫院建設行為醫學科的重要基礎。
醫生在專業發展上的需要是新學科在醫院發展的基礎與動力。也就是說,如果新的學科能夠促進醫生實現專業價值,那么這個新的學科就可能會被醫生所接受。醫院要實現業務發展,極大地依賴于醫生的態度、信念和行為。并且這點很難被測量、翻譯及與其他組織來比較。塑造一個積極向上的醫生文化,是醫院學科建設的重要基石。如果醫院能在新學科的規劃建設中充分考慮到醫生對專業發展的需求,那么,學科建設將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4 結論
在行為醫學學科建設實踐的主體是醫院的醫生,必須設法獲得醫生的理解、支持與參與。醫生文化對行為醫學學科建設有重要的影響。實施學科規劃過程中醫生態度及行為的改變,是本研究中行為醫學學科建設順利起步的重要原因,沒有醫生的參與和支持,學科建設無法在醫院取得成功。
[參考文獻]
[1] 白波,吉峰,楊志寅. 中國行為醫學研究與發展戰略之思考[J]. 中華行為醫學與腦科學雜志,2012,21(1):2-5.
[2] 楊志寅,蘇中華,吉峰. 行為改變技術的作用機制[J]. 中華行為醫學與腦科學雜志,2012,21(4):289-291.
[3] 楊志寅,蘇中華,孔令斌,等. 對行為醫學的再認識[J]. 中國行為醫學科學,2006,15(5):385-388.
[4] 楊志寅. 20 年歷程開辟行為醫學發展之路[J]. 中華醫學信息導報,2010,25(1):3-4.
[5] 楊志寅,蘇中華,王克勤. 行為醫學的新認識和發展趨勢[J]. 中國行為醫學科學,2007,16(9):769-772.
[6] 楊菊賢,楊志寅,張作記. 行為醫學學科發展與展望[J].中國行為醫學科學,2005,14(8): 673-674.
[7] 楊菊賢,楊志寅. 行為醫學在中國的誕生和發展[J]. 中華行為醫學與腦科學雜志,2009,18(12): 1057.
[8] 甘露,王志玲,黃慶軍. 我國行為醫學研究進展[J]. 白求恩軍醫學院學報,2006,4(1): 35-37.endprint
[9] 王丹,程侍苗,楊驊,等. 大型綜合性醫院學科建設戰略思考[J]. 解放軍醫院管理雜志,2006,13(1): 15-16.
[10] 于德華,李建剛,楊震,等. 臨床醫學學科建設策略與方法[J]. 中華醫院管理雜志,2011,27(9): 661-663.
[11] 張鵬俊,馮寶華,王辰. 醫院學科建設的內容及策略[J].中國臨床醫生,2014,(7): 25-27.
[12] 趙亮,金昌曉,喬杰. 大型公立醫院學科建設發展戰略探索與思考[J]. 中國醫院管理,2013,33(11): 44-46.
[13] 黃春基,齊德廣,林海,等. 綜合醫院研究型學科建設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與實踐[J]. 中國醫院管理,2014,34(6):71-72.
[14] Dahill,K. & Kalman,M. Rethinking physician relations[J].Health Forum Journal,2001,March/April,8.
[15] Bujak JS. How to improve hospital-physician relationships. Frontiers of health services[J]. Management,2003, 20 (2):3-21.
[16] Thomas M. Physicians and hospitals: new partnerships[J].Health Systems Review,1996,29 (3):35-37.
[17] Lyons M F. Be Positive-it's a necessary strategy[J]. Physician Executive,1999,25(2):72-73.
[18] Lyons MF. Common denominators of success[J]. Physician Executive,2001,27 (2):84-85.
[19] Mckay J,Marshall P. The dual imperative of action research[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2001,14:50-52.
[20] Kaplan R S. Innovation action research: creating new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1998,10:89-118.
[21] 高天,劉子棟,王國興,等. 醫院實施平衡記分卡過程中醫生文化的作用[J]. 中國醫院,2010,14(2):32-35.
[22] Fleuren,M.,Wiefferink,K. & Paulussen,T.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on within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literview and delphi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2004,16 (2):107-123.
[23] Gollop R,Whitby E, Buchanan D,et al. Influencing sceptical staff to become supporters of service improvement:A qualitative study of doctors' and managers' views[J].Quality and Safety in Health Care,2004,13:108-114.
[24] LEE FW. Adoption of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as a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 ambulatory care at the 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J]. Topics in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00,21(1):1-20.
[25] Letourneau B. Managing physician resistance to change[J].Journal of Healthcare Management,2004,49(5):286-288.
(收稿日期:2014-10-1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