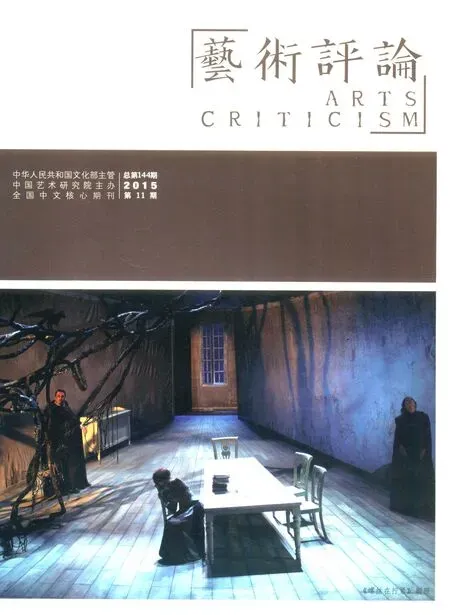試析交響樂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的藝術特色
孟 纓
試析交響樂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的藝術特色
孟 纓

小提琴協奏曲版《梁祝》發端于《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和1953年拍攝的越劇版電影,自從1959年問世以來,歷經歲月的淘洗依然熠熠生輝。想要改編如此久負盛名的作品,其難度可想而知。而王一巖導演及其團隊以全新的視聽形式,將《梁祝》精彩的演出用攝影機記錄下來,開創了中國拍攝交響樂電影的先河。該片于2014年8月在八一電影制片廠開拍,并獲得了中國愛樂樂團這樣的業界知名的實力派樂團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集團)的鼎力支持。這部由強大的團隊精心打造的影片在藝術上有著可圈可點的特色。
一、中西合璧
在探討中西合璧問題上,國際性與民族性是不能繞過的基礎概念。所謂國際性就是帶有超越國界的性質與特點,而民族性則指所要表現的元素立足于本民族的特性。“兼容并包、博采眾長”的國際化策略對于中國文化走出去必不可少,只有深深扎根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并在形式上大膽創新、積極與世界接軌,才是具有可行性的實踐之路。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自從1959年問世起,一直受到廣泛贊譽,堪稱中國交響樂史上的里程碑之作。這部被譽為東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經典音樂作品,因其西方交響樂的外殼和中國元素的內核的合理糅合而成為可資借鑒的中西合璧的有益范本。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之所以能夠獲得跨文化傳播的成功,不僅得益于其文本內容涉及“愛情”這一普世價值觀,更得益于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團隊成員的傾力合作。對西洋樂器與中國傳統文化因素特別是戲曲的形式方面的巧妙安排組接,是打通文化差異性的橋梁。而“通俗易懂、雅俗共賞”的觀眾定位也是助力其打破文化與地域的差異獲得廣泛的認同的原因之一。觀眾即便不知道《梁祝》的故事,也能夠通過旋律和演奏者的表演感受到音樂里面蘊藏的情感,從而產生情感共鳴。比如在梁祝二人一塊上學的段落,影片通過用近景、特寫等鏡頭紀錄兩對年輕情侶與一對老年夫婦在聽到此段時的喜悅表情,有力地佐證了這一特點。
王一巖導演的這部交響樂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有著以往《梁祝》的特色,整體保留了1959年版小提琴協奏曲的基本框架。首先,題材方面來自民間愛情傳說《梁祝》,講述反抗封建包辦婚姻、追求純美愛情的故事。影片又積極地賦予《梁祝》當下的時代意義,在傳統的主題中加入了現代人對人性和生命價值觀的思考,對自由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借鑒了西方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觀,很好地做到了“以我為主,為我所用”。
其次,在結構方面運用中國式的“啟、承、轉、合”布局。在“合”這一部分,采用中國戲曲中常用的大團圓的結尾方式。在影片前16分鐘左右的主創人員訪談及錄制現場的記錄影像中,影片的主角——小提琴獨奏者文薇提到“圓融”這個詞,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備受推崇的為人處世的至高之境,也是“以柔克剛”的道家之道。在最后的“化蝶”一段中,有情人終成眷屬,雙宿雙飛,這未必不是一種團圓。

中西合璧的成功實踐使得《梁祝》的魅力經久不衰,成為溝通中西方音樂藝術的橋梁和聯系中西方文化的紐帶,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和價值。對經典的重溫不只是紀念,更是對創新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與渴望。用紀錄片的形式將這一經典搬上銀幕,用電影的鏡頭語言重新詮釋新的時代背景下的《梁祝》,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交響樂《梁山伯與祝英臺》演奏現場
二、紀實與寫意相結合
導演王一巖女士充分發揮自己擅長拍攝紀錄片的優勢,完整地記錄了中國愛樂樂團演奏交響樂《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全過程,同時在演奏正式開始前插播對指揮余隆先生和新生代小提琴演奏家文薇女士的訪談。影片主創人員的交流在片頭處的真實記錄,對觀眾更好地了解接下來的演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指導意義。演奏開始后,對觀眾互動的鏡頭表現雖然表情略顯夸張,但同樣可以看到紀錄片的實質。演奏結束后接近十分鐘的余隆先生的訪談以及幕后花絮都透視出紀錄片的特征。
首先,影片片頭處在深藍色泛著白色珠光的背景下出現了畫外音——掌聲以及人聲嘈雜的聲音,在一種疏離感中顯示了現場在場感,更為真實。鑼鼓聲中,中國愛樂樂團團長李南出現在畫面中。伴隨著他介紹《梁山伯與祝英臺》的話音,余隆的正面近景出現在畫面中。當余隆談及自己接觸《梁祝》的緣起時,畫面中出現當年1959版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主創人員的老照片;接著,以畫外音形式伴隨著余隆的講述出現的是一段余隆回憶當年在愛爾蘭樂團擔任指揮、日本人西崎崇子擔任小提琴獨奏的資料回放。錄像和照片資料的介入,進一步增強了真實感。
接下來余隆先生和文薇女士的上句接下句式的“閃電式交替”的快速剪輯手法,加快了影片的節奏,使得訪談簡潔有力。同時,這種快節奏使得觀眾有一種探求下一步將會分享什么的心理欲求,產生一種懸念感,影片節奏的把握恰如其分,很好地兼顧了觀眾的觀影心理。影片中的主角——小提琴獨奏者文薇的訪談將她在詮釋《梁祝》故事中女主角祝英臺的切身心理感受和情感體悟與觀眾分享。比如文薇在談到“樓臺會”一段時,畫面切換到現場排練時文薇與代表梁山伯的大提琴手的交流,增強了敘述的真實性。對于“梁祝一塊上學”一節的情緒把握,余隆和文薇有共識:這一段一定要歡快。只有這樣才更符合人的天性,才能更加客觀真實地把人物的心理和情緒生動可感地表現出來。
在對余隆和文薇的訪談環節之后,導演安排了影片制作團隊的負責人間的交流,這種圓形團坐式的生活常態化的記錄有種隨意話家常的親和感,從而使得影片更加具有真實性。之后流暢的剪輯將化妝間中的準備真實地呈現給觀眾,使得觀眾也隨之有種預熱之感,產生即將聽演奏的期待心理。而演播室中攝像機鏡頭里的畫面和不時出現的拍攝現場實地拍攝的場景使得影片在真實性上更進了一步。
這16分鐘拍攝關于主創人員的訪談和交流和現場的攝錄情況,使得觀眾在未開始收看《梁祝》時對該劇的創作與片段的情緒把握有了一定的了解,對之后的觀影有很大的幫助。伴隨著9鏡2次的打板聲,“預備開始”的話音剛落,演奏正式開始。該片創新之處在于不是像越劇和徐克版的《梁祝》那樣采用故事化擴寫和想象來填充影片,而是采用紀錄片樣式,真實客觀的記錄演奏全過程,在確保演奏效果真實性的同時,通過觀眾的共鳴與不同角度、不同景別的交叉剪輯,使得影片避免了傳統紀錄片常見的沉悶、呆板、說教的弊病,兼顧了真實性與可看性。
在演奏結束之后導演安排了第三部分。首先,與片頭處呼應,畫外音表現謝幕后觀眾的掌聲和嘈雜的人聲,更加真實;接下來是中國愛樂樂團的全體人員合影,伴隨著與片頭處呼應的“咚咚咚”的鑼鼓聲,再一次凸顯了該片嚴謹真實的紀錄片特質。接下來對余隆和文薇的訪談以及幕后花絮都再次將觀眾帶進了真實的現場感體驗。
交響樂《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取材于家喻戶曉的中國民間故事,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其中最突出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寫意之法的借鑒和吸收。所謂寫意,與寫實相對,來源于中國傳統繪畫理論,講求“傳神”,講求神韻和創作者的志趣,不追求細節的完全摹寫。王一巖導演的這部交響樂電影有意識地借鑒了寫意的手法,將《梁祝》旋律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巧妙地借助現代技術手段呈現給觀眾,同時將音樂中要表達的思想感情和環境帶給觀眾,給予觀眾前所未有的視聽盛宴。
片頭處的畫面即已給人靜謐神秘、渺遠又深邃的心理感受。影片中寫意部分最出彩的運用在第二部分的主體段落——由實力雄厚的中國愛樂樂團帶來的這場盛大演出中。隨著“預備開始”的話音聲落,金色字體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字幕出現在藍色天幕這一背景中,隨之黃色字漸漸變小,像兩只蝴蝶般漸漸消失。開頭點題,這跟第一部分由李南團長說的話中引出的《梁祝》相呼應。接著,黃色光點消失變為兩瓣紅色花瓣,慢慢從天空中飄落下來,畫面中出現花,音樂舒緩,花枝就像相框,將江南水鄉攝入其中,鏡頭拉開,出現了經過特效處理的虛擬的“江南水鄉”舞臺。在這夢幻般的視聽語言中,特寫長笛,顯示聲音來自長笛,影片將長笛表現的內容具象化為實實在在的影像,運用特技呈現給觀眾一片春暖花開、鳥語花香的江南水鄉祥和之景,這種小寫意的手法不僅是影片對紀錄片體裁的一次大膽突破,對表達愛情主題以及融入導演對當下價值觀的看法也有一定的鋪墊作用。在同窗生情一節,影片從不同景別、不同角度進行拍攝,使得觀眾能夠從演奏者和觀眾的面部表情中獲知有效的內容信息,即便不知道《梁祝》故事,也能從中體會到音樂所要傳達的輕快愉悅心情;并多次運用虛焦手法和作純化背景處理,使得小提琴獨奏更加空靈和詩意化,而在“十八相送”和“樓臺會”段落中運用纏綿悱惻的音調表現了如泣如訴的感情。同時,為表現小提琴所指代的祝英臺與大提琴所代表的男主角梁山伯的十八相送欲言又止,樓臺相會互訴衷腸,影片運用特技表現,再次以純化背景的方法,將小提琴和大提琴置于烏云繚繞環境中,很好地映襯了情節的內容,同時情緒點也把握得十分到位。在影片最后“化蝶”一段中,特技做出花朵,慢慢盛開,從花朵里翩然飛出兩只瑩白的蝴蝶,雙宿雙飛,飛向高空,與象征著團圓的滿月以及畫面左下角的花朵三者一線,寄托了創作人員對花好月圓的希望。而這種帶給人無限遐思的留白有著大寫意的意蘊,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團圓的美好希冀形象唯美地表現出來,不僅給觀眾以心理上的滿足,也使影片在視聽上了無遺憾。而影片中聽眾對音樂的共鳴的呈現,如在聽到“化蝶”一段時,其中的一對年輕情侶手握在一起,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象外之旨,也是一種極富意蘊的廣泛意義上的寫意手法。
影片的環境和服裝設計也極富特色。正如在第一部分主創人員的交流中白麗君女士所說,對小提琴獨奏者文薇的服裝設計力求優美,裙子設計得飄逸,而發飾和眼角旁邊都有蝴蝶造型,在寫意化的手法中凸顯主題。
三、間離與縫合相結合
間離由布萊希特提出,意在不使觀眾太入戲,而是多給觀眾自由思考的時間。這種手法在中國其實并沒有太多市場,因為中國傳統的對大團圓結局的追求根深蒂固,以致于中國很少出現西方那樣純粹的悲劇。在中國,即便是悲劇也要傳達出“善惡有報”的倫理教化思想,在現實社會中無法解決的事情要放到神話或者語言故事中來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習慣用一種超現實的理想來對抗現實的殘酷。另一方面,在中國,縫合機制有著廣泛的通行證,在中國傳統的“起、承、轉、合”結構中,所有的矛盾、形成的裂隙都要解決。而紀錄片作為真實客觀的記錄類型,傳統的做法是不做過多干預和介入。王導的這部影片在這一辯證關系中做了新的積極有益的嘗試。
影片分為三大部分,開頭16分鐘主要是對余隆、文薇的訪談和影片主創人員的交流互動;中間部分是影片的主體部分,即由中國愛樂樂團傾力演奏的交響樂《梁山伯與祝英臺》;第三部分是大約十分鐘的對愛樂樂團的介紹、對余隆與文薇的訪談和幕后花絮。可以說,間離和縫合貫穿影片始終,是本片旗幟鮮明的一大特色。
在影片第一部分,對余隆的訪談中,根據談話內容插入的老照片和當年在愛爾蘭樂團指揮演奏《梁祝》時的錄像,將觀眾從訪談中抽離出來,使觀眾意識到這是一部紀錄片,需要大量的影像資料和老照片加以佐證,從而更加具有真實性。在余隆和文薇的訪談中不時插入文薇穿著淺灰色裙子演練的場景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二部分,即演奏過程的記錄部分間離效果明顯。通過觀眾、指揮和演奏者的“三位一體”的關系,形成套層結構:銀幕內部的“看與被看”的關系,以及銀幕外面觀眾與銀幕展現的影像的“看與被看”的關系。在這樣的巧妙構思下,影片通過多角度、多景別全方位的展示,大全景俯拍,橫移表現環境,樂器的局部特寫,觀眾的近景或特寫,都在一定程度上對主要演奏者的演奏有種間離效果,給觀眾足夠的思考時間。三對夫妻和戀人與演奏者的活動一定程度上也提醒銀幕下的觀眾這是在觀影,從而產生間離感。
第三部分中國愛樂樂團團隊集體合影等以及對余隆和文薇的采訪同樣具有間離效果,如插播姜文講話的鏡頭不禁會使得觀眾發問,為何要插播上姜文的鏡頭?這就給了觀眾從劇情中跳脫出來自由思考的時間。而這一部分在演播室和現場實錄中,不時出現攝像機中呈現的錄下的視頻使得這種間離效果更加明顯。
同時,影片仍然沿襲中國傳統的縫合機制,不斷地制造沖突同時又不斷地填補裂隙,不斷化解沖突,在設置障礙與破障之間尋求平衡。這一特點表現最明顯的是在第二部分。在“同窗生情”一段中,音樂旋律輕松明快,聽眾也露出會心微笑;在“投墳”一段中,在這一情緒的制高點,聽眾也為之流淚。還有其他幾處淚點:“十八相送”“抗婚”“樓臺會”“哭靈”等段落,聽眾為之落淚是因為入戲,而演奏者落淚也是因為入戲,這都是縫合機制的作用。
作為中國首部交響樂電影,王一巖導演的紀錄片《梁山伯與祝英臺》在視聽語言上有著積極大膽的開拓和創新,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特色。這在一定程度上對紀錄片的類型開拓,特別是在音樂與電影的跨界交融方面有著不容小覷的歷史地位。而影片主創人員和中國愛樂樂團的強強聯合也為觀眾帶來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音樂與電影的浪漫邂逅的視聽盛宴,值得期待。
1.趙鵬程.對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音樂闡釋[J] .大舞臺,2012(12) .
2.王婉如.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魅力何在?——對該作品50多年的研究述評[J] .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2013(3) .
3.孫惠柱.戲劇藝術從“間離效果 ”到“ 連接效果 ”——布萊希特理論與中國戲曲的跨文化實驗[J] .戲劇藝術,2010(6) .
孟 纓: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影視系
責任編輯:蔡郁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