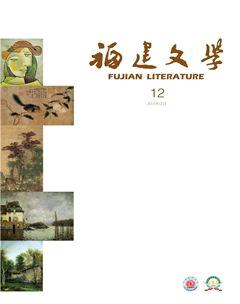你好,憂傷(外一篇)
傷水
莫名的感傷。我浸淫于這種久違的感受:無限的水波,深邃、暗藍,在腦海里由內到外擴散。那憂傷的波紋,磨蹭你,推搡你,直到把你徹底湮沒……
想起三十年前一個四月的薄暮,天臺石梁飛瀑,白天嘈雜的游客散盡,石梁瀑布在我腳下孤獨地摔下山崖。而山谷內寺廟的晚鐘當當響起,隱在群山里的群鳥突地涌向天空,點點滴滴,點點滴滴,最后融入天幕,渾然一體。我感覺我也是其中的一小點翅膀了,沒入了空蒙,消解了,虛化了。那刻,內心恍然,繼而無限感傷。
再想起二十年前的八月,那霧中的馬蹄聲:在新疆天山天池,大霧籠罩,湖水和周遭一切悉數淹沒,而耳邊清晰地響起馬蹄聲!不只一匹,該有十來匹馬在揚蹄奔馳,蹄聲就在身邊,急驟、短促、清脆。急忙循聲奔去,不見馬、不見馬群,盡是彌漫著的濃重的白霧。馬蹄聲轉瞬消失了,仿佛被茫茫霧氣神秘吸納,又仿佛根本不曾發生。那刻,內心恍然,繼而無限感傷。有太多的誘惑就在身旁,你無法觸摸;有曾經的發生由于轉瞬消失,你無法確認。
——那年女兒點點兩歲,還不大會說話,新疆回來后,某天我抱她到一個水潭邊,她看著平靜的水潭,嘴里竟發出模仿青蛙的叫聲。平時常抱她來水潭邊,聽熟了蛙鼓吧。女兒的“呱呱”聲,不自覺地使我想起那霧中的馬蹄,可能都是聽得到聲音見不到發音物的緣故。而小女兒情不自禁的蛙音模仿,給我的不是感傷,而是心中涌起對自己骨肉的無限憐愛。想起八十年代末,我二十郎當歲,剛放棄公職下海。每次出差回來,特別是從喧嘩熱鬧的城市回到我的小縣城,我會到文化宮舞廳的角落棲坐片刻,燈光黯淡,我的思緒漫無邊際,使得舞曲可有可無。那刻,我往往體會到陣陣感傷。是什么引發少年的落寞情懷呢?我已無法記憶。或許是追求的失意,對不可知的未來的擔憂,或許是現實與想象間的反差,或許是旅途的經歷和感受使然:那時出差經常是住宿地下室、澡堂;坐火車時連硬座票也買不到,攤張報紙,躺入他人的座椅下,閉上眼睛,身子隨著火車,哐當哐當地一路搖晃。人在旅途,on the way,“哪只船是家?沒有一件帆/不穿在身上/總是有珍貴的笑容,總是有/溫熱的手掌/熟悉后陌生//為何世界寬廣/而生命總在旅途……”
1988年11月,海南島,生平第一次遭劫,身無分文,并領會了一句終身受益的教導:“我可憐你,誰可憐我。”獲得幫助后,在海口到廣州的長途夜車上,與一車的盲流、民工、游客混雜,車內糟糕的音響一遍遍放送當時正流行的歌曲《昨夜星辰》,車窗外的南國黑黢黢又幽深深。劫后的心情、漂泊的境況,加上當時戀愛的不如意,與那“昨夜地、昨夜地星辰已墜落,消失在遙遠地銀河……想記起卻又已忘記,那份愛換來的是寂寞……”的歌聲很是合拍。那一夜的感傷,直到黎明時分下車在當時中國行騙、偷竊、販毒最為集中的廣州站,還是恍恍惚惚。次年到舟山買魚販賣給臺商,行至街口聽那“馬不停蹄的憂傷”,再次年蹲在出租房聽高明峻的“那種心跳的感覺”,都很是莫名的惆悵。“傷心太平洋”,我從不鄙視流行歌曲,可能是我的階段性感傷往往會對應一支“低俗”的流行歌曲的緣故吧。雖然,當時我的詩歌寫作正是弘揚大氣、陽剛、粗獷的“海洋文化”,我提倡海明威式的硬漢文字和硬漢做派,喜歡“壓力下的風度”,但誰沒有“溫柔的部分”呢?海明威不也正是“迷惘的一代”嘛,何況中彈9處、頭部受傷6次、腦震蕩12次、車禍3次、被取出過237塊彈片而不死的他,不還是自己用雙筒獵槍轟掉自己半個腦袋?——海明威一齊扣動兩個扳機的那一瞬,不是憂傷,而是憂傷的頂端——絕望。
2001年我到尼日利亞,飛機從上海到北京,從北京到倫敦,從倫敦到拉各斯,一口氣飛了二十五個小時,機內不準抽煙。雖三次轉機,但時間銜接緊湊,無法抽煙。對我這個大煙民來說,真是太殘酷了。機內除了駕駛員,所有人昏昏入睡,惟我輾轉反側,焦躁難安。幸得機上播放陳可辛導演的電影《甜蜜蜜》,讓感傷的情緒代替了我的極端煩躁。八十年代中期去香港打工的“黎明”和“張曼玉”由于孤獨成了朋友,而又各不是“理想”所在而分手,“黎明”接來無錫的女友,“張曼玉”做了黑社會二奶,但他們也終于發現自己一直愛著對方。緊接著一場變故,當兩人再次相遇時,他們站在紐約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櫥窗前,一起聽著鄧麗君去世的消息,四目相對,耳畔傳來的又是那首他們在香港時唱過的《甜蜜蜜》。你的笑容這么熟悉,在哪里見過你。——電影是靠細節來感人的,正如感傷的觸動,也是一個個經意或不經意的細節。伴著那歌那電影,無數往事,走馬燈一樣晃過:
……第一次聽鄧麗君時的巖洞般的玉城中學宿舍;第一次背起黃色的解放軍挎包浪跡四方,回到溫州碼頭口袋里只余的三毛鎳幣(多年后新婚出游回來也是如此);我寫的第一首詩;我作的第一首歌詞;在寒冬中的臺州師專大教室,我裹著被子通宵書寫《詩歌氛圍說》;我暗戀過的女孩,“荒涼的山岡上站著四姐妹/所有的風只向她們吹/所有的日子都為她們破碎”(海子《四姐妹》);更有黑暗中阿莊對我說的那句震撼的話語,四歲的女兒聽《賣火柴的女孩》時那眼中忍不住的淚水。
……我虧過的錢與賺來的票子;澆灌海水后販賣的大同煤;武漢長江上泊著的巨大的杉木筏;綁著腿的梭子蟹;塊凍的紅頭宮蝦和同樣塊凍的日本大坂;舊機床市場上低價買來的大車床和加工出口的黃澄澄的銅閥門。
……祖父皸裂的掌心攤著的那幾顆“山里紅”;父親書寫在老式雕花櫥柜板門里的生辰八字;外公用中藥包裝紙精心包裹的那排“古書”;祖母用瓷碗燜給我吃的米飯,倒扣在一家人吃的整鐵鍋番薯絲內;“文革”中背我逃下“牛牯頭嶺”的遠房姑姑(嫁到哪啦?);落水時拉我上岸的小姐姐(叫阿梅?);靠在產床上阿莊笑意漣漣的雙眼,正對著從寧波趕回的氣喘吁吁的我……
而最令我難忘的是2000年1月,因為某種幾乎莫須有的原因,我被某機構傳喚詢問,半天下來,仍呈僵持對立狀態。隔墻就是女兒剛讀一年的小學。下午放學的電鈴聲響了,孩子們群鳥般的聲音傳來。我六歲的點點肯定在其中,她馱著書包,怯生生地爬上1路公交車,再跳下來步行,用掛在脖子上的鑰匙旋開樓下的鐵門,拾級上樓梯,打開自家的防盜門,進屋,攤開本子寫作業,等待平常六點多下班的我。等我一起吃飯、等我在她作業上簽上家長名字,等我給她講段小時候的故事,等我一起進被窩睡覺,小手緊緊繞著我的右臂。而我在被莫名地詢問,她媽媽遠在香港上班。放學的鈴聲響了,我要馬上回家,我女兒在等我。而我還不知道什么時候能走。我不知道。放學的鈴聲響了,我內心沒有悲憤,而是層層疊疊的憂傷,無窮的蒼涼。自由才是人的第一需求,其次是,平安和健康。
你好,憂傷。書柜中那本多年前買來的,法國女作家薩岡十八歲寫的青春叛逆小說,被翻譯成《你好,憂愁》,一字之差,讓我哽噎般難受,應該是《你好,憂傷》。隨風而逝的憂傷,就像那夏天暑期里的愛情。你好,憂傷。從不會背書的我,會記得高更在《諾阿,諾阿》結尾記錄的那支毛利土著哀歌:南方的風啊,快吹啊/快吹到那座小島/我的情郎正坐在他喜愛的樹下/把我的思念告訴他,把我的悲傷告訴他。——我發現許多優秀的詩篇是在憂傷下寫就,或傳達出美妙的憂傷而動人和不朽。男孩子蘭波1870年在《流浪》末尾悲吟,“我在幻影中吟誦,拉緊/破鞋上的松緊帶,象彈奏豎琴/一只腳貼近我的心!”七十年后猶太女詩人薩克斯在《當你們站起來去死》里,悲傷得劈頭就問:“當你們站起來去死,/誰倒掉你們鞋里的沙?”而我更同意“蠟給女人,青銅給男人”,曼德爾斯塔姆在《悲傷》里這么寫。
我可憐你,誰可憐我?
我棄教從商那年,海南島海口市暮秋的一個黃昏。我永遠記得那個時間:1988年11月8日晚六時。那一刻我被搶得身無分文。海口下午六時天色明朗,我去投宿步行至解放路和平里時,夾在左腋窩的公文包突然被人從身后抽走——急轉身,只見一個著牛仔服的家伙正撒腿折身往街邊小巷狂奔。我大喊著追去,在小巷的轉彎處被早已埋伏的搶劫合伙者不知用啥物砸中頭部,被擊倒后再站起,搶劫者的腳步聲已遙。——解放南路和平里,負責治安的是幾公里外的博愛南派出所。如此這般,這個既“解放”又“和平”還“博愛”的地方,我被幾個絕對友好的同胞不友好地掠劫一空。
然后我想到去報案。我攔住了一輛出租三輪摩托,開摩托的得知我身無分文就“呼”地一聲駛遠了。我攔住了第二輛,坐上后誠懇地向開摩托的青年說明我的困境:第一次來海口,剛下車就遭搶,饑疼交迫,整個海南島舉目無親,請他將我免費送到派出所,他喝到:下去!我纏著要他可憐可憐幫我一次忙,他回答我的是一句炸彈般的話:我可憐你,誰可憐我?
我可憐你,誰可憐我?!
我鄭重地記下這句話,這句可能是銘心刻骨的語言,不是要說明人世間缺乏溫情和友愛諸如世態炎涼此類的意思,這段小經歷最終也是有人“可憐”我才得以順當回來。我想說的是當時我置身窘境時的心態和以后對這句“名言”的感悟。
我感到又遭受了一次痛擊,僅一下就把人擊暈的那種痛擊——我可憐你,誰可憐我——沒有人可憐你,只有你自己可憐你自己:充分自立,放棄所有縛系的纜繩和可能依傍的港灣,自身把握自身的命運,自身的命運把握自身!而我們依賴得是不是太多了,有太多不滿足又不肯邁出那其實虛無的門檻——患得患失、瞻前顧后、首鼠兩端的人格形成,實在是民族的悲哀,由此帶來的人種的退化甚至是全人類的悲哀。
上述最后一句絕對不是當時的感慨。當時實在是容不得有什么感慨。那無形的痛擊后我在心里攥緊拳頭,我自責:這點小麻煩要人家可憐什么!當我佇立街頭惘然四顧,當我那夜宿于派出所車庫和成群蚊蟲混居,當我次日喝自來水充饑時,我決心就是趴車、行乞也要靠自己的力量回來。“我可憐你,誰可憐我”,教我從悲涼中感觸了激奮。是的,我們本來就應該是一無所有,工作、福利、醫保等都是被賦予的,將這些都還給賦予者,自身營造自身,能不能生存?我開始為如何把握自己而深深焦慮。
“我可憐你,誰可憐我?”在這句偉大的教導下我將自己放逐到還不是充分自由競爭的沼澤中去了。我對岸說:我永不回來。我將成為魚,我將一直游動,哪管能否游到目的地。信心和毅力,我還堅信意志的永恒。我在游動的過程中,自身首先得到了解放。
這解放的代價是遭遇一次次的孤立無援、四面楚歌,上帝的手掠走了無數機遇和幸運,余下的是艱辛和掙扎。我可憐你,誰可憐我?沒有人可憐!也沒有人接受你的投降,就任被消滅。但我們說:我們不能被打敗。就像海明威《老人與海》中所寫的那種人:你可以消滅他,但你永遠打不敗他。我崇敬瀟灑的大玩家,如那個叫博雷爾的矮個法國佬,離開老家時身無分文,憑借款經營快餐店為生,后來他閃電般地擴展到1000家餐廳和旅館,資產300多億美元;當1986年懸在其頭頂的巨斧墜落時,他卷起鋪蓋搬回塞納河畔的舊家,并對來訪者驕傲地說:我發過財,可我的妻子沒有換,還是原來的那一個。他從零到零,可他最后說:我從來不服輸,我還要出去。——誰能打敗這樣的人?
細思忖之,人之初全是兩手空空,你沒有什么可牽掛的,沒有什么不可放棄的;照樣,你什么都可以擁有,什么也都可以占領。《北京人在紐約》中那個王啟明,從象征著我們現有體制賦予者身份的“北京”突地甩到沒有人可憐的殘酷的競爭生存空間“紐約”,頓感茫然無措,繼而“進入”然后“同化”。人只有在布滿挑戰和陷阱的生存環境,才最有生命力。我很想說:這個時代要的不是驕兵,而是戰士!
讓我接著把那遭劫的結局講完。次日中午,萬般無奈中我想象浙江省政府該在海南設有辦事處,設法得到地址并步行兩個多小時,找到了辦事處暨大東南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在其處飽餐一頓后才如實托出自己的遭遇,不再要求“可憐”的我得到了幫助。我握手告別頗具聲名的辦事處領導歷德馨同志,至今我仍不能忘記他那雙手給我的感覺:柔軟且溫暖。
責任編輯 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