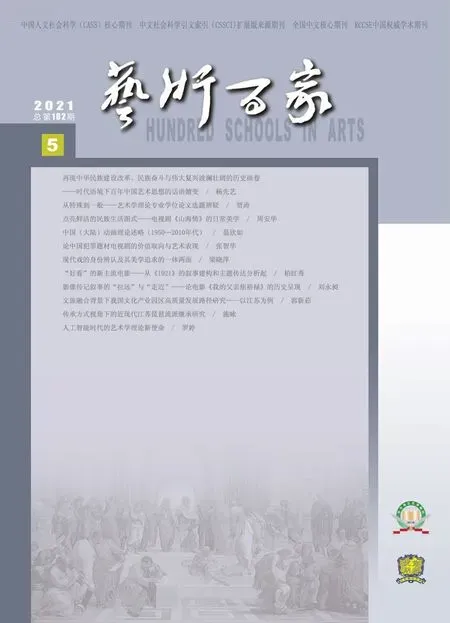氣·骨·神·韻
張建軍
摘要:氣、骨、神、韻為中國書畫中的精神必性范疇,它們聯系著作品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精神價值、藝術特質。“氣”在中國古代思維中,其實有著多重含義。繪畫與書法中的“氣”,聯系著生命和精神這兩個要素。氣是生命,也是可以感動人的精神力量。骨與力量有關,而骨的力量,是源自于一種內在的力量,或者說一種人格的感染力并形成骨力、骨氣、風骨、氣骨等藝術品評術語。神這一范疇在繪畫中與在書法中略有不同,繪畫中的神,來自于被畫對象——人物——的神。書法的神,是“風神”,是由書家的技法高超的書法行為造就而成的書法作品的神。氣和骨都與作品的感染力及藝術價值相關,而“神”是這種感染力的核心。神往往與想象力相聯系。韻與神相似,都處于藝術價值、藝術感染力的中心。韻是一件書法、繪畫作品是否可以稱得上藝術作品的試金石。與神一樣,韻是超越于形和單純技術的一個概念,標志著書法、繪畫批評擺脫“用”的標準與“技”的標準,確立起超越性、精神性、藝術性的標準。
關鍵詞:中國書畫;精神性;生命力;感染力;精神價值;藝術特質
中圖分類號:J20文獻標識碼:A
在中國書畫作品中,“氣、骨、神、韻”都屬于作品的精神性范疇,其與書法、繪畫作品的物質性范疇——“形”——的關系如下:
基本層次:形;
中間層次:形之中所含蘊的生命力、感染力——氣、骨;
最高層次:超越于形的精神價值、藝術特質——神、韻。
一、氣
我們先來看“氣”這一范疇。
根據中國古代傳統思想,“氣”在中國古代思維中,其實有著多重含義。首先,氣聯系著物質,氣之凝結,則成“物”,甚至人也是氣之凝結的結果。其次,氣包含有能量,氣是生命的依據,也是世界之運行、變化的依據,氣的運行,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動力。再次,氣不僅限于物質、能量這兩個層面,氣也聯系著精神,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通過氣而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構成完整的世界。
繪畫與書法中的“氣”,聯系著生命和精神這兩個要素。
氣是生命。《淮南子·原道訓》說:“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膋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黑白、視丑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顧愷之《論畫》評《小列女》說:“面如恨,刻削為容儀,不盡生氣。”謝赫《古畫品錄》評丁光畫:“雖擅名蟬雀,而筆跡輕羸,非不精謹,乏于生氣。”氣是生命之氣,氣與生是一體的。
氣也是可以感動人的精神力量。
鐘嶸《詩品序》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
謝赫《古畫品錄》評衛協書法:“雖不該備形妙,頗得壯氣。凌跨群雄,曠代絕筆。”同書評晉明帝書法:“雖略于形色,頗得神氣。筆跡超越,亦有奇觀。”這里的氣,都是超越于形似之上的一種感染人的精神力量。
袁昂《古今書評》說:“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又說:“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這種風氣、意氣都是一種深深地打上了主體印記的作品的精神力量。
氣既是作品中的氣,又是來自于書法家、畫家主體的氣,通過這種主體的氣的注入,作品才具有了“氣場”的效應,書法、繪畫作品才能感動人,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書論中談到的“意氣”往往與這種主體的氣相關。
“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傳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后》)。意與氣相連而言之,這里的意氣,正是主體的充實之氣,也是將要被注入于作品中的氣,它將直接導致作品的生氣、生命力、感染力的成立。
二、骨
再來看“骨”這一范疇。
謝赫《古畫品錄》提到的“六法”,其二為“骨法用筆”。
早于謝赫,顧愷之畫論中也多次提到骨,其《論畫》中有:
評《周本紀》曰:“重疊彌綸有骨法”,評《伏羲神農》曰:“有奇骨而兼美好”,評《漢本紀》曰:“有天骨而少細美”,評《孫武》曰:“骨趣甚奇”,評《醉客》曰:“多有骨俱”,評《列士》曰:“有骨俱”,評《三馬》曰:“雋骨天奇”。
在書法中,“骨”用得更普遍。略舉如下。
(傳)衛鑠《筆陣圖》:“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圣,無力無筋者病。”
(傳)王羲之《書論》:“余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鐘繇書,骨甚是不輕,恐子孫不忘不記,故敘而論之。”
王僧虔《論書》:“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
王僧虔《筆意贊》:“骨豐肉潤,入妙通靈。”
蕭衍《梁武帝又答書》:“純骨無媚,純肉無力。”
陶宏景《陶隱居又啟》:“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
繪畫中的骨,與相學中的骨相之說有關,與人的骨相有一定的關系;書法中的骨與書法中的具體的筆畫有關,一般指那種瘦勁的筆畫中所包含的力量。繪畫與書法中的“骨”的概念相互之間有影響,“骨法用筆”一詞,顯然就受到了書法的影響,而書論中把骨看作力量的標志,也與骨相之說有關,并可能受到了繪畫中的秀骨清像的風氣的影響。
總之,骨與力量有關,而骨的力量,是源自于一種內在的力量,或者說一種人格的感染力,因此,骨除了與力連用之外,往往還與氣、風連用。形成骨力、氣骨、骨氣、風骨、氣骨等藝術品評術語。
謝赫《古畫品錄》評曹不興說:“迨莫復傳,唯秘閣之內,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虛成?”
袁昂《古今書評》說:“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蕭衍《書評》說:“王僧虔書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流氣骨。”
日本學者河內利治說:“作為書法審美范疇的骨字,是一個抽象概念,是產生能量、精力——力的根本和生命體。”①
南朝文藝理論名著《文心雕龍》中有《風骨》一篇,其辭曰:“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
《文心雕龍》是從文學立場來談風骨的,但風骨、氣骨,作為作品的一種品質,聯系著作品的力量感,是作品感染力的保證,這一點,繪畫、書法與文學是一致的。
三、神
再看“神”這一范疇。
神這一范疇在繪畫中與在書法中略有不同,繪畫中的神,來自于被畫對象——人物——的神,由承認被畫的人的神,到承認繪畫作品本身具有的神,經歷了一次轉換,即對象的神轉換為作品的神。書法的神,是“風神”,是由書家的技法高超的書法行為造就而成的書法作品的神。書法的神,沒有對象之神這一環節。換言之,繪畫的神來源是“對象+畫家”,而書法的神來源是書家。
傳神是超越于存形的一個層次,顧愷之的傳神論是對“存形莫善于畫”的一個突破與超越,畫固然是要形,但畫還要超越于機械的工匠式的存形,而要達到“傳神”的高度。
《世說新語·巧藝》載顧愷之畫事兩則: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在顧愷之看來,人物之神與人物之形即所謂“四體妍蚩”相比,具有更本質的意義,繪畫的價值就是要傳達出這種“神”。形與神之間,神是第一位的,形是第二位的,神是目的,形是依托。
這種具有超越性,傾向于精神層面的“神”,具有反映對象、繪畫作品、創作主體三個維度。神首先是繪畫所描繪的對象的“神”,這種“神”在當時是與所謂魏晉風度分不開的,是對魏晉士大夫之富有個性色彩的人格的一種描繪與反映。這種魏晉風度、這種士大夫人格、精神體現在繪畫中,仍是對象之神,是人物之神,但由此形成了作品的藝術價值,藝術的神彩、風神,那么,神同樣也可以在作品層面找到,神同樣可以用來描繪作品本身,而不僅僅是作品所反映的對象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品的神來自于畫家高超的藝術創造力,這種藝術創造力也可以用神來形容,而這種創造力最終要凝結于作品,也就是說作品中同樣也凝結了創作主體即畫家的神。
王僧虔《筆意贊》說:
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于手,手忘于書,心手達情,書不忘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乃為《筆意贊》曰:剡紙易墨,心圓管直。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先臨《告誓》,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植槊,勒若橫釘。開張鳳翼,聳擢芝英。粗不為重,細不為輕。纖微向背,毫發死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
“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同樣宣告了書法重神的超越性觀念,因為書法“非仿象”性質,書法之神,沒有一個描繪、反映對象之神的問題,而直接與作品之神、創作主體之神聯系起來。
書論中的神與書寫過程的玄妙莫測也有密切關系,書法創作,與繪畫相比,其技術的復雜性、規定性較低,但對創作主體的精神狀態的要求更高,“必使心忘于手,手忘于書,心手達情,書不忘想,是謂求這不得,考之即彰”,正是對這種精神狀態的一種描繪。
(傳)王羲之《書論》也說:“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學無及之。”對主體的精神境界、精神狀態的要求,在書論的尚神、尚妙觀念中,具有重要意義。
氣和骨都與作品的感染力及藝術價值相關,而“神”是這種感染力的核心,一部作品沒有了“神”,就沒有了“君形者”,作品就是死的。
正因為神是一種超越性概念,所以神往往與想象力相聯系。
顧愷之《論畫》:“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按顧愷之的觀念,臺榭之類的建筑畫,其中缺少遷想妙得,即天才的想象力的發揮,因此,“一定器耳”,即往往缺少藝術的“神”、“韻”,這種看法正確與否姑且不論,但以是否需要“遷想妙得”來判斷藝術品質,也具有啟發意義。
四、韻
從代表著作品的感染力及藝術價值這一點看,韻與神相似,都處于藝術價值、藝術感染力的中心,但韻這一范疇,從來源與含義上都和神具有一定的區別。
“韻”,是一個來自音樂的詞。日本學者金原省吾說:“謝赫之韻,皆是音響的意味,是在畫面所感到的音響。即是:畫面的感覺,覺得不是由眼所感覺的,而感到恰似從自己胸中響出的一樣,是由內感所感到音響似的。”②從人類歷史來看,人類音樂的起源是非常古老的,而且,音樂不同于其他藝術,音樂完全沒有具體形象,音樂更抽象,古希臘哲人畢達哥拉斯就認為音樂與數學是一體的。正因為音樂更抽象,它也成為人們心目中在純藝術的概念出現之前的“純藝術”的代表,于是音樂性的標志“韻”就成為了繪畫與書法的藝術性的代名詞。
謝赫《古畫品錄》列六法其一即“氣韻生動”,在對具體畫家的評價中亦多用“韻”字,如:
張墨、茍勖,風范氣韻,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厭膏腴,可謂微妙也。
顧駿之,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謹細,有過往哲。變古則今,賦彩制形,皆創新意。
陸綏,體韻遒舉,風彩飄然。一點一拂,動筆皆奇。
毛惠遠,畫體周贍,無適弗該,出入窮奇,縱橫逸筆,力遒韻雅,超邁絕倫。其揮霍必也極妙。
戴逵,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善圖圣賢,百工所范。茍、衛以后,實為領袖。
清代梁巘在評論歷代書風的基本特征時,說:“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梁巘《評書帖》)韻是魏晉士大夫從其魏晉風度、音樂、文學、書法、繪畫中提煉出來的一種藝術特質的總稱。
與“神”一樣,繪畫中的韻,首先是來自繪畫的反映對象的韻,然后才凝結成作品中的韻。書法由于沒有具體的描繪、反映物象對象,所以對書法主體、書法行為,乃至書法作品本身給予了更多重視,書法中的“韻”,與書家的“意”關系十分密切,有時,書論中提到的意,其實就相當于繪畫中的“韻”。
(傳)衛鑠《筆陣圖》說:“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后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后者勝。”意是創作主體的意,書家的意的統攝,意的投入,決定了作品的成敗,決定了作品的韻。
(傳)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后》說:“心意者,將軍也。”
(傳)王羲之《書論》說:“凡書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其后,未作之始,結思成矣。”
這里的意都是主體的意,主體的意通過思的過程和書寫的行為貫徹于作品,保證了韻的品質構成。
在王羲之尺牘中,意有時就是指作品的藝術的意蘊、藝術韻味,“意其實就相當于“韻”。
《與友人書》說:“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鐘、張故為絕倫,其余為是小佳,不足為意。去此二賢,仆書次之。頃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
這里“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句中,“意”都可換成“韻”,不過韻偏重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那種韻味,意也指這種韻味,但仍讓人聯系到這種韻味是創作者的主體之意的一種投射。
韻與氣連用成氣韻,與神連用成神韻。氣韻、神韻分別成為中國書畫品評論中的最常采用的術語之一。
氣韻,聯系著作品的藝術韻味(韻與韻味相關),聯系著作品的氣質(氣與氣質相關),聯系著作品中的力度(氣與氣力相關)。
神韻,聯系著作品的風神,聯系著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藝術創造的神奇幻化、變動無方,也聯系著作品中的超越于表層的更深遠的隱喻與想象。
韻是超越性的概念,是一件書法、繪畫作品是否可以稱得上藝術作品的試金石。與神一樣,韻是超越于形,超越于單純技術的一個概念,它標志著書法、繪畫批評擺脫“用”的標準與“技”的標準,而確立起超越性、精神性、藝術性的標準。(責任編輯:徐智本)
①[日]河內利治著,承春先譯《漢字書法審美范疇考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頁。
②轉引自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