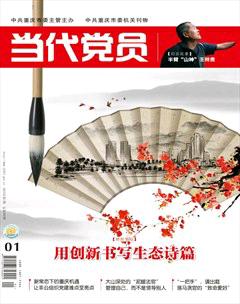“一把手”,請出庭
陸睿


2014年,王中云59歲,幫別人駕駛客車。
他在合川區肖家鎮的家里,收藏著一份上世紀80年代的行政訴訟《判決書》。
《判決書》是油印的,上面印著“(1987)合法行字第01號”的文件號。
在“01”數字背后,王中云早年的一次“壯舉”躍然紙上。
“民告官”第一人
1986年以前,王中云和家人住在肖家鎮哨馬街103號。
那是一排土墻房,很擠,也很寒磣。
1986年4月,王中云攢了點錢,決定搞個“大工程”——把臨街四間屋改成一樓一底的樓房。
說干就干。
接下來一些日子,新屋一點點長高,王中云心里偷著樂。
卻不想,合川縣(現合川區)建設委員會和鎮政府干部找上門來。
“你家房屋施工未得到審批,而且侵占了部分規劃街道——得停止施工。”干部們說。
王中云跳了起來:“開工前,我的申請村主任簽字同意了,我又交到鎮里,鎮里管事的干部也口頭同意了!”
一場口水戰之后,雙方不歡而散。
第二天,王中云收到鎮政府停止施工的書面通知。接下來一些日子,縣建委和鎮上干部也屢次上門勸阻。
王中云都置之不理。
新屋蓋好了,縣建委的《處罰通知》也送到了——罰款200元,責令拆除侵占規劃街道的房屋。
“管事干部同意了的,憑什么罰款?”王中云怒氣滿胸。
“上法院——行政訴訟!”有人支招。
第二天,他一紙訴狀,把縣建委告上法庭。
他并不知道,自己這個案子,成了重慶市各級人民法院成立行政法庭一年來受理的第一案。
1987年2月26日,縣法院開庭審理此案,上百人擠進現場旁聽。
訟戰的焦點是“王中云修房是否屬于無證施工”。
控辯結束,審判長宣判——因為拿不出核心證據,王中云被判敗訴。
當年,他拆了規劃紅線內的房屋,并承擔了訴訟費20元。
“壞就壞在‘口說無憑——如果當初拿到了書面證明,哪會有這些惱人事!”從此,王中云干任何事都要先“辦手續,存憑證”。
王中云訴縣建委一案,開啟了重慶“民告官”新紀元。
“敢為天下先”
王中云計劃修屋之際,應屆畢業生劉春焱告別母校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進入市人大當了干部。
一報到,他就接到“大任務”——參加制訂《重慶市行政訴訟暫行規定》。
“當時,這項立法在全國尚屬首例。”憶及當年,劉春焱仍熱血沸騰。
上世紀80年代,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各類利益糾葛和矛盾激增,群眾和政府部門頻現摩擦。
如此摩擦,如何解決?
1983年,《民事訴訟法(暫行)》指出一條解決之道——行政訴訟,即普通公民、法人或其他社會組織通過司法程序,以相關政府部門為對象展開訴訟爭取合法權益,俗稱“民告官”。
可是,《民事訴訟法(暫行)》并沒有對行政訴訟具體程序作出規定。
“因為缺乏具體法律程序支撐,法院即使面對行政訴訟也不知如何受理——就像有了路牌,路卻沒修通。”一位律師如是說。
而修通這條“路”,就是劉春焱和同事們的努力方向。
其時,剛剛成為計劃單列市的重慶市,擁有了一定立法權。
通過動用立法權,重慶啟動了“鋪路”之戰。
“重慶市做此項工作時,《行政訴訟法》尚未頒布,我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劉春焱說。
在1986年那些充滿激情的日子里,市人大立法團隊以訴訟基本程序為主線,對每一個訴訟環節都進行謹慎論證,逐項作出了操作規定。
立案條件、訴訟主體、審理程序……隨著一塊塊“攔路石”被搬開,“民告官”之路通暢起來。
1987年,《重慶市行政訴訟暫行規定》出爐,舉國矚目。
“《規定》出臺,意義有二。”劉春焱說,一是積累了行政訴訟的實戰經驗,為隨后出臺的國家《行政訴訟法》提供了立法經驗和操作依據;二是在法理上破除了“民不與官斗”的傳統社會倫理,讓群眾在官民矛盾面前不再“忍氣吞聲”。
1990年,《行政訴訟法》出臺,行政訴訟受理體系迅速覆蓋全國。
“路”雖通,卻并不平坦。
異地審理避“干擾”
1995年,法官汪華富遭遇到了“民告官”審理的坎坷。
那年,他調任華中某省一區級法院行政庭首任庭長。
上任頭兩個月,汪華富就連續受理了多起行政訴訟,被告都是區政府。
在受理行政訴訟案件過程中,常會有各級領導跟他“打招呼”。
“哪個區領導不比我大?哪個都可以‘領導我!”他說。
問題出在管轄權屬上——行政訴訟案件受理主要采取屬地管轄,即本地法院受理本地行政訴訟案件。
可因人、財、物都受制于當地,讓地方權力干擾行政案件受理有機可乘,導致一些案件不能判、不敢判。
地方行政權力“插手”,成為“民告官”的第一大阻力。
如何規避?
2007年,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長楊煜參加了一個“試驗”。
“試驗”核心是異地審理——即讓本地法院受理外地行政訴訟。
“我們選取了轄區內的墊江、武隆、南川、涪陵、豐都五個區縣,開展行政訴訟異地審理,以此避開地方行政干擾。”楊煜說。
同樣的試驗,華中一些省份也在進行。
引得各地爭相實踐——異地審理有何魅力?
“因為它瞅準了‘干擾的命門。”一位法官評價。
“現在,否決權全部收歸三中院——作為中級人民法院,三中院人、財、物都直屬于市高級人民法院,不受區縣節制,不用看區縣‘臉色。”楊煜說,“原告可以申請異地審理——離開了本土利益網絡,‘游說也就無門。”
至此,“民告官”第一大阻力消解。
“告官不見官”
和基層法官們不同,讓律師楊廷瑞撓頭的,是“民告官”的另一大阻力——“告官不見官”。
“我和一個政府部門打官司,他們就來了一個副職領導干部。”
“我更慘——他們就派了一個工作人員。”
…………
隨著“民告官”制度完善,地方行政“亂插手”現象正在消解。可是,面對行政訴訟,一些行政部門又開始消極回避。
對這個問題,市人大代表楊家學深有體會。
作為律師的他,曾代理過20多件行政訴訟案。“在這些案子的庭審中,被告部門‘一把手無一出庭。”他說。
“委托出庭人不了解具體工作,也做不了主,老是要‘回去商量,反復開庭,浪費司法資源,同時也降低了審理效率,讓起訴的老百姓怨聲載道。”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王振宇直陳“告官不見官”兩大危害。
如何才能讓“一把手”出庭?
在參加全市“兩會”期間,楊家學曾經接連提交議案,希望出臺約束“一把手”出庭應訴的制度。
在大足區,楊廷瑞也在努力。
2013年初,大足區“兩會”期間,楊廷瑞提交了《行政訴訟案“一把手”出庭應形成制度》的提案。
…………
在各級人大和政協助推下,《重慶市行政機關應訴辦法》醞釀出臺,對行政“一把手”出庭作出了明文規定。
隨即激起陣陣“漣漪”——大足、合川、榮昌……一大批區縣爭相出臺配套制度。
隨著這些制度陸續運轉,一個約束“一把手”出庭的體系開始生效。
出庭吧,“一把手”
巴南區跳石鎮永隆村村民李世榮,就是這個體系的受益者。
2014年8月20日上午,巴南區人民法院第20法庭,李世榮坐上原告席。
原來,在一塊林地權屬問題上,李世榮和本村另一位村民發生糾紛。2011年,李世榮發現區林業局在2007年就將《林權證》發給了那位村民,于是認為區林業局“亂作為”,隨即狀告區政府,要求注銷對方《林權證》。
這個本分的農民做夢也沒想到——庭審那天,自己竟會和“大干部”對簿公堂。
坐定后,李世榮向被告席掃了一眼。
被告席上,坐著一個中年漢子。
“好像在電視上看到過……”瞇眼瞄了一會,李世榮感覺那漢子頗眼熟。
突然,他想起來了,“那是區長陳剛!”
“吃了一驚”的李世榮,并沒有因此“手軟”。
庭審開始——在隨后舉證、質證、辯論各個環節,李世榮頻頻出擊。
陳剛也不示弱——以法律法規為依據,逐項論證區林業局行政行為“無違規”。
雙方你來我往,激烈交鋒。
平頭百姓和區縣行政首長對簿公堂——這樣的畫面,不僅僅出現在巴南區。
在城口縣,五兄妹聯合狀告縣政府,縣長出面參加庭審。
在南川區,區長親自上庭,應訴村民集體征地公告案。
…………
2014年11月,全國人大通過了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決定,對“一把手”出庭作出明文規定。
至此,一個覆蓋國家、省(區市)、區縣三級的階梯式制度體系,開始推動“一把手”直面來自百姓的訴訟。
法庭內,李世榮和陳剛的辯論進入尾聲,控辯雙方進入總結陳詞。
此時,出乎意料的事發生了。
陳剛在發言時,竟然向李世榮道謝:“感謝原告通過司法程序來解決問題,而不是通過其他渠道上訪纏訪,這是群眾民主法治意識增強的結果,也給政府公務人員敲響了依法行政的警鐘。”
李世榮心里百味交集。
庭審結束,他主動找到陳剛,伸出了手:“不好意思,把你告了。”
“依法解決糾紛——你的行為值得鼓勵!”陳剛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