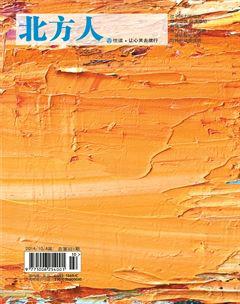誰是漢語的敵人
羽戈
四年前,有關部門曾對NBA、GDP、WTO等英語縮略詞痛下殺手,取而代之以“美國職業籃球聯賽”、“國內生產總值”、“世界貿易組織”等。打開電視,原本聽慣了于嘉、張衛平們一口一個NBA,忽然滿嘴“美職籃”,不免有些別扭;畫面之上,CCTV依然在,并未改做“中央電視臺”,則令人頓感滑稽。而且,電視臺改口“美職籃”,民間依舊NBA,一個中國,被此禁令橫斷為兩塊。
如今,“改口令”隱然有卷土重來之勢。昨天有媒體批判外來語濫用,如Wi-Fi、CEO、MBA、CBD、VIP、PM 2.5等,不經翻譯就見諸報端甚至學術期刊,使語境支離破碎,破壞了漢語的純潔性。例如:“……采用了基于O penEdX開源平臺,開發了HTML5視頻播放器,不再依賴國外課程播放首選的YouTube,解決了國內用戶無法訪問國外edX平臺問題。”話說這四個英文詞,我只識得中間兩個,不由汗顏無地。
假如順應此批判,不再使用Wi-Fi、iPhone式的外來語,該當如何?有人造句道:“記者能不能借我一個通用串行接口移動硬盤,我想拷貝一份全美職業籃球聯賽的運動圖像專家組數字音頻壓縮技術四代視頻到我的個人計算機上,以便傳輸到我的蘋果手機五代彩色版里。”這樣的表達,簡直令人發狂。
兩者相爭,何去何從?其實這兩個例句我都不太喜歡,倘譬之為飯,前者顯然夾雜了沙石,后者壓根沒有燒熟。
漢語與外語的戰爭已經上演了千載,近兩百年來,爭斗尤烈。這背后,則是政治與文化之戰。我們難以判定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卻可斷言,最終的勝者必將是一種開放的語言,以及一種開放的政治與文化心態。
以純潔性評判語言,實屬苛求。一個封閉的語言系統,大抵最為純潔,然而它可能已經喪失了活力。要有活力,必須海納百川,兼容并包,這正是漢語的特長。如我們現在使用的“胡同”,來自蒙古語,“菩薩”、“剎那”等,來自梵語。漢語江山,正因它們而增色。
批判Wi-Fi、CEO、MBA等外來語,可曾想到,平日常用的“政府”、“方針”、“政策”、“組織”、“紀律”,以及各種主義,都是從日本舶來?以語言的純潔而論,漢語的血統早已被敗壞。據說,今日之漢語,大約有1/4的外來語。
風物長宜放眼量。而今你覺得一些外來語面目猙獰,也許百年過后,只道是尋常。晚清時期,排斥外來語(新詞)者,不在少數。如張之洞,見幕僚所擬文中有“健康”一詞,便怒道:“‘健康乃日本名詞,用之殊覺可恨。”幕僚反駁:“‘名詞亦日本名詞,用之尤覺可恨。”當時,就連批判新詞,都得用新詞,可見新詞之兇猛。今天,“名詞”哪里還是什么新詞,誰還在乎它從哪里來呢。
當然,海納百川,不能泥沙俱下,漢語并非沒有敵人。想起一則故事。1988年,流沙河在北京晤蘇叔陽,共嘲當今文風之可笑,蘇叔陽朗誦論文長句:“審美主體對于作為審美客體的植物生殖器官的外緣進行觀感產生生理上并使之上升為精神上的愉悅感。”流沙河不懂,蘇解釋道,此言之意,用大白話說,即“聞花香很愉快”。這等裝腔作勢的表達,正是漢語的最大敵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