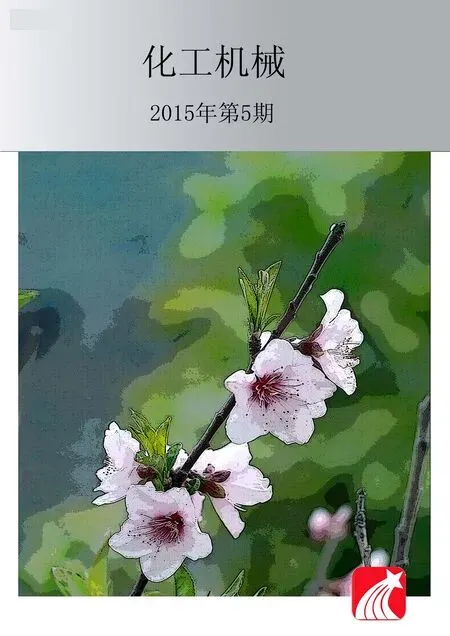矩形截面螺旋通道氣液兩相流可視化研究與壓降計算
周云龍 李佳研
(東北電力大學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
單螺桿膨脹機復雜三維矩形截面螺旋通道內多組分、多相流動結構是影響膨脹機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目前主要側重于膨脹機的加工和性能研究[1],缺乏對其內部多相流動結構和相分布規律的研究,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對于圓形截面螺旋通道內氣(汽)水兩相流動特性已有廣泛的研究[2~5],但對于其他截面形狀的螺旋通道,大部分還停留在數值研究階段[6],實驗研究較少。而僅有的對于矩形截面螺旋通道的實驗研究也多是針對單相流體所進行的流場結構和流動特性的研究,Bolinder C J和Sunden B對正方形截面螺旋通道內層流流場進行了測量[7]。張麗等對低雷諾數下高寬比為3.5的矩形螺旋通道流場進行了實驗測量,測量值與數值模擬值吻合較好[8]。馬源等利用二維粒子圖像測速儀(PIV)對矩形截面螺旋通道的5個橫截面流場進行了實驗測量,獲得了不同雷諾數下,不同橫截面的二次流瞬態流場和渦量場圖像[9]。但是,對矩形截面螺旋通道內氣液兩相流型和摩擦壓降的研究還未見報道。
鑒于此,筆者通過實驗的方法研究了單螺桿膨脹機內部矩形截面螺旋通道空氣-水兩相流的流型和摩擦壓降,探究了流型對摩擦壓降的影響規律,得出了適用于計算不同流型下摩擦壓降的經驗關系式。為尋求有效手段提高膨脹機效率,改善其性能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礎。
1 實驗系統與裝置
通道由一個外壁帶螺旋翅片的圓柱和一個外套管圍成,為了實現可視化研究,材料采用有機玻璃,螺旋翅片由車刀車出,與外套管的配合公差小于1mm。外套管內徑120mm、厚5mm,翅片高22mm,螺旋翅片厚度6mm,螺距110mm。所圍成的矩形截面的長、寬分別為24、22mm。通道當量直徑為23mm,曲率為0.47,撓率為0.36,Bolinder C J認為在2.5倍螺距處,流體流動已經充分發展[10]。因此為保證流動充分發展,本實驗中,取有效直管段的長度為550mm,即5倍螺距。
實驗裝置流程如圖1所示。水和空氣分別在離心式水泵和空氣壓縮機的動力推動下流經電磁流量計和熱式氣體質量流量計,經兩相混合器充分混合后流入實驗段,而后經旋風分離器分離,水流回水箱繼續循環使用,空氣排入大氣中。空氣壓縮機額定工作壓力為0.8MPa,實驗過程在常溫下進行,壓力參數范圍為0.1~0.3MPa;空氣的折算速度范圍為0.2~20.0m/s;水的折算速度范圍為0.04~2.70m/s。

圖1 實驗系統示意圖
實驗所使用的高速攝影儀鏡頭水平放置并與實驗段中軸線處于同一水平面上,拍攝實驗段前側的流動圖像,其最大分辨率為1536×1024,最大幀頻可達到10 000幀/s,可以十分清晰地拍攝到通道內的氣液兩相流型的變化。光源采用6 400K色溫的三基色照明,光亮穩定、均勻,無閃爍。使用差壓變送器采集機壓差信號通過數據采集器輸入計算機,實驗選擇相距2倍螺距的兩個取壓點采集壓差信號,兩點在同一水平線上,首個取壓點距離進口2.5倍螺距。實驗中采用的差壓變送器在實驗前使用電子手操器進行量程校準。
2 實驗結果與分析
2.1矩形截面螺旋通道兩相流流型
通過高速攝影儀觀察了矩形截面螺旋通道內的流型。對實驗拍得的圖片進行整理分析后,筆者將矩形截面螺旋通道氣、液兩相流流型區分為4種:柱塞狀流、彈狀流、環狀流和分散泡狀流,并繪制了流型圖。
當氣相與液相折算速度均較小時,觀察到了柱塞狀流,氣相以長氣泡狀分散在連續的液相中,如圖2a所示;隨著氣相折算速度的增高,觀察到了彈狀流的存在,如圖2b所示,大氣泡呈現氣彈狀,其間伴有小氣泡產生;隨著氣相折算速度的繼續增高,管道內逐漸形成了環狀流流型,氣相在管內中心流動,形成氣柱,液相趨于貼近壁面四周流動,如圖2c所示;當液相折算速度增高到一定程度時,觀察到了分散泡狀流流型,如圖2d,氣相變成細微小氣泡分散在連續的液相中。


圖2 典型流型
依據實驗數據并借助觀察所得將矩形截面螺旋通道試驗結果繪制成流型圖,如圖3所示。從流型圖可以看出:與經典圓形截面螺旋管的流型圖[11]相比,各流型轉換的過渡區域的邊界形狀基本一致,只是轉換邊界過渡區的位置有一定差異,不同之處是本次實驗未發現在圓形截面螺旋管一定區域內會出現的波狀分層流型,原因有待繼續研究;柱塞狀流向彈狀流轉換和彈狀流向環狀流轉換的過渡邊界為一近似垂直的帶狀區域,過渡區流型如圖4a、b所示,過渡區氣相折算速度分別為JG=0.81~1.12m/s、JG=16.8~20.1m/s。如果把柱塞狀流和彈狀流看作統一的間歇流,那么間歇流與分散泡狀流轉換的過渡邊界類似一傾斜上升的帶狀區域,過渡區流型如圖4c所示,過渡區液相折算速度約為JL=0.73~1.19m/s。

圖3 流型

圖4 過渡區流型
氣液兩相流各種流型的出現及其轉換是由作用在氣液兩相上的各種力的相互作用及平衡引起的[12,13]。水平管中,兩相流主要受液相紊流應力和氣相慣性力的作用,而在矩形截面螺旋通道中還要受到液相離心力的影響。間歇流向環狀流的轉換主要是由于氣相流速的增加使氣相慣性力增大,氣相能夠克服液相重力的作用并形成氣柱,表面張力亦起到一定的作用;間歇流向分散泡狀流的轉換是由于當液相的流速比較高時,矩形截面螺旋通道內產生比較強烈的二次流,促使氣液兩相混合,當混合的趨勢足以克服由液相離心力帶來的兩相分離趨勢時,間歇流就會向分散泡狀流轉換。
2.2矩形截面螺旋通道摩擦壓降
壓差傳感器測得的壓降值為摩擦壓降,即流動加速引起的壓降與重力勢差引起的壓降之和,因此摩擦壓降需要通過計算獲得。 流動總壓降的表達式為:
Δptotal=Δpstatic+Δpmom+Δpfrict
(1)
其中,Δptotal為管內流動總壓降,Δpstatic為重力勢差引起的壓降(本實驗中兩取壓點水平高度相同,Δpstatic=0),Δpmom為管內流體加速引起的壓降,Δpfrict為流體的摩擦壓降,本次實驗加速壓降產生的影響較小,可以近似忽略,因此本實驗系統的摩擦壓降Δpfrict可以近似的等同于總壓降Δptotal,進而通過實驗測得。
2.2.1計算方法
筆者采用Lockhart- Martinelli分相模型處理實驗數據,并使用Chisholm的B系數法擬合經驗關系式,Lockhart- Martinelli分相模型是最早提出并被廣泛應用至今的摩擦壓降計算方法。具體計算式如下:
(2)

(3)
(4)

Chisholm在L- M實驗曲線擬合式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數據范圍,得到了經驗式為:
(5)

式中B——與工質物性及質量流速有關的參數;
n——雷諾數的指數值。
2.2.2計算結果與實驗結果的比較
運用上述計算方法計算矩形截面螺旋通道的摩擦壓降。通過與實驗數據比較發現處理結果不夠理想,與實驗值有一定的偏差。從圖5中可以看出:3種流型液相摩擦因子的分布并不一致,變化規律也不相同,這說明流型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兩相摩擦阻力。因此,為了提高摩擦壓降計算模型預測的準確性,筆者采用了分流型計算矩形截面螺旋通道摩擦壓降的方法。通過對摩擦壓降的測量結果進行數學回歸與處理,建立了適用于矩形截面螺旋通道不同流型下的摩擦壓降計算經驗關系式:

(6)

(7)

(8)

圖5 3種流型的實驗結果
圖6為各流型下液相摩擦因子預測值與實驗值的對比。3種流型(間歇流、環狀流、分散泡狀流)計算值與實驗值的平均偏差分別為17.27%、13.73%、45.81%。間歇流與環狀流的預測結果與實驗值的平均偏差在30%以內,由文獻[18,19]可知,計算結果與實驗結果符合較好,而分散泡狀流預測值與實驗值的平均偏差為45.81%,總體上偏差較大。結果表明:Chisholm模型更適用于間歇流和環狀流狀態下的壓降預測,而對于液相流速相對較高的分散泡狀流區間的預測存在較大誤差。
3 結束語

圖6 液相摩擦因子預測值與實驗值的對比
實驗觀察到了矩形截面螺旋通道氣、液兩相流有柱塞狀流、彈狀流、分散泡狀流、環狀流幾種典型的流型,與經典圓形截面螺旋管的流型圖相比,各流型轉換的過渡區域的邊界形狀基本一致,只是轉換邊界過渡區的位置有一定差異,實驗中未發現在圓形截面螺旋管一定區域內出現的波狀分層流型。流型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矩形截面螺旋通道內兩相摩擦阻力,采用分流型計算矩形截面螺旋通道摩擦壓降的方法可以有效提高預測精度。Chisholm模型適用于間歇流和環狀流狀態下的壓降預測,分散泡狀流狀態下的壓降預測有待進一步研究。
[1] 何為,吳玉庭,馬重芳.兩級單螺桿膨脹機空氣動力系統性能研究[J].機械工程學報,2010,46(10):139~145.
[2] Biswas A B,Das S K.Frictional Pressure Drop of Air Non- newtonian Liquid Flow Through[J].The Canadian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2007,85(2):129~136.
[3] Biswas A B,Das S K.Two- phase Frictional Pressure Drop of Gasnon- Newtonian Liquid Flow Through Helical Coils in Vertical Orientation[J].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Processing:Process Intensification,2008,47(5):816~826.
[4] Santini L,Cioncolini A,Lombardi C,et al. Two- phase Pressure Drops in a Helically Coiled Steam Generato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2008,51(19/20):4926~4939.
[5] Murai Y,Yoshikawa S,Toda S,et al. Structure of Air- Water Two- phase Flow in Helically Coiled Tubes[J].Nuclear Engineering and Design,2006,236(1):94~106.
[6] Xia G D,Liu X F,Zhai Y L,et al.Single- phase and Two- phase Flows Through Helical Rectangular Channels in Single Screw Expander Prototype[J].Journal of Hydrodynamics,2014,26(1):114~121.
[7] Bolinder C J,Sunden B.Numerical Prediction of Laminar Flow and Forced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in a Helical Square Duct with a Finite Pit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Mass Transfer,1996,39(15):3101~3115.
[8] 張麗,邢彥偉,吳劍華.矩形截面螺旋通道內流體的流動特性[J].化工學報,2010,61(5):1089~1096.
[9] 馬源,曹文瑾,林梅.矩形截面螺旋通道內的二次流流場特性[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14,48(8):122~127.
[10] Bolinder C J.Flow Visualization and LDV Measurements of Laminar Flow in a Helical Square Ducts with Finite Pitch[J].Experimental Thermal and Fluid Science,1995,11(4):348~363.
[11] 張鳴遠,陳學俊.螺旋管內氣-水兩相流流型轉換的研究[J].核科學與工程,1983,3(4):298~304.
[12] Yih- yun Hsu,Graham R W.Transport Processes in Boiling and Two- phase Systems[M].Washington D C:Hemisphere Publishing Company,1986.
[13] 赤川浩爾.氣液兩相流動[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76.
[14] Tribbe C,Muller- Steinhagen.Structure of Two- phase Flow in Coiled Tubes[J].Multiphase Flow,2007,(26):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