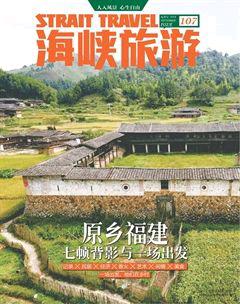一百年后,我們會成為湯姆遜嗎?
周湘瑜



一百多年前,有一位名叫湯姆遜的蘇格蘭人,從廣東、臺灣來到福建,當他從閩江口坐船向福州進發的時候,被閩江沿岸的風光折服,并且用影像留下了珍貴的記錄,他甚至認為閩江可以與歐洲幾條著名的河流所媲美。作為世界紀實攝影的先驅者之一,湯姆遜還出版了《福州與閩江》、《中國和中國人影像》等在西方十分著名的出版物。
2014年,《福建畫報》啟動了一個名為《閩江》的大型影像文化創作工程,召集了國內外十幾位攝影師,計劃用一年時間,從閩江正源、中源等源頭出發,走遍閩江所有支流和主干,用影像記錄今天的閩江。
《閩江》是一個以紀實為創作風格,以社會學的田野記錄為手法的人文影像項目。參與的攝影師包括曾璜、Frank Folwell(美國)、那興海、崔建楠、李世雄、曲利明、陳勇鵬、周躍東、王鷺佳、賴小兵、陳偉凱等國內外知名攝影師。每個人均依主題拍攝,包括閩江沿岸的日常生活、閩江風光、人、宗教與宗族、書寫閩江、即將消失的船家、戲曲、民俗等等。
《閩江》的拍攝方法為“集體行走,個人創作”。一共安排四次“集體行走”,第一次在2014年5月,行走富屯溪。行走北溪和西溪兩條支流,走到每一個支流的最遠的村莊和鄉鎮。然后再行走光澤至順昌、邵武的富屯溪主流。第二次行走在2014年7月,行走崇陽溪、南浦溪、建溪部分。第三次行走計劃安排在2014年9月,行走閩江正源(沙溪)建寧至南平部分。年底11月計劃第四次行走,線路為南平至福州的閩江主流以及這個河段上重要的支流,比如古田溪、尤溪、大樟溪等。
因為強調紀實的影像創作風格和社會學的田野記錄,在這個工程中,采訪和拍攝同樣重要。所以,每一位攝影師都需要文圖雙重記錄,在已經完成的兩次行走拍攝中,他們已經通過微信推送了許多飽含行走情感的文字和圖片,那些珍貴的影像比普通的攝影展示更具直達人心的力量。
我們采訪了《閩江》工程的策劃人和組織者,《福建畫報》社社長、總編輯崔建楠先生,他說,《閩江》是一次向湯姆遜的致敬!所有的歷史都需要用影像將變化和進步保留,“我們一直在用穿越的眼光去審視自己在閩江的行走和記錄,一百年之后,我們會不會也是湯姆遜了呢?”
海峽旅游×崔建楠
這次閩江拍攝,您選了“人”的拍攝主題,為什么?
我一貫拍攝的方向就是人物。我覺得,人是一個句號,其他的都是逗號。人們最關心、最喜歡觀看的,是人自己。對紀實影像來說,風光、建筑、民俗,沒有人,總是有所缺失。
其次,《閩江》的前因是因為湯姆遜的那些一百年前閩江的片子,在他的影像中,有閩江沿岸各種各樣的人物。一百多年來,也有不少外國攝影師拍過中國人。但是,無一例外的,他們拍攝的中國人的表情都很木訥。可能中國人那時候的表情就是那樣?或者面對外國人的鏡頭太緊張?還是因為當時感光材料的原因,曝光時間太長而“略過了”更豐富的表情?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覺得,中國人也有喜怒哀樂,湯姆遜之后,我想記錄更為“生活”、有更多表情的中國人。事實上,我在拍攝時發現,現在閩江沿岸的人與湯姆遜拍攝的人已經大不一樣,現在的中國人面對鏡頭的時候都很開放、開朗,都很陽光。我想這應該是一種進步。有機會的話,也希望讓外國人看一看。未來要是時機成熟,我覺得甚至可以通過影展的方式,將我們拍攝的人物與湯姆遜的做個對比。
《閩江》拍攝強調紀實,現代藝術家陳勇鵬在閩江沿線書寫心經的行為藝術的加入,是刻意設置的嗎?有沒有爭議?
四年前《跨越三個世紀的影像——湯姆遜的福州和閩江》攝影展時,我們就有了拍攝閩江的想法,這幾年一直在調整思路,但紀實風格是肯定的。把陳勇鵬的創作納入《閩江》,有爭論,有人認為行為藝術不適合在紀實類的紀錄之中。但曾璜(著名攝影理論評論家,影像收藏學者)老師認為,《閩江》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平臺,作業形態應該更豐富。將“心經書寫”的行為放進來,有一定的表現力和豐富性。包括之后我們還吸收了攝影師郭曉丹的針孔攝影。針孔攝影其實也是非紀實影像,更多是觀念上的一種呈現。
目前《閩江》已經完成了兩次行走拍攝,我們發現,事實上這兩位非紀實的作品更突出,更能吸引眼球。這對于活動的推廣、加強影響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當然最重要的是,只要它的紀錄有作用,能讓紀錄更扎實更全面,就沒有問題。
接下來在拍攝方法上還會有拓展和變化嗎?
我們的拍攝方法一直在拓展。
第一次行走時,我們是規定主題。所有攝影師都按照規定的主題拍攝,結果發現會漏掉很多內容。第二次我們就調整為拍攝內容的“規定動作+自選動作”。規定動作一定要完成,自選動作由攝影師自己決定。
第二次行走之后,我們又嘗試了一個閩江漂流項目,幾位年輕攝影師劃艇拍攝,從建寧的源頭一路漂到三明。幾天的漂流拍攝,給《閩江》這個大作業帶來了非常難得的寶貴與真實的一面。因為前面我們都是走“陸路”,常常是要離開溪水江水。漂流在水面上,會看到許多我們未曾發現的東西,有山水生態很美的河段,也有一些“負面”的發現。比如,在建寧閩江源頭的村落,發現了很嚴重的污染;在安沙水庫,發現了公路建設砂石亂傾倒;還有永安小煤礦隨意傾倒礦渣,水面上經常可以碰到電魚的人……
我們前兩次紀錄都是比較正面的,不論拍攝的是民俗、民居還是其他,這并非刻意為之,可能因為前兩次走到的地方確實生態保護比較好,也可能是因為陸路水路的差別。第三次大規模行走時,我們會從陸路再走一回閩江正源,給這條已經漂流過的線路,再做一次驗證。
有沒有考慮新攝影師的加入?
《閩江》活動開始以后,有很多攝影師想要參加進來,因為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劃時代的項目。從湯姆遜之后,沒有過這樣整整耗時一年的四次行走,即使是湯姆遜也沒有把閩江的主干、支流都走遍,這個“走”本身就可能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但是,我們增加人會非常慎重,因為隊伍越龐大,操作難度就會越大。
閩江一線的鄉村是什么樣的狀態?
城鎮化給鄉村帶來的空村化很嚴重。媒體講空村化,多半是持批評態度。我們在實地看過后,感覺城鎮化的進程,傷害的是城市,而不是農村。我在源頭看到的鄉村,植被很好,草木茂盛,滿眼都是綠色。村里連獵人都沒有了,鳥獸也變得很多。空村化竟然讓鄉村的自然生態得到了休養生息的機會,我認為這是一種好處。
當然,空村化的鄉村真的很破敗落后,基本沒有建設,很多老房子塌掉了,人的生活痕跡也沒有了,很可惜。
可現在不是正有返鄉潮流?
只有藝術返村的潮流形不成大趨勢。村干部的家都在縣城,他們開著車到村里來“上班”。進城的青年人要從城市再回到農村?我覺得也許要一百年后,至少要再經過三四代人的輪回吧。
這個問題其實關乎到鄉愁。良好的生活環境,有魅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我喝你的杯中酒,你吃我的碗中菜,這是我們的鄉愁。可問題是,鄉愁的主體不是城里人,而是農村里生活的人,但他們正在迫不及待地拋棄這些我們覺得丟了可惜的傳統和生活方式去城里。鄉愁已經支離破碎,還是留在心里好了。
在鄉村與我們漸行漸遠的當下,記錄很重要,許多傳統不記錄可能就沒了。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攝影師、導演,到鄉村田野中去。您對他們有什么建議?怎么真正有價值地去記錄,而不只是一味說“鄉愁”?
就好比你把腳踏進一條河,不要太囂張,不要奔跑,不要把水濺出來。去體驗,不要用自己很主觀或藝術的行為方式去看鄉村、表現鄉村。先體會鄉村,再去審視自己的方式是否合適。很多攝影師都是撲通一聲撲進人家生活當中去,攪得一團糟后,抽身就離開了。
鄉村對您而言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安靜和寧靜。時髦的說法是,可以安放一下靈魂。在源頭的村子時,我就想,如果我在這里生活一段,那種簡單生活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來的啊,來往的人應該也就那么幾個,生活上干凈,空氣清新,聽覺安靜。回來后,心靈上都很躁動。這次拍攝是大部隊行動,沒能更好體驗,我是留有遺憾的,以后一旦有機會,應該會邀上一兩個朋友,背起行囊就出發。
福建鄉村與別的地方相比有什么不同?
一是山清水秀,尤其是在諸多的閩江源頭地區。福建的丘陵地貌和暖濕氣流覆蓋,植被良好,生態也好。近年的城鎮化,鄉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形成的“空村化”也一定程度上利于鄉村生態保護。二是文化多元。福建文化基本是歷朝歷代中原文化南遷與本土文化(古越文化)融合的結果,又因為自然地形的原因,文化南遷落地后基本不與周邊交流,就形成了文化的小氣候,獨立、獨特、多元、多彩。所以只要去的節點對頭,就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民俗文化現象,這些保留了中原文化基因的民俗活動,遍及生產、宗教、節慶、日常生活之中。
推薦幾個閩江沿線最值得去的鄉村?
目前我們只走了富屯溪和建溪。富屯溪的光澤縣崇仁鄉的油溪村很值得去,那里有閩北廊橋承安橋。承安橋每年農歷7月都要舉行民俗活動“走橋”。那一帶的農民在這個季節要走過三座橋,夫妻橋、子孫橋和父母橋,走過了,夫妻子孫父母今年就平安了。承安橋是“夫妻橋”。油溪村還有“茶燈戲”,是非遺項目,《閩江》的攝影家都拍了在橋上的演出。附近有個村子叫饒坪,有“大圣廟”(孫悟空崇拜)。
第二個推薦村莊是邵武桂嶺鄉的橫坑村,這個村子是閩江中源富屯溪源頭之西溪的源頭,生態以及傳統民居保護較好,是桂林鄉設計的大學美術專業學生的寫生基地。
還推薦建溪上游九曲溪的源頭村子桐木村,那里是武夷山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地帶,但是進去需要特別申請報備。還可由桐木村去往華東第一高峰黃崗山,也要申請。桐木村是紅茶正山小種的原產地,春季制茶季節可以看到家家戶戶做茶的景象,也有豐富的紅茶歷史、紅茶制作技藝可以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