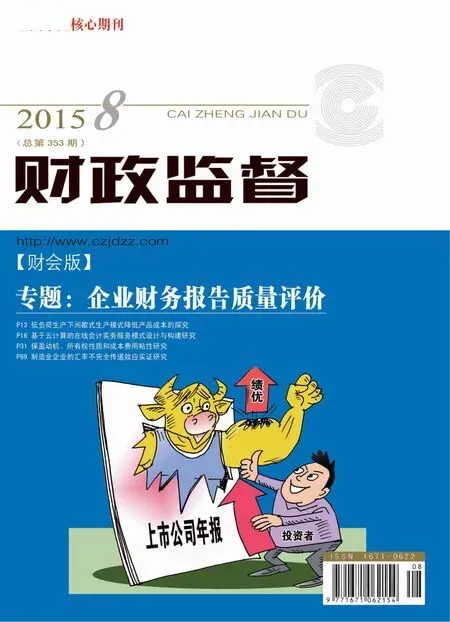保盈動機、所有權性質和成本費用粘性研究
●新疆財經大學 華雯雯 耿玉環 張婧超
保盈動機、所有權性質和成本費用粘性研究
●新疆財經大學 華雯雯 耿玉環 張婧超
成本費用粘性是最近比較受關注的熱點問題,目前我國企業成本費用粘性的研究基本上使用公開數據(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此類數據的使用,在反映成本變動下的真實成本性態的情況時,并未考慮管理層盈余操縱行為對成本費用粘性的影響,而忽略了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會使成本費用粘性的估計出現偏差。本文考慮相關管理人員資源調整時存在的潛在動機,特別是在為達到盈余目標這個動機(保盈動機)的驅動下進行的資源調整,在業務量下降的情況下他們會加快減少松弛資源(指超過維持其短期正常運作所必需的組織資源水平,包括冗余員工、閑置的財物資源和未使用的能力以及未被開發利用的機會等),進而會影響成本費用的結構。在忽略了保盈動機的情況下,成本費用粘性在以前的研究中很可能被高估了,這種動機其實會降低企業的成本費用粘性,而不是增加成本費用粘性。本文分別使用基本的和改進了的成本費用粘性經驗模型,選取2007-2012年所有非金融類行業非ST的A股上市公司,對上述假設進行了驗證。
成本費用粘性 保盈動機 產權性質
本文的研究是新近出現的研究內容的一部分,此類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擴展對進行資源調整的管理決策是如何影響公司的成本結構的理解(Kallapur和Eldenburg,2005;Banker等, 2011;Chen等,2012)。Anderson,Banker和Janakjraman(2003),以下簡稱ABJ,他們定義成本的粘性表現為在同等幅度的業務量變化條件下,由業務量下降所引起的成本下降幅度小于由業務量上升所引起的上升幅度,認為產生粘性成本的原因是管理層基于目標進行的深思熟慮的資源調整。陳磊等(2012)認為管理層在企業面臨虧損時經常采用的“洗大澡”式的盈余管理,降低了成本粘性的水平,“管理費用”的粘性水平降為原來的三分之一,“銷售費用”幾乎不具有粘性了。本文更關注自利的管理者作出的決定,研究管理者具有保盈動機時進行的資源調整,是怎樣影響成本費用粘性的程度的,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成本費用粘性。而國有上市企業存在更嚴重的委托代理問題,本文將進一步探究保盈動機對國有上市企業和非國有上市企業的作用是否有區別,是否對國有企業的作用更顯著,是否能對企業的成本決策和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改革提供一些幫助。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現狀。Banker等( 2010)對成本費用粘性的相關實證研究做了一個總結,將公司的成本粘性主要成因歸結為三個方面,分別為調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管理者樂觀預期 (Optimism)和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s)。將調整成本作為成本粘性成因的觀點認為,企業成本的產生是管理層對投入各種資源承諾的結果,管理層作這些決策時會深思熟慮,因為管理層在決定需要增加或者減少這些已經承諾的資源時,公司會產生調整成本。ABJ(2003)、Banker和 Chen (2006)以及 Kama和Weiss(2010)等學者的研究結果都支持了管理者樂觀預期的觀點。將代理問題作為成本粘性成因的觀點認為,管理者與所有者之間存在代理問題,管理者對各種承諾資源進行調整決策時會存在自利行為,他們的自利行為使得成本習性與公司的最優資源配置出現不一致,就會導致成本粘性問題,但是代理問題既可能增加也可能減少公司的成本粘性,取決于具體的情形(Kama和Weiss,2010)。Banker等(1993)最早發現費用的增減與業務量變動之間有非對稱關系,他們在對美國航空業的一次研究中發現其費用上升和下降的幅度與業務量變動的方向相關,還預告了企業存在費用粘性的可能性。ABJ(2003)進一步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企業銷售和管理費用的變化確實存在不對稱性,并借用經濟學中價格粘性的概念,將這一現象稱為成本粘性,明確了成本粘性的定義。
(二)國內研究現狀。李糧和趙息(2013)以2007-2010四年的深滬兩市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高管不同預期對費用粘性的作用,研究結果發現當上市公司管理者對未來的銷售額持樂觀預期時費用具有粘性,且費用粘性水平隨著樂觀預期程度的增加也不斷增加,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對未來業務量持悲觀預期時費用粘性的表現并不明顯。他們的結果也驗證了管理者的樂觀預期是成本費用粘性成因的觀點。萬壽義和徐圣男(2012)將我國滬深兩市上市公司按照實質控制人性質的不同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采用2004-2010年的公開數據,得出我國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銷管費用均存在費用粘性行為,且國有企業的費用粘性程度要高于非國有企業,金融危機后我國上市企業的費用粘性程度都有所提高,特別是非國有企業提高的幅度比較大,資本密集度對于我國上市企業費用粘性的增強起到一定作用,相比較而言,國有企業受其影響較強烈。王東清和王煜姣(2013)以2003-2011年我國深滬兩市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Dan Weiss的成本粘性直接測度模型(直接從公司角度出發,計算出樣本個體的費用粘性和費用反粘性的存在與否及其粘性水平大小)對我國上市公司成本習性現狀進行了統計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成本粘性和成本反粘性在我國上市公司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伴隨著時間的不斷增加,粘性水平會越來越不明顯。
二、研究假設及研究模型
(一)研究假設的推演。Banker等(2011)發現當投入資源的支出創造出未來的高價值時,給予管理層的股權激勵與投入資源消費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他們的研究結果還表明,股權激勵影響管理者調整資源的決策,但他們沒有進一步探索股權激勵對成本的不對稱程度的潛在影響。代理方面,Chen等(2012)證明了擴張激勵會影響管理層成本決策,特別是需要應對外生的需求沖擊的情況下。他們表明,有擴張激勵的經理層當業務量增加時增加的“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SG&A)成本幅度比業務量減少時SG&A成本減少的幅度要大得多。也就是說,擴張激勵產生了成本不對稱,這意味著代理問題和SG&A成本不對稱程度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
大量的證據表明,代理問題導致管理者降低成本,以滿足各種基準 (Dechow和Sloan,1991;Baber等,1991;Bushee,1998)。特別是Graham等(2005)、Roychowdhury(2006)、張俊瑞等(2008)、顧鳴潤等(2012)都指出管理者會降低成本,以避免虧損和盈利下降,或符合分析師的預測。然而,以滿足保盈目標的成本降低對成本不對稱程度的影響尚未被研究。
當業務量下降時,閑散的資源不能都被消除,除非經理層作了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將其消除。由于未來的需求是隨機的,管理人員首先評估業務量下降是暫時性的還是非暫時性的,然后決定是否削減資源。削減松弛資源在銷售額下降的情況下,向下調整資源(減少資源)可能會導致額外的成本產生(例如,解雇員工的成本),以及如果銷售額在未來恢復重新更換那些資源(例如,重新雇用新員工)的成本。因此,基于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考慮,當管理者預期目前的銷售額下降只是暫時性的,他們就會保留這些閑散的資源。在業務量下降時保留閑散的資源這一現象導致業務量降低時成本減少的幅度比業務量上升(與降低同等數額)時成本增加的幅度小很多,這就產生了成本粘性(ABJ,2003)。
在本文中,我們探討以滿足保盈目標的資源調整和成本費用粘性程度之間的關系。ABJ認為,除了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考慮,經理人選擇保留閑散資源的原因也可能是基于個人利益的考慮。這些選擇導致了代理成本的形成,因此,又進一步產生了成本費用粘性。對于資源的調整,我們推斷,以滿足保盈目標的激勵機制會使管理層加速削減資源,以期實現節約成本費用的目的。在業務量下降的情況下這樣加速削減閑散的資源,會導致更大的成本降低,相比于沒有滿足保盈目標的激勵措施。因而推測,為滿足當前的保盈目標的動機會減輕成本費用的粘性程度,而不是增加了成本費用的粘性程度。
面對保盈目標,在業務量下降的情況下成本費用粘性程度的減少是因為經理層會加快削減成本。這種管理者行為是代理成本的一種表現形式,是自利的經理層為滿足保盈目標的動機作出的決定,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個人的效用,而不是公司的價值。經理層面臨滿足盈余目標的激勵機制,在業務量下降時很可能削減松弛資源即使他們預期業務量下降只是暫時性的。削減松弛資源會直接導致成本節約的結果,為了滿足保盈目標這也是必要的。換句話說,為滿足保盈目標,自利的管理者在業務量下降時會大量削減資源。
萬壽義和徐圣男(2012)的研究證明因為國有企業特有的性質,我國國有上市企業的費用粘性程度大于非國有上市企業。國有企業的主要管理者多為政府委派,經營目標具有多重性,并且他們的報酬與升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治、社會和業績等因素,相對非國有企業更容易進行真實盈余活動操縱(顧鳴潤等,2012)。本文首先依據產權性質,分別討論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保盈動機對成本費用粘性程度的影響,特別是在業務量下降時保盈動機對國有企業的成本費用粘性程度的影響應該要高于非國有企業。
(二)研究假設的提出。當業務量增長時,滿足保盈目標的動機很可能鼓勵管理者減少增加新的資源,進而使成本的增長速度放緩。但是,我們注意到相比業務量下降,在業務量上升時有兩個原因削弱了這個動機的影響。
第一個原因,在業務量下降時未達到保盈目標的壞消息比其他的壞消息存在更嚴重的影響 (Rees和Sivaramakrishnan,2007)。管理層很可能要承受非常大的壓力去避免出現財務報告未達到保盈目標這樣的壞消息,特別是它還伴隨著業務量下降的壞消息(Graham等,2005)。因此,對于經理層滿足保盈目標的激勵機制創造的更多的壓力,在業務量下降而不是業務量上升的情況下起到了更多的作用。
第二個原因,假設一個管理者有避免損失的保盈動機(Burgstahler Dichev,1997;吳聯生等,2007),當他所在的企業在本年度中有微小的收益和較少的業務量增長時,它很可能經歷了去年的損失,因為業務量在去年較低。因此,管理者有可能已經在去年就削減了松弛的資源,以減少虧損。在這種情況下,只剩下較少的松弛資源供本年度削減。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公司有微小的收益,而本年度的業務量卻下降了,它也有可能在去年經歷了較大的收益,其業務量高于往年。在這種情況下,管理者在去年就會面臨較小的壓力,不會去大量削減松弛資源。進而,有更多的松弛資源被留在本年度,與業務量增加相比,業務量減少時更可能削減松弛資源。總體而言,與業務量上升相比,業務量下降時為滿足保盈目標的激勵機制在資源調整特別是削減松弛資源方面會起到更大的作用。
產權性質的差異是我國企業所特有的,而且我國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國有控股企業改制而成。龔啟輝等(2010)發現由于國有企業具有更為嚴重的代理問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對成本費用的粘性影響更加明顯。萬壽義等(2012)發現國有企業的費用粘性程度高于非國有企業的費用粘性程度,資本密集度對費用粘性有負的影響,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受其影響更明顯。顧鳴潤等(2012)認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相比,更有動機為了避免虧損、盈利下降,或滿足分析師的盈利預測進行真實盈余管理。本文認為相對非國有上市企業,國有上市企業的成本費用粘性程度受保盈動機作出資源調整的影響會更大,特別是在業務量下降的情況下。
本文進行以下假設總結上述觀點:
H1(a):為滿足保盈目標作出的資源調整會減少成本費用粘性的程度,即有保盈動機的上市企業成本費用粘性較弱。
H1(b):與非國有上市企業相比,國有控股上市企業為滿足保盈目標作出的資源調整,使成本費用粘性減少的程度更大。
H2(a):給定的業務量下降時,有保盈動機比沒有此動機的管理人員會更積極地削減成本,成本費用粘性減少的程度更大。
H2(b):與非國有上市企業相比,在給定的業務量下降時,國有控股上市企業有保盈動機的管理人員會更積極地削減成本,成本費用粘性減少的程度更大。
(三)研究模型
1.成本費用粘性存在性的基本檢驗模型。本文根據ABJ (2003)、孫錚和劉浩(2004)、孔玉生等(2007)用于檢驗成本費用粘性存在性的基本模型如下:

模型1中的因變量△lnOC用來度量成本粘性水平,模型2中的因變量△lnEXPENSE用來衡量費用粘性水平,模型1中的β1是指業務量每增加1%時,成本增加的幅度,β1+β2表示業務量每下降1%時,成本減少的幅度。模型2中的β1是指業務量每增加1%時,費用增加的幅度,β1+β2表示業務量每下降1%時,費用減少的幅度。成本費用粘性的研究文獻表明,當β1顯著大于0且β2顯著小于0時,證明成本費用粘性是存在的。β1+β2的大小則顯示了成本費用的粘性程度。
2.成本費用粘性的全面檢驗回歸模型。模型1和模型2強調的是業務量下降和業務量上升時成本費用的變動幅度,我們擴展了模型1和模型2,形成模型3和模型4,突出在業務量下降或上升時,為實現保盈目標進行的資源調整,討論為實現保盈目標進行的資源調整與成本費用的變動幅度之間的關系。

本文根據張俊瑞等(2009)、顧鳴潤等(2012)將TARGET這個變量作為衡量企業是否具有保盈動機 (避免報告虧損的動機、避免盈余下降的動機和達到分析師預測水平動機)的指標。當LOSSit或EDECit取1時,虛擬變量TARGETit=1,說明企業具有保盈動機,而LOSSit和EDECit都取0時,TARGETit=0,表明企業沒有保盈動機。
模型3中的因變量△lnOC用來衡量成本粘性水平,模型4中的因變量△lnEXPENSE用來衡量費用粘性水平。在模型3與模型4中根據現有的研究文獻,我們選取了三個控制變量,ABJ認為前期的收益是減少的時候,成本費用的粘性程度會比較低,原因是當第一次出現收益下降時,管理者可能不會立刻減少松弛資源,但當收益持續下降時,管理者預期收益減少具有持續性,就會有動機去削減松弛資源,我們用變量SUC_DEC控制連續的收益下降,并預計對成本費用的粘性是負的作用。Callejia等(2006)、龔啟輝等(2010)的研究結果認為財務杠桿和資本密集度會影響成本費用粘性并且也都是負的作用,因此我們又分別控制了LEV和CAPRATION這兩個變量。
本文用擴展后的模型來檢驗保盈動機是否會減輕成本費用粘性的幅度,在模型3和模型4中,β1+γ1表示存在保盈動機的情況下,業務量增加1%時成本或費用增加的幅度,存在保盈動機時,業務量下降1%時成本或費用減少的幅度為β1+γ1+β2+γ2+δ1+δ2+δ3,因為β1+γ1在業務量下降和業務量上升時都存在,因此當存在保盈動機時,是否存在成本費用粘性取決于系數β2+γ2+δ1+δ2+δ3,沒有保盈動機時,成本費用粘性是否存在,看系數β2+δ1+δ2+δ3。因此如果γ2>0,則驗證了假設1,即為滿足保盈目標作出的資源調整會減少成本費用粘性的程度。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差別我們參照Chen等(2010)的Z值計算做法,Z值等于兩個回歸模型中變量的回歸系數之差除以回歸變量方差之和的平方根。
模型3和模型4同樣可以驗證假設2,當業務量下降時,沒有保盈動機時成本費用粘性的存在用系數β1+β2+δ1+δ2+δ3來衡量,存在保盈動機時成本費用粘性用系數β1+γ1+β2+γ2+ δ1+δ2+δ3來衡量,因此當γ1+γ2>0時,假設2給定的業務量下降,有保盈動機比沒有此動機的管理人員會更積極地削減成本,成本粘性減少的程度更大成立。
創新類課程[3]為完全學分制下的一種特色選修課,存在一個教學班級的學生年級、專業背景不同的情況,不能和常規基礎課班級采用相同教學方法。本文在完全學分制環境下,采用多模式教學方法,對如何提高“創新類”課程的教學效果進行探討。
(三)子樣本的選取。Graham等(2005)認為由于外部市場壓力的存在,真實盈余管理的最主要動機有三個:達到上一年的盈利目標、滿足分析師的預測和避免財務報告損失。本文定義如果企業年末凈利潤除以年初總資產在[0,0.005]區間的是有動機避免報告虧損的,即ROA=[0,0.005],和(年末凈利潤減去上年凈利潤)/年初總資產在[0,0.005]區間的樣本公司是具有為了達到上年報告盈余(避免盈余下降)或達到分析師預測水平動機的,我們將存在這三個動機之一的樣本定義為有保盈動機的樣本,就是我們的子樣本,與沒有保盈動機的樣本進行比較分析。
三、樣本選取及實證檢驗
(一)樣本選取及其描述性統計。本文涉及的所有變量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樣本選取為2007-2012年所有非金融類行業非ST的A股上市企業。因為2007年1月1日開始實施新的會計準則,為了保持所選數據具有可比性,故本文未選擇2007年以前的數據。我們取得的數據是2007-2012年剔除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管理費用、銷售費用為負數、缺失或前一年數據缺失、為負數的和控制變量缺失或為負數的數據,得到的最終樣本數據為7871個,其中所有權性質為國有企業的樣本數據有4655個、非國有企業樣本數據為3216個,有保盈動機的樣本有1283個,其中國有企業中有840個,非國有企業中有 443個。本文使用Excel和Stata12.0軟件,對數據進行了處理。

表1 樣本的分布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3 總樣本各變量的Pearson相關性

表4 保盈動機對成本粘性影響的基本模型回歸結果
從表4總樣本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可以看出營業收入增長率(lnREV)與成本增長率(lnOC)、費用增長率(lnEXPENSE)成正相關的關系,營業收入變化量(REVDEC)與成本、費用增長率成正相關的關系,保盈動機(TARGET)與費用增長率在10%的水平上負相關,財務杠桿(LEV)與成本增長率負相關,與費用增長率正相關,資本密集度(CAPRATION)與成本增長率正相關,與費用增長率負相關,以前年度營業收入變化量(SUC_DEC)與成本增長率正相關,與費用增長率負相關。同樣做了Spearman檢驗,結果與Pearson檢驗基本一致。分別做了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樣本各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只有變量保盈動機對非國有樣本沒有顯著的關系,其他變量的相關性與總樣本并沒有差別。我們預計保盈動機對非國有企業的成本費用粘性減少的作用不明顯。
(二)實證檢驗結果及其分析
1.成本粘性存在性的基本檢驗。我們根據所有權性質,將樣本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總樣本、國有企業樣本和非國有企業樣本,然后根據是否具有保盈動機 (TARGET=1或TARGET=0)分別再對這三個樣本進行細分。總樣本、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樣本中又分為有保盈動機的樣本和沒有保盈動機的樣本。
本文通過模型1進行回歸,得出的回歸結果為表4,從總樣本來看,沒有保盈動機(TARGET=0)時,β2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但當有保盈動機(TARGET=1)時,β2雖然還為負值,但已經不顯著了,且β2由原來的-0.4417下降到現在的-0.1184,國有樣本中不存在保盈動機時,β2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但當存在保盈動機時,β2雖然還為負值,但已經不顯著,且β2由原來的-0.3054下降到現在的-0.0225,非國有樣本中不存在保盈動機時,β2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但當存在保盈動機時,β2雖然還為負值,但不顯著,且β2由原來的-0.5119下降到現在的-0.2203,這支持了假設1(a),國有企業樣本的β2為-0.0225,遠小于非國有企業樣本的-0.2203,且兩者之間的差異Z值為1.80,支持了假設1(b)。
從總樣本來看,沒有保盈動機(TARGET=0)時,β1+β2為0.5592,但當有保盈動機時(TARGET=1),β1+β2為0.9261,兩者有0.3669的差異,國有樣本中不存在保盈動機時,β1+β2為0.7771,但當有保盈動機時β1+β2為1.0122,兩者的差異為0.2351,非國有樣本中不存在保盈動機時,β1+β2為0.4252,但當有保盈動機時β1+β2為0.8407,兩者的差異為0.4155,支持了假設2(a),但相對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成本粘性減少的幅度更大,原因很可能是在沒有保盈動機時非國有企業的成本粘性程度0.4252遠高于國有企業的成本粘性程度0.7771,所以保盈動機減少的成本粘性幅度大于國有企業。
本文通過模型2進行回歸,得出的回歸結果為表5,從總樣本來看,沒有保盈動機(TARGET=0)時,β2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但當有保盈動機(TARGET=1)時,β2雖然還為負值,但已經不顯著了,且β2由原來的-0.1553下降到現在的-0.0124,國有樣本中不存在保盈動機時,β2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但當存在保盈動機時,β2在0.0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非國有樣本中不存在保盈動機時,β2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但當存在保盈動機時,β2在0.0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有保盈動機反而比沒有保盈動機的費用粘性更大。總樣本和國有企業樣本支持了假設1(a),國有企業樣本的β2為0.1581(顯著),而非國有企業為-0.2497(顯著),二者之間的差異Z值為4.67,支持了假設1(b)。

表5 保盈動機對費用粘性影響的基本模型回歸結果
從總樣本來看,沒有保盈動機(TARGET=0)時,β1+β2為0.2404,但當有保盈動機(TARGET=1)時,β1+β2為0.3664,兩者有0.1640的差異,國有樣本中不存在保盈動機時,β1+β2為0.1902,但當有保盈動機時β1+β2為0.5094,兩者的差異為0.2743,非國有樣本中不存在保盈動機時,β1+β2為0.2271,但當有保盈動機時,β1+β2為0.2113,兩者的差異為-0.0158,總樣本和國有企業樣本支持了假設2(a)。國有企業具有保盈動機比沒有保盈動機減少了0.2743的費用粘性程度,而非國有企業保盈動機反而增加了費用粘性程度,所以支持了假設2 (b)。
表4和表5的結果表明,在保盈動機驅動下國有企業的成本費用粘性大于非國有企業,特別在業務量下降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更傾向于向下調整成本類和費用類資源,成本費用粘性減少的幅度更大。
2.全面檢驗模型下的實證結果。表6為對模型3進行回歸的結果,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成本粘性更嚴重,總樣本和國有企業樣本以及非國有企業樣本的γ2都為正,分別為0.1151、0.2263和0.0259,雖然不顯著,但說明保盈動機應該能夠減輕成本的粘性程度。所有γ1+γ2也都為正,但也都不顯著。說明在業務量下降時,保盈動機應該更能減輕成本的粘性程度。

表6 保盈動機對成本粘性影響的全面模型回歸結果
本文也發現控制變量資產負債率在總樣本和非國有企業樣本中與成本粘性呈負相關,而資本密集程度在國有企業樣本中與成本粘性呈負相關,基本上與本文所預計的一致。
表7為對模型4進行回歸的結果,總樣本和國有企業樣本的γ2都顯著為正,特別是國有企業樣本的γ2在0.01水平上顯著為正,但是非國有企業樣本的γ2在0.05水平上顯著為負,支持了假設1(a)。γ2在國有樣本與非國有樣本之間的差異Z值為3.33,在0.01水平上顯著,所以也就支持了假設1 (b)。

表7 保盈動機對費用粘性影響的全面模型回歸結果
總樣本和國有企業樣本與非國有樣本的γ1+γ2都為正,且都在0.05的水平上顯著,這就支持了假設2(a)。而γ1+γ2在國有樣本與非國有樣本之間的差異Z值為3.07,在0.01水平上顯著,所以也就支持了假設2(b)。
本文也發現控制變量資產負債率和以前年度收入變化量在總樣本、國有企業樣本和非國有企業樣本中與費用粘性成負相關,資本密集程度在國有企業樣本和非國有企業樣本中與費用粘性成負相關,和本文的預計基本一致。
表6和表7的結果表明,有保盈動機時國有企業的費用粘性減少幅度大于非國有企業,但非國有企業的成本粘性減少幅度大于國有企業,特別是在業務量下降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更傾向于向下調整的資源多為費用類,而非國有企業則更偏向于減少成本類的資源,國有企業的費用粘性降低的幅度更大。
(三)穩健性檢驗及檢驗結果。參照ABJ(2003)和孫錚、劉浩(2004),本文將模型的成本和費用變化及收入變化從一年區間分別擴展到兩年、三年和四年,檢驗在多期中保盈動機與產權性質對成本費用粘性的作用是否依然存在。根據基本模型,擴展出本文的全面回歸模型。模型中其他變量的定義在前面已經詳細闡述,在此不再贅述。
全面回歸模型:
表9和表10的結果表明,國有企業的成本和費用粘性都大于非國有企業,這說明在業務量下降的情況下,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更傾向于向下調整成本費用類的資源。此外,三四年期的成本粘性和四年期的費用粘性變化程度不高,由于成本費用粘性的反轉型也符合許多人的證明,所以也驗證了本文實證部分的結果。
四、研究結論和啟示

利用2007-2012年的成本和費用變化及收入變化分別為兩年、三年和四年的數據,并剔除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管理費用、銷售費用為負數或缺失的部分,得到最終的樣本數據。
研究發現,保盈動機確實能夠降低成本費用的粘性程度,但對成本粘性的作用不顯著,對費用粘性的降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對非國有企業保盈動機對國有企業費用粘性減少的作用更大,對非國有企業保盈動機似乎沒有起到作用。在業務量下降時,保盈動機確實能夠降低成本費用的粘性程度,但對成本粘性的作用不顯著,對費用粘性的降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對非國有企業保盈動機對國有企業費用粘性減少的作用也更大。通過利用2007-2012年的成本和費用變化及收入變化分別為兩年、三年和四年的數據對以上的結果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基本上和實證結果相一致,但是由于成本費用粘性的反轉型,四年期的成本費用粘性明顯減弱,有的幾乎消失了,這也就導致保盈動機和所有權性質對成本費用粘性的作用不是很明顯。

表9 穩健性檢驗成本差異多年期回歸結果
通過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啟示:一是認識和更準確地估計企業的成本費用粘性需要考慮保盈動機,相對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中保盈動機對成本費用粘性的作用更明顯。即存在保盈動機時,管理層更不愿意向下調整松弛資源,特別是國有企業。二是企業的成本費用粘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源配置效率,當忽略了保盈動機這個因素時,我國企業的成本費用粘性程度被高估了,特別是國有企業。
結果表明應該根據管理者的動機,特別是代理問題驅動下的資源調整決策,了解企業成本結構的決定因素,進一步改善企業的成本管理,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相對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應該進一步改革,提高國有企業資源的配置效率。以后的研究方向可以具體分行業,特別是考慮制造業中保盈動機和所有權性質對成本費用粘性的作用。■

表10 穩健性檢驗費用差異多年期回歸結果
1.陳磊、宋樂、施丹.2012.企業的成本粘性被高估了嗎?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中國會計評論,10(1):3-16。
2.顧鳴潤、楊繼偉、余怒濤.2012.產權性質、公司治理和真實盈余管理[J].中國會計評論,10(3):255-274。
3.吳聯生、薄仙慧、王亞平.2007.避免虧損的盈余管理程度:上市公司與非上市公司的比較[J].會計研究,2:44-51。
4.萬壽義、徐圣男.2012.中國上市公司費用粘性行為的經驗證據——基于上市公司實質控制人性質不同的視角[J].審計與經濟研究,27(4): 98-99。
5.ABEL,A.,J.E BERLY.1994.A Unified Model of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1369-84.
6.WEISS,D..2010.Cost Behavior and Analysts’Earnings Forecasts[J].The Accounting Review,32:144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