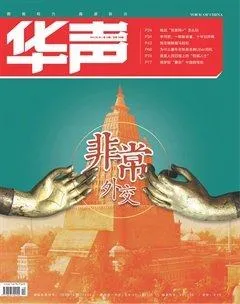一起由“襲警”引發的命案
那五
“襲警”是一個現代的法律概念,清朝在新政之前,并沒有建立近代警察編制,自然也沒有“襲警”的說法。這里的“襲警”一詞,只是借用而已。如果要仿照“襲警”造一個恰切的詞,不妨叫“襲役”——因為當時履行類似警察職能的公職人員,叫做“捕役”,也就是我們在古裝電視劇中常常看到的捕快。
今天我們就來說一樁發生在清朝嘉慶二年、由“襲警”引發的人命案。案件的當事人叫邵本,是縣衙一名負責緝拿盜賊的捕役。
話說某日,縣衙接報:盜賊李二等人盜竊了平民的馬資、衣物。縣令便命捕役邵本率領同事邵殿立、趙來法查緝李二一伙。
邵本很快偵查到李二等人下落,立馬乘夜前往緝拿。到達李二與同伙段二的藏身之所時,已是三更時分。捕役邵殿立與趙來法上前叩門,段二不知是捕役,出來開門探看,即被邵殿立當場拿獲。邵本則馬上沖進屋,想捉住李二。在邵本進屋后的短短幾分鐘時間內,屋內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成了一個謎。等到趙來法沖入房間時,發現李二已被邵本的鐵槍扎中腹部,倒地不起。三日后,李二殞命。
一起尋尋常常的盜竊案,現在卻演變成人命大案。邵本也從一名捕快變成了殺人嫌犯,接受調查與審訊。
法庭審訊的重點,放在盜賊李二在邵本沖入房間之后是否有“持械拒捕”、“襲警”的情節上。因為按照《大清律例》,“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勿論;若已就拘執及罪人不拒捕而殺,各以斗殺論。”意思是說,捕役當場殺死手持武器拒捕的逃犯,屬于履行職務,不必坐罪;如果逃犯已被拘執,或者沒有拒捕的舉動,捕役殺死他,則要論罪,按“斗殺罪”論處。只有一種情況下捕役不可殺死犯人:犯人無力(已被拘執)或無意拒捕的時候。因此,“邵本殺李二”案的審訊重點,就是認定李二有沒有拒捕。如果李二有拒捕之舉,則捕役邵本當場扎他一槍,屬于正當履行職務,無罪;如果李二沒有拒捕,邵本殺他,就犯了“斗殺罪”。依清律,斗殺致人死亡,要判絞刑。
邵本的口供說:在他沖進房間時,李二聞聲驚起,操起一把刀子,“欲行拒捕”。邵本擔心被他砍傷,情急之下,才用所帶鐵槍扎了他肚子。如此說來,捕役邵本動槍,顯然屬于正當履行職務了。
但是且慢。法官很快發現了一個疑點:“邵本等商同往拿竊賊時,已三更。李二等業已睡宿。邵本進屋時,必然昏黑,何以見及李二拾刀?拒捕情節已未確鑿。”換言之,捕役邵本有可能撒謊。
審訊到最后,法庭因為無法排除邵本撒謊的疑點,便按“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斗殺論”的律例,判處邵本絞刑。
案子經巡撫復審后,上報到中央刑部。刑部在復核時,又認為原來的判決太草率,捕役邵本并無殺死李二的動機,如果李二沒有持械拒捕,邵本似乎沒有理由要置李二于死地。如果邵本的動槍屬于正當履行職務,卻被判了絞刑,豈不是含冤而死?原判決“僅稱李二聞拿驚起,欲行拾刀拒捕,遽將邵本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斗殺論律,擬以絞候”,案情未明,擬罪失當:“聲敘未為明晰,罪名生死攸關”。
因此,刑部將案件駁回重審,“令該撫遵照指駁情節,推究確情,按律妥擬”。
邵本殺李二究竟是不是“罪人不拒捕而擅殺”,案子最后的審判結果又如何,限于史料記載沒有下文,我們現在也就不得而知了。這宗未知結果的公案告訴我們:現場監控視頻有多么重要。如果那時候有視頻資料,馬上就可以水落石出。當然,這里說的視頻資料是指未經剪輯的原始圖像記錄。
摘編自“有難度”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