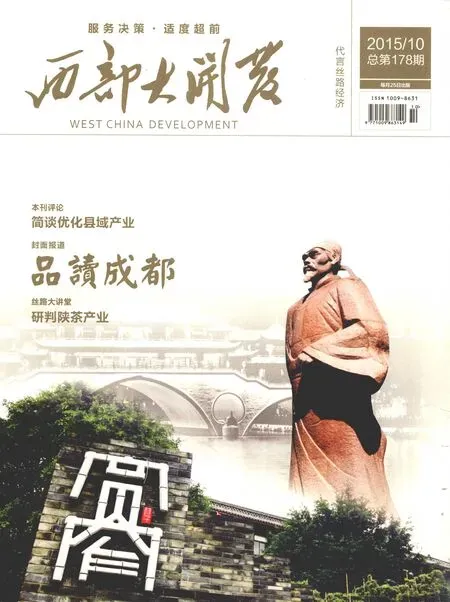重塑中國區域經濟新版圖
文 / 牛播坤 周笑雯
伴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創新以及新的區域規劃思路的展開,乃至反腐的深入推進,中國經濟地理正在勾勒出新的版圖。亦如中國今日傳統和新興冰火兩重天的產業表現,中國區域經濟也呈現分化裂變的新格局,有傳統老工業聚集區域的衰落塌陷,有能礦省份的增長困局,有塌方式腐敗地區的重整,也有鳳凰涅槃的創新聚集之地,以及在“兩橫三縱”上崛起的產業集群城市。
過去30多年來,基于資源稟賦、行政區劃及產業政策等,中國基本形成了東部對外開放-中部承接產業轉移-西部能礦-東北重工業,由沿海到腹地的單一層級的線性區域經濟地理格局。
伴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創新以及新的區域規劃思路的展開,乃至反腐的深入推進,中國經濟地理正在勾勒出新的版圖。亦如中國今日傳統和新興冰火兩重天的產業表現,中國區域經濟也呈現分化裂變的新格局,有傳統老工業聚集區域的衰落塌陷,有能礦省份的增長困局,有塌方式腐敗地區的重整,也有鳳凰涅槃的創新聚集之地,以及在“兩橫三縱”上崛起的產業集群。
維度1:能礦重化工省份普遍面臨增長困境

圖表1 2012-2015年能源類省區GDP增速走勢

圖表2 2015年較2012年能源類省區GDP下降點數
近年來,外需持續走弱及環保等監管措施趨嚴,給能源、礦產、重化及相關配套行業帶來巨大壓力;特別是2014年以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度持續走低,令國內中上游行業步入寒冬。從工業增加值的累計同比增速變化看,采礦業增速絕對水平顯著低于工業整體增速,且降幅也較工業整體下降更為嚴重;而在1999-2011年間,重工業增速顯著高于工業整體增長水平。從細分行業的工業增加值增速變化看,采礦和開采輔助等相關行業增速降幅居前。受此影響,能礦、重化工業主導的省區如山西、陜西、云南、內蒙古、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經濟增速、財政收入、PPI增速都出現較大幅度下滑(圖表1、2),山西、甘肅、新疆2015年上半年PPI分別下降10.8%、10.9%、16.7%。與其他省區相比,這些地區經濟結構調整的困難更多,企穩所需的時間也將更久。
維度2:西部區域受全球貿易低迷的影響顯著高于東南沿海
從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及貨物服務凈出口三大需求角度看,凈出口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已經顯著減弱;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凈出口對GDP貢獻曾連續三年為負。全國范圍看,2014年最終消費貢獻經濟增長的50.2%、資本形成貢獻48.5%,而凈出口僅貢獻1.3%。從各省GDP支出法核算情況看,出口對地方經濟的拉動作用存在顯著差異。以2008年為例,內地31省市區中,凈出口對GDP增長正向貢獻的省區有12個,廣東、浙江、江蘇、山東、河北五省居前;其余19個省區均為負向貢獻。2013年,該指標在前述五省均出現不同程度下滑,但浙江、江蘇、廣東目前仍維持在6%以上,在全國處于領先水平。
維度3:國有工業企業占比高的區域面臨更大的經濟下行壓力
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統計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占“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的比例,衡量省區內工業經濟對國有資本的依賴程度。
2010年以來的經濟增長中樞下移過程中,國有企業面臨比民營企業更大的經營壓力。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累計同比增速看,2010年以來國有企業工業增加值增速下滑速度明顯快于私營企業:2010年初國有企業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20.7%,而2015年7月已降至1.6%,下降了19.1個百分點,且尚未出現企穩跡象;同期私營企業工業增加值增速從24.0%降至8.8%,下降了15.2個百分點,2015年6、7月連續兩月小幅回升(圖表3)。上述國有企業占比較高的省區,普遍經歷了較大幅度的GDP增速“下臺階”(圖表4)。例如,2010年山西、黑龍江、吉林、內蒙古經濟增速分別為13.9%、12.7%、13.8%、15.0%,2015上半年增速已降至2.7%、5.1%、6.1%、6.9%,排名掉至全國末位。反觀國有經濟占比很低的浙江、江蘇兩省,2015上半年經濟增速8.3%、8.5%,僅較2010年低3.6、4.2個點,通過“互保斷鏈”、“老板跑路”等形式演繹了市場出清,快速而高效。

圖表3 2012-2015年 兩類企業工業增加值累計同比

圖表4 部分國資占比較高省區GDP增速變化
維度4:由市場驅動的內生創新力量注入區域發展新活力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是當下及未來中國經濟面臨的重要課題。隨著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下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經濟內涵增長的關鍵,而加大研發投入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途徑。以統計局公布大中型工業企業R&D經費投入占GDP比重作為衡量地區自主創新能力的指標,并與2012年以來GDP增速變化進行交叉對比(圖表5),浙江、廣東、上海、江蘇、山東等研發投入占比相對較高的地區,增速降幅相對較小;天津盡管降幅較大,但2012年增速全國第1、2015年上半年增速仍排名全國第3。其中,浙江2015上半年GDP增速已高于2012年,在全國范圍內率先企穩。
浙江和廣東作為最具內生創新力量的兩個區域,研發生產融合對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作用已經顯現。以浙江為例,2015年1-7月浙江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中,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新興產業占比分別達到36.2%、25.5%;工業投資中,用于技術改造的投資占比達到71.6%;服務業投資中,高技術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速均保持30%以上。一季度杭州市信息經濟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達22.1%,增長28.2%,其中電子商務增長48.7%,物聯網增長30.5%,互聯網金融增長110.6%,數字內容增長36.0%。深圳“創新驅動發展”模式更為典型,上半年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例達60.2%,信息技術、互聯網、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等高技術含量產業的增加值占比達GDP的38.4%。
維度5:“兩橫三縱”帶動中部城市群崛起
在“以陸橋通道、沿長江通道為兩條橫軸,以沿海、京哈京廣、包昆通道為三條縱軸”的“兩橫三縱”城鎮化戰略布局下(圖表6),中西部地區將重點吸納東部返鄉和就近轉移的農民工人口,加快發展產業集群。鄭州、武漢作為“兩橫三縱”關鍵節點,明顯受益于產業梯次轉移,對省內乃至周邊經濟的輻射效應日益明顯。2000年武漢市GDP約1207億元,占湖北省的比重約34.0%;2014年武漢市GDP突破1萬億元大關,占全省比重提高到36.8%。2000年鄭州市GDP約728億元,占河南省比重14.4%;2014年鄭州市GDP達到6783億元,占全省比重升至19.4%,對省內經濟的帶動尤為明顯。
維度6:地方治理穩定的區域經濟更為平穩
反腐帶來的地方治理結構重建也關系到地方經濟的發展。四川、山西、云南等省區短期內數十名省級、地級官員違紀被查,同期當地經濟發展情況明顯落后于經濟結構相似、增速排名相近的兄弟省區。
以云南為例。云南和貴州地理位置相近、產業結構相似,歷史上GDP增速絕對值及排名也較為接近。然而2013年以來,兩個省的經濟增長情況出現分化。貴州延續了一直以來的兩位數增長,2015年上半年經濟增速10.7%,排名保持全國第2,較2012年下降2.9個點。云南經濟增速和排名均出現較快下滑,2015年上半年GDP增速8.0%,排名由全國第4位降至第15位;較2012年下降5.0個點,降幅居全國第5位。
山西作為“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典型,經濟受到的影響則更加嚴重。以臨近兄弟省區內蒙為例,山西、內蒙古都是傳統產煤大省,產業結構相似,歷史上經濟增速差異不大。2014年以來兩地區經濟都受到煤炭價格大幅下跌影響,然而山西的經濟增速明顯低于內蒙古。2015年上半年山西經濟增速僅2.7%,已降至全國倒數第2位,較2012年大幅回落了7.4個百分點,回落幅度全國第1;內蒙古增速6.9%,較2012年回落4.6個百分點,回落幅度全國第8。

圖表6 “兩橫三縱”城鎮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