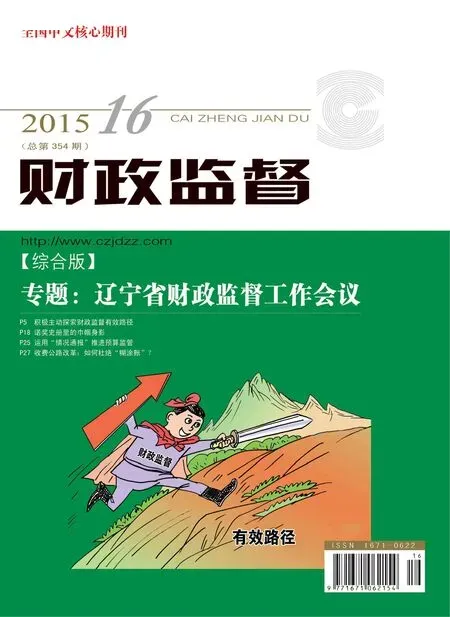從法律基本概念論預(yù)算法修訂
●黃炎斌
從法律基本概念論預(yù)算法修訂
●黃炎斌

預(yù)算法修訂已經(jīng)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審議通過,并于今年開始正式實(shí)施。這是預(yù)算法自1994年頒布以來,過去二十年的第一次修訂。此次修訂,秉承開門立法的理念,廣泛聽取各方修訂意見,共收集全國(guó)意見三四十萬條,形成了對(duì)預(yù)算法修訂的強(qiáng)大民意基礎(chǔ)。本次修訂,從公布的預(yù)算法修正案來看,改動(dòng)或說變動(dòng)幅度不可謂不大,但是,若從法的幾個(gè)基本方面看,已經(jīng)通過的修訂的預(yù)算法,仍存在一些不足與缺陷,甚至是存在比較大的缺陷,與依法治國(guó)、依法執(zhí)政、依法行政所需要的法律體系和法律規(guī)范仍有距離或不相適應(yīng),還不能完全滿足現(xiàn)實(shí)的需要,還有比較大的改進(jìn)空間。本文試從法律基本概念著手,探析新預(yù)算法存在的不足。
一、立法宗旨
立法宗旨是指立法的中心思想,它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為什么要立法,進(jìn)行立法的意義何在,它要達(dá)到什么目的。立法宗旨的確立,為整部法律定下了基調(diào),同時(shí)也奠定了法律規(guī)范的基本方向。因此,法律宗旨必須清晰而明確。法律之所以要不斷進(jìn)行修訂,是因?yàn)殡S著時(shí)代和環(huán)境的變化,原有的立法宗旨及其法律規(guī)范,已經(jīng)不適應(yīng)變化了的時(shí)代要求。這次預(yù)算法修訂,其立法宗旨表述為 (新法第一條):“為了規(guī)范政府收支行為,強(qiáng)化預(yù)算約束,加強(qiáng)對(duì)預(yù)算的管理和監(jiān)督,建立健全全面規(guī)范、公開透明的預(yù)算制度,保障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健康發(fā)展,根據(jù)憲法,制定本法。”與舊法(舊法的立法宗旨是:“為了強(qiáng)化預(yù)算的分配和監(jiān)督職能,健全國(guó)家對(duì)預(yù)算的管理,加強(qiáng)國(guó)家宏觀調(diào)控,保障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的健康發(fā)展,根據(jù)憲法,制定本法”)相比,其立法宗旨改進(jìn)了許多,新法宗旨突出了對(duì)預(yù)算與執(zhí)行主體 (特別是對(duì)政府)的約束與規(guī)范、對(duì)預(yù)算的管理與監(jiān)督、預(yù)算的全面公開與透明,說明新法已摒棄了將法律作為政府調(diào)控工具的舊有思維,向著正確的立法方向邁出了堅(jiān)定的步子。
應(yīng)當(dāng)指出的是,就目前我國(guó)社會(huì)的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而言,預(yù)算的公平與公正,比之公開透明,要更為迫切,讓發(fā)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由全體人民共享,更加離不開預(yù)算的公平與公正。或者再退一步說,制定更為合理科學(xué)的預(yù)算制度,也是預(yù)算立法目的的一個(gè)選項(xiàng)。另外,實(shí)現(xiàn)預(yù)算公平公正的目標(biāo),預(yù)算民主是正途。因此,預(yù)算民主作為預(yù)算公平主要的實(shí)現(xiàn)手段,融入預(yù)算法的立法宗旨,也是順理成章的。就此而言,新預(yù)算法的立法宗旨,仍然只著眼于當(dāng)前,欠缺前瞻性,仍不夠全面,還需要適當(dāng)加入更為長(zhǎng)遠(yuǎn)的目標(biāo),使新法更有針對(duì)性、更具科學(xué)性。
二、法律關(guān)系
法律關(guān)系是指法律在調(diào)整人們行為的過程中形成的特殊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關(guān)系。或者說,法律關(guān)系是指被法律規(guī)范所調(diào)整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法律關(guān)系由三要素組成,即法律關(guān)系的主體、法律關(guān)系的客體和法律關(guān)系的內(nèi)容。沒有特定的法律關(guān)系主體的實(shí)際法律權(quán)利和法律義務(wù),就不可能有法律關(guān)系的存在。法律關(guān)系是法律規(guī)范的實(shí)現(xiàn)形式,是法律規(guī)范的內(nèi)容在現(xiàn)實(shí)中的具體貫徹。法律關(guān)系是法律的主心骨,任何一種法律規(guī)范只能在具體的法律關(guān)系中才能得以實(shí)現(xiàn)。
按照法律關(guān)系主體是法律關(guān)系的參與者,是指參與法律關(guān)系,依法享有權(quán)利和承擔(dān)義務(wù)的當(dāng)事人,也就是在法律關(guān)系中,一定權(quán)利的享有者和一定義務(wù)的承擔(dān)者的定義,法律關(guān)系主體必須全面和完整,任何法律主體的缺位或缺失,都構(gòu)成法律的硬傷。在每一具體的法律關(guān)系中,主體的多少各不相同,在大體上都屬于相對(duì)應(yīng)的雙方:一方是權(quán)利的享有者,成為權(quán)利人;另一方是義務(wù)的承擔(dān)者,成為義務(wù)人。任何法律主體的行為或義務(wù),都應(yīng)得到體現(xiàn)和尊重,任何法律主體涉及法律關(guān)系客體的行為或義務(wù),都應(yīng)得到規(guī)范,并能體現(xiàn)于法律條文中,這是法律關(guān)系的重要體現(xiàn)。
具體到預(yù)算法,其法律關(guān)系是什么,必須準(zhǔn)確界定,在此基礎(chǔ)上,理順涉及預(yù)算的各種法律主體、法律關(guān)系的客體,以及其相互之間的關(guān)系,按照主體、行為(權(quán)利行為或義務(wù)行為)、責(zé)任的條文結(jié)構(gòu),鑲?cè)腩A(yù)算編制、審查批準(zhǔn)、預(yù)算執(zhí)行、調(diào)整、監(jiān)督、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全過程,并對(duì)相關(guān)主體每一環(huán)節(jié)相應(yīng)權(quán)利或義務(wù)行為進(jìn)行法定配置,同時(shí)對(duì)應(yīng)于適當(dāng)?shù)姆韶?zé)任,構(gòu)筑起具有嚴(yán)密邏輯關(guān)系的預(yù)算法律規(guī)范縱向架構(gòu)。
新預(yù)算法雖然沒有明確表述預(yù)算法律關(guān)系,但從公共財(cái)政角度,其職能是對(duì)公共資金的籌集與分配,本質(zhì)上表現(xiàn)為一種利益(資源)的共享關(guān)系,它是通過公共委托與代理的形式實(shí)現(xiàn)的,而預(yù)算則是實(shí)施和調(diào)整利益關(guān)系的基本手段及基本方式。所以,預(yù)算法律關(guān)系可表述為相關(guān)利益主體就涉及預(yù)算的分配內(nèi)容、形式、過程與結(jié)果等相互之間發(fā)生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預(yù)算法律應(yīng)當(dāng)圍繞這個(gè)預(yù)算關(guān)系進(jìn)行規(guī)范。就相關(guān)法律關(guān)系主體而言,預(yù)算法律關(guān)系,通俗地可表述為“在一定預(yù)算范圍內(nèi),你有編制和執(zhí)行預(yù)算的權(quán)利,你有編制好和執(zhí)行好預(yù)算的義務(wù);你有審批和監(jiān)督預(yù)算及預(yù)算執(zhí)行的權(quán)利,同時(shí)你有審批好和監(jiān)督好預(yù)算及其執(zhí)行的義務(wù);你有審批預(yù)算調(diào)整的權(quán)利,同時(shí)你有嚴(yán)格執(zhí)行法律對(duì)此所規(guī)定的義務(wù);你有無條件獲得監(jiān)督預(yù)算編制和執(zhí)行的權(quán)利(這里指體制外監(jiān)督主體),但不須有特定的義務(wù)”。
新法將預(yù)算法律關(guān)系主體按照預(yù)算法律所規(guī)范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不同,劃分為:預(yù)算編制主體、預(yù)算審批主體、預(yù)算執(zhí)行主體、預(yù)算監(jiān)督主體。預(yù)算法修正案已囊括了這些主體,但是新修訂的預(yù)算法,未能完全影射預(yù)算法律關(guān)系,其法律關(guān)系并不十分清晰,一些相關(guān)主體的權(quán)利義務(wù)不相配,與其所應(yīng)承擔(dān)的責(zé)任不相稱,存在主體有權(quán)利而無義務(wù)、有權(quán)利而無責(zé)任 (有監(jiān)督權(quán)利,無監(jiān)督責(zé)任或義務(wù)),或主體權(quán)利空泛,或主體權(quán)利過少,或?qū)ν粰?quán)利(如預(yù)算參與權(quán))進(jìn)行選擇性授權(quán)(一些主體有,一些主體無)。如何將預(yù)算主體的各種預(yù)算行為(權(quán)力、義務(wù)與責(zé)任),將可能影響預(yù)算編制及執(zhí)行質(zhì)量的各種因素進(jìn)行解剖分析,全部準(zhǔn)確地抽取出來,并將之植入法律規(guī)范中,體現(xiàn)預(yù)算法律關(guān)系主線,是預(yù)算法修訂必須考慮的一個(gè)重要方面。
就此而言,新法沒有準(zhǔn)確抽離預(yù)算法律關(guān)系,并按此核心架構(gòu)法律規(guī)范。
三、法律行為
這里指的是預(yù)算法律行為,不是抽象的法律行為。根據(jù)法律關(guān)系客體是指法律關(guān)系主體之間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所指向的對(duì)象的定義,預(yù)算法律關(guān)系客體就是主體對(duì)財(cái)政資金的分配、使用及管理的過程,具體來說是財(cái)政資金的運(yùn)作過程,筆者將預(yù)算法律關(guān)系主體行使權(quán)利與履行義務(wù)的行為,即籌集、安排、調(diào)度、使用和監(jiān)督評(píng)價(jià)屬于預(yù)算資金的一系列過程,統(tǒng)稱為預(yù)算法律行為。這個(gè)行為過程必須詳盡置于預(yù)算法律規(guī)范之中,以此作為形成預(yù)算法律制度的中心內(nèi)容。法律關(guān)系主體必須與客體對(duì)接到位,具有相對(duì)應(yīng)的權(quán)利義務(wù)與責(zé)任關(guān)系,任何具有構(gòu)成與客體相對(duì)應(yīng)的主體及其行為,都不能游離于法律規(guī)范之外。
就此而言,預(yù)算法對(duì)法律關(guān)系客體的集合與解構(gòu)不夠全面和詳盡,造成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條文有所欠缺,嚴(yán)重弱化對(duì)預(yù)算過程的約束。如新法涉及轉(zhuǎn)移支付的預(yù)算法律文本只有兩條,即第一章總則第十六條和第四章預(yù)算編制的第三十八條,只對(duì)轉(zhuǎn)移支付作了原則性規(guī)定,并無設(shè)置如何更進(jìn)一步的法律規(guī)定,與目前預(yù)算實(shí)踐所需要的制度規(guī)范需求很不相稱,特別是在專項(xiàng)轉(zhuǎn)移支付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制度供給缺口。第三十八條規(guī)定:“一般性轉(zhuǎn)移支付應(yīng)當(dāng)按照國(guó)務(wù)院規(guī)定的基本標(biāo)準(zhǔn)和計(jì)算方法編制;專項(xiàng)轉(zhuǎn)移支付應(yīng)當(dāng)分地區(qū)、分項(xiàng)目編制。”專項(xiàng)轉(zhuǎn)移支付按照分地區(qū)、分項(xiàng)目編制,這是預(yù)算編制的形式要求,并且這種形式已經(jīng)作為預(yù)算編制的結(jié)果呈現(xiàn)并獲得通過,而專項(xiàng)轉(zhuǎn)移支付為什么是這個(gè)規(guī)模,為什么是這些項(xiàng)目,這些項(xiàng)目是如何被納入預(yù)算的,這些項(xiàng)目應(yīng)當(dāng)達(dá)到什么目標(biāo),如何對(duì)這些項(xiàng)目及其應(yīng)達(dá)到的目標(biāo)進(jìn)行監(jiān)督等等,這些關(guān)鍵性內(nèi)容,均無一涉及。目前,專項(xiàng)轉(zhuǎn)移支付多頭供給,既有來自財(cái)政部門的,也有來自專業(yè)部門的,同一項(xiàng)目可以獲得不同渠道的資金來源,只重獲得,不重使用,隨意立項(xiàng),實(shí)行撒胡椒面式的分配,對(duì)有限的財(cái)政資源造成了極大的浪費(fèi),甚至人人都把它當(dāng)成“唐僧肉”,財(cái)政領(lǐng)域發(fā)生的違法違紀(jì)案件也多發(fā)于此。據(jù)公布的有關(guān)統(tǒng)計(jì)數(shù)字,2013年全國(guó)專項(xiàng)轉(zhuǎn)移支付預(yù)算數(shù)為19265.86億元,專項(xiàng)支付項(xiàng)目名目繁多,達(dá)幾百種,數(shù)不勝數(shù),幾乎覆蓋了所有的預(yù)算科目,如何管理好這一龐大預(yù)算,特別是管理好有二次預(yù)算分配權(quán)的部門掌握的專項(xiàng)資金,使之能夠達(dá)成預(yù)期的特定政策目標(biāo),如何讓專項(xiàng)轉(zhuǎn)移支付的財(cái)政自由裁量權(quán),裝進(jìn)法律制度的籠子,受到應(yīng)有的約束、規(guī)范和節(jié)制,新法在此未能體現(xiàn)。
又如,新法第四十八條“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和地方各級(jí)人民代表大會(huì)對(duì)預(yù)算草案及其報(bào)告、預(yù)算執(zhí)行情況的報(bào)告重點(diǎn)審查下列內(nèi)容:預(yù)算安排是否符合本法的規(guī)定”。但是本法對(duì)預(yù)算安排的規(guī)定都有哪幾條呢?又是如何規(guī)定的呢?審查內(nèi)容的第四項(xiàng)“重點(diǎn)支出和重大投資項(xiàng)目的預(yù)算安排是否適當(dāng)”,第六項(xiàng)“對(duì)下級(jí)政府的轉(zhuǎn)移支付性支出預(yù)算是否規(guī)范、適當(dāng)”。那么,對(duì)其審查又是憑借哪一條規(guī)定、憑什么標(biāo)準(zhǔn)來判斷呢?這些才是預(yù)算編制的重要內(nèi)容和依據(jù),法律本應(yīng)當(dāng)在此加以嚴(yán)格規(guī)范,使預(yù)算的編制做到科學(xué)、合理、有效,但恰恰在此,法律規(guī)范出現(xiàn)了空缺。
四、法律規(guī)范
法律規(guī)范是指法律中所包含的主體如何行為及其相應(yīng)后果的行為標(biāo)準(zhǔn)或行為尺度,是法律的基本或核心內(nèi)容。一般來說,每一個(gè)法律規(guī)范都是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兩部分構(gòu)成。行為模式分為可以為、應(yīng)該為、不可為三種。法律規(guī)范在成文法中由法律條文來具體體現(xiàn),并以授權(quán)性規(guī)范、命令性規(guī)范和禁止性規(guī)范三種形式出現(xiàn)。縱觀新預(yù)算法,一些法律條文并沒有按照法律規(guī)范的內(nèi)在邏輯結(jié)構(gòu)來措置,行為模式不清,法律后果不明。
(一)法律條文過于原則和籠統(tǒng),在現(xiàn)實(shí)中難以操作執(zhí)行
我國(guó)的立法原則(習(xí)慣)從來都是宜粗不宜細(xì),這種立法原則與法律原則是背道而馳的,與現(xiàn)代法制精神極不相符,是亟需摒棄的立法觀念。過于原則的文字表述,只有立法者才能理解與領(lǐng)會(huì)條文含義,于是便出現(xiàn)了立法之后釋法(所謂釋法,就是隨后制定條例與規(guī)章,以行政立法形式來解析法律)不斷的怪現(xiàn)象。不僅如此,法律條文過于原則,法律主體如何執(zhí)行,有如一道難題,難以操作。如新法第十七條“各級(jí)預(yù)算的編制、執(zhí)行應(yīng)當(dāng)建立健全互相制約、互相協(xié)調(diào)的機(jī)制”。這個(gè)機(jī)制應(yīng)當(dāng)怎樣建立?由誰去建立這樣一種機(jī)制?不按法律建立這樣的機(jī)制,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怎樣的后果?都不得要領(lǐng)。這樣的法律條文有相當(dāng)于無,起不到任何的約束作用。第十六條“國(guó)家實(shí)行財(cái)政轉(zhuǎn)移支付制度。財(cái)政轉(zhuǎn)移支付應(yīng)當(dāng)規(guī)范、公平、公開,以推進(jìn)地區(qū)間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為主要目標(biāo)”。十六條作為法律規(guī)定明確之前,各級(jí)政府已經(jīng)實(shí)行轉(zhuǎn)移支付制度,問題不在于有沒有這條規(guī)定,而是應(yīng)當(dāng)怎樣建立轉(zhuǎn)移支付制度,如何做才是規(guī)范的轉(zhuǎn)移支付制度,這里涉及財(cái)政管理相當(dāng)重要的內(nèi)容 ,必須加以規(guī)范。目前,一些地方財(cái)政一般轉(zhuǎn)移支付不大,但專項(xiàng)轉(zhuǎn)移支付卻相當(dāng)大,這里面的管理相當(dāng)混亂,問題相當(dāng)多,財(cái)政部門和人員違法違紀(jì)多集中在此領(lǐng)域,原因就是目前對(duì)財(cái)政專項(xiàng)轉(zhuǎn)移支付缺乏應(yīng)有的制度規(guī)范與約束,存在相當(dāng)大的制度漏洞,極容易串通合謀騙取財(cái)政資金。預(yù)算法律應(yīng)當(dāng)在此建立一個(gè)制度籠子,將財(cái)政部門及其人員的財(cái)政分配自由裁量權(quán)極大地壓縮,堵塞此漏洞。但至少新預(yù)算法,還是欠缺此方面比較詳細(xì)的規(guī)范。
(二)預(yù)算監(jiān)督條文虛化,可問責(zé)性弱
由于預(yù)算審查(第五章)并未列入監(jiān)督框架,法律是將之作為一種政治權(quán)利的行使形式而規(guī)定的,現(xiàn)實(shí)中,一年一度的預(yù)算審查,變成一種儀式,集體審查不強(qiáng)調(diào)審查的程序、審查的方式、審查的結(jié)果,以及應(yīng)當(dāng)取得的成效,并沒有從實(shí)質(zhì)監(jiān)督視角去審查從而發(fā)現(xiàn)問題,并切實(shí)履行審查責(zé)任。盡管有第四十八條規(guī)范,但可以預(yù)見,最后是走過場(chǎng),起不了作用。由于將預(yù)算監(jiān)督的內(nèi)容前置到預(yù)算審查,因此直接導(dǎo)致了第九章監(jiān)督內(nèi)容的虛化,沒有任何實(shí)質(zhì)性內(nèi)容。新法監(jiān)督條款共八條,條款設(shè)置及內(nèi)容非常簡(jiǎn)潔和簡(jiǎn)單(第八十六條應(yīng)該不屬于監(jiān)督內(nèi)容,只是規(guī)定政府應(yīng)當(dāng)履行預(yù)算執(zhí)行情況報(bào)告程序),其中三條(第八十七、八十八、九十條)強(qiáng)調(diào)的是政府系統(tǒng)內(nèi)各主體自我監(jiān)督、自主監(jiān)督,基本上說的是監(jiān)督預(yù)算的執(zhí)行,據(jù)筆者對(duì)條文的理解,它內(nèi)在的意思是指監(jiān)督預(yù)算執(zhí)行的進(jìn)度,僅此而已。這樣的監(jiān)督有與無,毫無實(shí)際意義,而且難以判斷其是否履行了監(jiān)督職責(zé),也難以追責(zé),要糾正其違反預(yù)算的行為,更是一句空話。由于監(jiān)督條文的虛化,也直接導(dǎo)致了監(jiān)督責(zé)任的不對(duì)稱或不對(duì)等,直接導(dǎo)致第十章法律責(zé)任欠缺對(duì)預(yù)算監(jiān)督的歸責(zé)條款。
對(duì)預(yù)算的監(jiān)督,應(yīng)著重于預(yù)算編制及執(zhí)行過程監(jiān)督的實(shí)質(zhì)化,監(jiān)督的內(nèi)容、監(jiān)督的形式、監(jiān)督的程序及過程、監(jiān)督的結(jié)果、監(jiān)督的責(zé)任等主要監(jiān)督要素,應(yīng)當(dāng)涵括于法律文本的規(guī)定之中,使各種法律主體權(quán)利、義務(wù)與責(zé)任在法律文本中得以統(tǒng)一,彰顯監(jiān)督法權(quán),真正使監(jiān)督有法可依,有責(zé)可循,不流于形式。
(三)法律條文授權(quán)(賦權(quán))不對(duì)等
第四十五條“縣、自治縣、不設(shè)區(qū)的市、市轄區(qū)、鄉(xiāng)、民族鄉(xiāng)、鎮(zhèn)的人民代表大會(huì)舉行會(huì)議審查預(yù)算草案前,應(yīng)當(dāng)采取多種形式,組織本級(jí)人民代表大會(huì)代表,聽取選民和社會(huì)各界的意見”。也就是說,縣級(jí)以上的預(yù)算草案不用接受聽取選民和社會(huì)各界的意見,這是毫無道理的。本來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條款,體現(xiàn)了預(yù)算民主的精神,應(yīng)更加具體和詳細(xì)規(guī)范才對(duì),但法律對(duì)此卻作了選擇性授權(quán),使公民全面參與預(yù)算權(quán)利得不到應(yīng)有的尊重,體現(xiàn)了法律授權(quán)的不平等。
(四)法律條文向下授權(quán)過多
從預(yù)算法修訂的目的看,顯然不是為了使預(yù)算行為與過程更加便捷,更方便某些部門行使權(quán)力,更不是作為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宏觀調(diào)控的工具,而主要是為了預(yù)算的公平、公正及公開,預(yù)算行為與過程得到更多的約束與規(guī)范。就此而言,新修訂的預(yù)算法,應(yīng)當(dāng)體現(xiàn)為更多的限權(quán),而不是賦權(quán),是一部以限權(quán)為主兼有一定賦權(quán)的法律。但從新法內(nèi)容看,法律規(guī)范向下授權(quán)過多,形成了“法權(quán)”(筆者認(rèn)為“法權(quán)”是某種行為應(yīng)納入法的架構(gòu)中,并且該行為應(yīng)由相應(yīng)法律所約束和規(guī)范的權(quán)利或權(quán)力)過多轉(zhuǎn)移,特別是第四章預(yù)算編制,如一般性轉(zhuǎn)移支付和專項(xiàng)轉(zhuǎn)移支付、預(yù)算周轉(zhuǎn)金、預(yù)算穩(wěn)定調(diào)節(jié)基金、地方債務(wù)規(guī)模、涉及預(yù)算分配權(quán)重大問題的法權(quán)轉(zhuǎn)移。在諸多影響預(yù)算編制及執(zhí)行質(zhì)量的因素中,預(yù)算分配權(quán)是最為重要,也是最值得重視的方面,它從根本上影響預(yù)算是否科學(xué)、合理,是否公平與公正,是否具有效力,必須將之納入預(yù)算法權(quán)中,進(jìn)行嚴(yán)格的法律規(guī)范。預(yù)算分配權(quán)是公共權(quán)力,現(xiàn)實(shí)中以賦權(quán)委托行使的方式,但必須將預(yù)算分配的各種標(biāo)準(zhǔn)和規(guī)模、分配領(lǐng)域,在獲得公共討論通過后,基本固定下來,形成法律標(biāo)準(zhǔn),從而使公共預(yù)算編制有法可依。重大項(xiàng)目的預(yù)算安排,必須經(jīng)過嚴(yán)格的論證,并征求公共意見,未經(jīng)過公共討論或論證的所謂重大項(xiàng)目,不得列入預(yù)算,這也是一項(xiàng)預(yù)算法權(quán)。區(qū)域公共服務(wù)均等化也必須有具體的標(biāo)準(zhǔn),也應(yīng)納入預(yù)算法權(quán)。專項(xiàng)轉(zhuǎn)移支付的立項(xiàng)、分配、使用、效益等,也必須有法可依。分級(jí)預(yù)算與政府事權(quán)如何清晰界定并對(duì)接,預(yù)算超收如何安排,重大的預(yù)算調(diào)整,對(duì)國(guó)企的財(cái)政補(bǔ)貼等等,這些重大的預(yù)算分配事項(xiàng),涉及預(yù)算分配權(quán)的多個(gè)方面,法律必須予以規(guī)范,以充分體現(xiàn)預(yù)算法權(quán)。
預(yù)算權(quán)或說預(yù)算分配權(quán),屬于預(yù)算法權(quán),法律本身所需要的法權(quán)應(yīng)當(dāng)?shù)玫綕M足,并且將之直接鑄于法律文本中,不能隨意轉(zhuǎn)移。雖然法權(quán)在某種情形下,作出適當(dāng)?shù)霓D(zhuǎn)移是應(yīng)該的,也是必要的,但法權(quán)在法律中轉(zhuǎn)移或讓渡過多,其造成的結(jié)果是,名義上執(zhí)行的是“法”,實(shí)際上執(zhí)行的是“規(guī)”(行政法規(guī))。法律空,法規(guī)實(shí),最后可能是部門規(guī)章實(shí),而法律被虛化。法權(quán)轉(zhuǎn)移或讓渡過多已成為立法過程中的一大弊端,新法對(duì)自身的法權(quán)轉(zhuǎn)移或說讓渡過多,支解了預(yù)算法的系統(tǒng)性、嚴(yán)謹(jǐn)性、完整性,損害了法律的權(quán)威性。
預(yù)算分配權(quán)對(duì)預(yù)算的公平公正及結(jié)果具有重大影響,在法律規(guī)范中必須保留,而預(yù)算編制權(quán),則可通過法律賦權(quán)轉(zhuǎn)移。
可以肯定的是,國(guó)家預(yù)算編制主體并非預(yù)算分配主體,從法理上是每個(gè)公民進(jìn)而是各級(jí)人民代表大會(huì)(代表全體公民),預(yù)算分配權(quán)應(yīng)由人民代表大會(huì)行使,但新法沒有將之劃分開來,也沒有明確賦權(quán),各種預(yù)算編制主體,通過編制預(yù)算,卻隱含獲得了預(yù)算分配權(quán),這是極為不恰當(dāng)?shù)模@是新法的一大硬傷。財(cái)政資金使用的效率低下,甚至被肆意挪用、浪費(fèi),以及財(cái)政資金分配的公平與公正得不到保障,與法律至今沒有對(duì)預(yù)算分配權(quán)作出規(guī)范,有莫大關(guān)系。
五、法律責(zé)任
法律責(zé)任是指違反法律規(guī)定應(yīng)該受到的責(zé)任追究和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的后果。法律責(zé)任的措置,是法律權(quán)威性和威懾力的保證,法律責(zé)任應(yīng)當(dāng)細(xì)致、精確、完整,以最大限度減少執(zhí)行過程中的自由裁量權(quán),減少人為干預(yù)和操作法律的空間。按照權(quán)利義務(wù)責(zé)任相統(tǒng)一的原則,法律關(guān)系所確定的各種主體,都有相應(yīng)的權(quán)、義和責(zé)任,就預(yù)算法律關(guān)系而言,只有體制外的公民這個(gè)法律主體,不需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除此之外,每個(gè)法律主體都要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法律責(zé)任。新預(yù)算法在法律責(zé)任設(shè)置上,存在一些缺陷。
(一)法律責(zé)任與行為規(guī)范在法律關(guān)系主體上未能一致,法律主體歸責(zé)不夠全面,有所欠缺
新法第十章《法律責(zé)任》的承擔(dān)主體都是“各級(jí)政府、有關(guān)部門、單位及其工作人員”,但責(zé)任法定卻沒有將政府作為主體,缺少對(duì)政府整體的法律責(zé)任規(guī)范,也沒有將部門、單位作為主體,進(jìn)行法律責(zé)任規(guī)范(全章只有第九十五條“對(duì)單位給予警告或者通報(bào)批評(píng)”)。可以肯定的是,法律將政府作為主體,應(yīng)當(dāng)具有可歸責(zé)性,其預(yù)算行為也應(yīng)具有可歸責(zé)性。此外,法律專門賦予政府監(jiān)督權(quán)(第八十七條)、縣級(jí)以上政府審計(jì)部門監(jiān)督權(quán)(第八十八條),但相對(duì)應(yīng)的法律責(zé)任缺失。還有,作為權(quán)力機(jī)構(gòu)擁有監(jiān)督權(quán),如不履行法律所賦予的權(quán)力,應(yīng)承擔(dān)何種法律責(zé)任?新預(yù)算法都沒有涉及,凡此種種,與法律權(quán)利義務(wù)責(zé)任不相稱。監(jiān)督無責(zé),監(jiān)督便會(huì)軟弱無力,法律之權(quán)威也因此消減。
(二)法律責(zé)任不全面、責(zé)任偏輕,約束力弱
法律責(zé)任有刑罰、行為罰、經(jīng)濟(jì)罰、行政處罰等多種形式,它是由違反法律的情節(jié)的輕重所決定的,與責(zé)任大小直接相關(guān),雖然不是每部法律都設(shè)置所有形式的罰則,但是作為一部重要的經(jīng)濟(jì)法律,只設(shè)置行為罰、行政罰和刑罰,而獨(dú)欠缺經(jīng)濟(jì)罰,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有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預(yù)算法約束的對(duì)象,其經(jīng)濟(jì)來源來自于財(cái)政撥款,對(duì)其處予經(jīng)濟(jì)罰,是左口袋的錢進(jìn)了右口袋,是沒有意義的。違反預(yù)算法律的經(jīng)濟(jì)所得,可能是由單位所得,也可能是由個(gè)人所得,當(dāng)個(gè)人所得不是進(jìn)了個(gè)人的口袋,而是由單位人均分,或是由幾個(gè)人均分,或是用作其他用途,同時(shí)構(gòu)不成刑事法律責(zé)任,對(duì)個(gè)人實(shí)施經(jīng)濟(jì)罰,是天經(jīng)地義的。退而言之,當(dāng)對(duì)單位實(shí)施經(jīng)濟(jì)罰,而且規(guī)定只能從人員經(jīng)費(fèi)列賬,直接減少個(gè)人所得,甚至個(gè)人損失是所得的幾倍,就會(huì)大大降低違法的幾率,無疑具有威懾作用。遺憾的是,新法法律責(zé)任一章,無論對(duì)單位還是個(gè)人,經(jīng)濟(jì)罰則全部缺失。由于預(yù)算法律責(zé)任在預(yù)算法上規(guī)定得過于籠統(tǒng),且責(zé)任形式不具有多樣性,不僅影響了預(yù)算監(jiān)督,同時(shí)也極大地影響了預(yù)算法的約束效力。
(三)新預(yù)算法的執(zhí)法主體,同時(shí)又是執(zhí)行主體,難以究責(zé)
第九章《監(jiān)督》,賦予各個(gè)主體監(jiān)督執(zhí)法權(quán),并規(guī)定有上對(duì)下的監(jiān)督權(quán)力。盡管如此,但由于各個(gè)監(jiān)督主體同時(shí)又是預(yù)算的執(zhí)行主體,他們是否違法,不能由自己判定,必須由第三者來判定,預(yù)算法對(duì)此卻沒有規(guī)范。第十章《法律責(zé)任》第九十二條至九十五條,“各級(jí)政府及有關(guān)部門、單位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責(zé)令改正……對(duì)人員追究行政責(zé)任或依法給予處分”。由誰責(zé)令改正?是由人大,還是上級(jí)政府、同級(jí)政府,或是縣級(jí)以上審計(jì)部門、政府所屬部門?又由誰來追究行政責(zé)任或依法給予行政處分?現(xiàn)實(shí)中最尖銳的事實(shí)是,為對(duì)沖2008年國(guó)際金融風(fēng)暴對(duì)我國(guó)經(jīng)濟(jì)下行的影響,政府迅即出臺(tái)4萬億投資來刺激經(jīng)濟(jì)。這4萬億投資決策是如何制定的?其涉及重大的預(yù)算變動(dòng),有沒有經(jīng)過人大及其常委會(huì)的審議批準(zhǔn),有沒有違反預(yù)算法?人大及其常委會(huì)是否履行監(jiān)督的職責(zé),如沒有,該如何擔(dān)責(zé)?這些條款還涉及行政處分權(quán),如何依法給予處分?法律對(duì)此言語不詳。這種既是執(zhí)行主體,又是執(zhí)法主體,既當(dāng)運(yùn)動(dòng)員,又當(dāng)裁判員,集雙重身份于一身,屬于自我監(jiān)督或內(nèi)部監(jiān)督的規(guī)定,有違法律原則,在現(xiàn)實(shí)中也難以執(zhí)行。
預(yù)算法應(yīng)當(dāng)將所有的法律關(guān)系主體違反預(yù)算編制(包括虛報(bào)、虛列、隱瞞)、預(yù)算調(diào)整、預(yù)算執(zhí)行、預(yù)算監(jiān)督、決算編制、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種種行為一一羅列并統(tǒng)攝于法律責(zé)任條文中,按照違反情節(jié)的輕重,措置不同的法律責(zé)任,使每種違法行為,都能有法所依,讓所有的違法部門與人員,都逃不脫法律的制裁,體現(xiàn)法律的公平與公正。
預(yù)算法的核心在于預(yù)算的編制及執(zhí)行與監(jiān)督,不在于預(yù)算和決算的初審和批準(zhǔn)。如何編制、如何執(zhí)行以及違反與此相關(guān)的預(yù)算規(guī)范的追責(zé),應(yīng)是預(yù)算法內(nèi)容的重中之重。若偏離于此,則無論如何都不能稱之為一部完善的法律。所謂加強(qiáng)對(duì)預(yù)算的剛性約束,加強(qiáng)對(duì)預(yù)算的管理和監(jiān)督,所針對(duì)的對(duì)象就是預(yù)算編制和執(zhí)行的一系列行為及過程,這個(gè)行為過程必須符合預(yù)算法律規(guī)范的種種約束。而是否科學(xué)合理全面完整地設(shè)置了預(yù)算編制及執(zhí)行可用以進(jìn)行約束的法律行為規(guī)范,是預(yù)算法修訂是否成功的標(biāo)志,也是預(yù)算法修訂的難點(diǎn)之處。就此而言,新的預(yù)算法,仍有很大的改進(jìn)空間。■
(作者單位:財(cái)政部駐廣東專員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