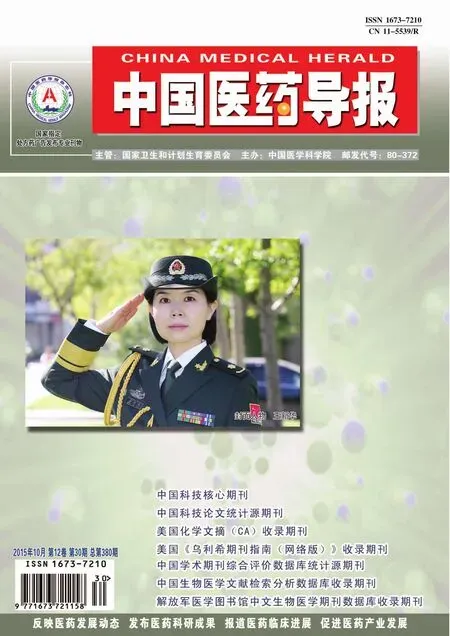人工全膝關節置換手術術后持續被動運動的干預效果
劉 琦
河南省遂平中醫院,河南遂平 463100
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及成熟運用,人工全膝關節置換手術(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已經成為臨床治療膝關節部位終末期疾病的關鍵療法,臨床上已廣泛使用[1]。 但因為TKA 術后可出現多種并發癥,影響患者術后康復, 需要采用康復運動進行干預,以協助患者降低并發癥發生率,并有效改善膝部關節的功能[2]。 本研究選擇遂平中醫院(以下簡稱“我院”)TKA 術后采用持續被動運動(continuous passive motion,CPM)手段治療的患者,對其康復的影響進行分析比較,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2 年1 月~2013 年1 月在我院接受TKA手術的患者34 例(41 膝),其中男13 例,女21例;年齡55~79 歲,平 均(64.7±8.1)歲;病 程4~19 年,平 均(5.2±2.1)年;疾病種類:骨性關節炎者27 例(29 膝),類風濕性關節炎者7 例(12 膝);行單膝關節置換者26 例,雙膝關節置換者8 例;術前患膝關節的活動度為55°~100°,平均(78.6±12.7)°;內翻畸形為0°~30°,平均(17.5±7.5)°。將患者分為觀察組(17 例,20 膝)和對照組(17 例,21 膝),其中觀察組男7 例,女10 例,平均年齡(65.6±8.4) 歲, 術前患膝關節活動度平均(77.8±12.0)°,骨性關節炎者13 例(14 膝),類風濕性關節炎者4 例(6 膝),行單膝關節置換者13 例,雙膝關節置換者4 例;對照組男6 例,女11 例,平均年齡(64.1±8.0) 歲, 術前患膝關節活動度平均 (78.9±12.8)°,骨性關節炎者14 例(15 膝),類風濕性關節炎者3 例(6 膝),行單膝關節置換者13 例,雙膝關節置換者4 例。 兩組年齡、性別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0.05),具有可比性。
納入標準:①為原發性膝關節疾病;②癥狀較重,采取保守療法3 年以上無明顯臨床改善;③X 線顯示關節病變嚴重,具備手術指證;④均為自愿加入本研究,簽署知情同意書;⑤肝腎功能無異常,無精神性疾病。排除標準:①繼發性膝關節疾病;②關節的二次翻修手術。
1.2 方法
對照組患者給予術后常規康復性訓練,包括股四頭肌的收縮功能鍛煉,膝關節屈伸能力訓練,術后15 d內禁止負重活動,術后1~2 個月內逐步進行負重鍛煉。觀察組在對照組的訓練基礎上給予圍術期以CPM 為核心的康復訓練,具體如下:
1.2.1 術前期的康復訓練方法 讓患者知曉術后康復訓練的常規程序,鍛煉加強患側股四頭肌以及腘繩肌的肌力,提高關節的活動度,可采取股四頭肌收縮訓練、關節抗阻力或不抗阻力情況下的主動屈伸鍛煉等[3]。
1.2.2 術后早期康復 術日至術后第2 天,可常規采取伸膝位制動,主要目的是降低疼痛及出血[4]。具體方法:①藥物干預:止疼、抗感染類,術后12 h 起給予低分子量肝素抗凝;②抬高患側肢體,并使用靜脈泵,同時進行髖、踝關節的主動或被動練習,屈伸動作30 次為1組,2~3 組/d;③術后3 d 內視引流情況拔除引流管。④進行股四頭肌的等長收縮;⑤術后給予下肢末端至腹股溝處的彈力繃帶包扎,連續使用5 d;⑥膝部手術部位給予冰袋冷敷。
1.2.3 術后中期康復 由術后第3 天至第2 周末,本階段訓練的主要目的是減少組織粘連,提高關節的活動度,其次是肌力的恢復性訓練[5-6]。具體方法:①運用被動關節活動器進行鍛煉, 活動范圍由伸直0°、 屈曲30°開始,逐漸增加,屈膝活動的初期運動范圍不超過40°~45°,以5°~10°/d 的速度逐漸增加屈膝活動度。關節活動的頻率早期2~3 次/min 開始,根據患者情況逐漸增加。 第1 周內屈膝可逐漸增加到60°,至第2 周可逐漸達到屈膝90°,期間出現疼痛、傷口愈合不良等征象,需暫停活動,待情況好轉后酌情繼續。 屈曲達90°后可不再進行持續被動運動治療。 進行持續被動活動期間,在治療時間之外,膝關節均應處于伸直位。②進行主動性膝關節活動度的訓練。③加強股四頭肌及腘繩肌肌力的鍛煉。④借助雙拐等輔具進行下地行走。 ⑤髖、踝關節等其他康復運動。
1.2.4 術后晚期康復 術后14 d 之后的康復活動目的是在保證關節活動度的情況下, 增強下肢肌肉的肌力,增強抗阻力的肌力鍛煉,同步進行日常功能的康復鍛煉,如靜態單車、上下樓梯等[7]。 夜間給予患者伸膝位固定,一般應堅持6~8 周鍛煉時間。
1.3 觀察及評價指標
①膝關節主動屈伸度(AROM):采用專業量角器對患者的患膝關節主動屈伸度進行測量,包括膝關節術后15 d、3 個月時的屈伸度及膝關節屈伸至90°的時間;②膝關節功能評價:采用西部安大略麥克馬斯特大學骨關節炎指數(WOMAC)評定量表在患者術后3 個月時進行膝關節功能評價,主要指標包括膝關節部位疼痛、膝關節僵硬及膝關節功能3 個方面,合計24 項,每項得分為0~4 分,分值越高表明患者膝關節整體狀況越差[8]。③對兩組平均拆線時間、住院時間及并發癥發生情況進行比較。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專業統計軟件SPSS 18.0 對所得數據進行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兩獨立樣本的計量資料采用t 檢驗。 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 以P <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術后15 d、3 個月AROM 情況比較
觀察組術后15 d 膝關節主動屈伸度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兩組術后3 個月膝關節主動屈伸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觀察組膝關節屈伸至90°的時間明顯短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 見表1。
表1 兩組術后15 d、3 個月膝關節主動屈伸度情況比較(s)

表1 兩組術后15 d、3 個月膝關節主動屈伸度情況比較(s)
組別 例數/膝數 膝關節屈伸至90°時間(d)膝關節主動屈伸度(°)術后15 d 術后3 個月觀察組對照組t 值P 值17/20 17/21 91.5±5.2 76.1±3.1 3.41<0.05 117.5±2.6 113.4±2.0 1.20>0.05 10.1±1.1 18.6±1.2 2.59<0.05
2.2 兩組術后3 個月WOMAC 膝關節功能評價比較
觀察組術后3 個月膝關節疼痛、 膝關節僵硬、膝關節功能、WOMAC 總分等項目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0.05)。 見表2。
表2 兩組術后3 個月西部安大略麥克馬斯特大學骨關節炎指數膝關節功能評價比較(分,s)

表2 兩組術后3 個月西部安大略麥克馬斯特大學骨關節炎指數膝關節功能評價比較(分,s)
組別 例數/膝數膝關節疼痛膝關節僵硬膝關節功能WOMAC總分觀察組對照組t 值P 值17/20 17/21 7.21±1.75 8.54±2.07 3.04<0.05 3.46±0.89 4.64±1.05 3.91<0.05 35.66±6.19 43.71±5.64 4.57<0.05 46.79±7.86 56.10±7.40 5.94<0.05
2.3 兩組平均拆線時間、 住院時間及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所有患者切口都為Ⅰ期甲級愈合, 均未發生感染、下肢深靜脈血栓及肺栓塞等并發癥。 兩組平均拆線時間、 住院時間比較,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P >0.05)。 見表3。
表3 兩組平均拆線時間、住院時間比較(d,s)

表3 兩組平均拆線時間、住院時間比較(d,s)
組別 例數/膝數 平均拆線時間 平均住院時間觀察組對照組t 值P 值17/20 17/21 17.5±2.4 18.6±2.1 1.19>0.05 15.1±1.6 15.2±1.5 1.04>0.05
3 討論
TKA 手術的效果決定于手術操作的技術及術后的及時進行康復訓練,后者主要包括肌力鍛煉及膝關節屈伸度的訓練。 TKA 術后CPM 治療只要為防止關節僵硬,提高關節屈伸活動的范圍[9-10]。 術后早期采用CPM 療法可以降低膝關節術后粘連的出現, 改善術后關節屈伸活動度;改善局部血液供應,消除組織水腫,有利于術后愈合。 CPM 同時可以加快下肢靜脈回流速度,有益于防止下肢靜脈血栓出現。 CPM 治療應在TKA 術后早期即可采用,因為TKA 術后早期手術部位容易出血、水腫,此時采用CPM 治療,能夠使關節部位組織隨CPM 的屈曲及伸展運動而被動地伸長及縮短,不斷將關節腔及周圍組織的積血、積液排出關節區,從而有效降低關節及周圍組織的腫脹,使關節運動的阻力降低,屈伸活動范圍加增加。 相關研究證實,CPM 療法可加速關節腔內及關節周邊組織積液的回吸收,防止關節部位周邊疏松組織的腫脹。 出血量的增加是CPM 療法使用過程中較為常見的并發癥[11-13]。 相關研究顯示,術后的早期采用CPM 療法不會增加出血的概率,因此,術后早期如果手術部位已停止出血,且組織水腫開始消退,是采用CPM 療法治療的恰當時機[14-16]。
在應用CPM 治療的過程中, 要密切關注切口愈合的問題。有研究顯示,采用CPM 進行屈膝訓練大于40°時,手術部位的氧供給顯著減少,這表明如果術后早期訓練時屈曲活動過度, 可致使傷口愈合出現障礙,故在屈膝鍛煉早期,活動不宜大于40°,屈膝活動度應逐步提高,若出現傷口愈合不良,則應停止使用CPM 治療[17-20]。 對于CPM 治療使用過程中出現局部刺激癥狀或有疼痛則需暫停治療,待癥狀好轉后方可酌情繼續。 另外,TKA 術后采用CPM 治療時,應給予彈力紗布進行包扎, 這樣一方面能使關節可以隨CPM 治療器械活動,又能降低對手術部位的壓力,對手術恢復有所幫助[21-23]。
TKA 術后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是臨床極為重視的并發癥之一。 TKA 術后下肢血流較為緩慢、血管壁損傷、血液處于高凝狀態是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的重要因素。 術后早期進行CPM 治療可改善下肢血流速度,結合彈力襪、主動訓練等療法以及術后低分子肝素的使用, 可明顯較少TKA 術后下肢深靜脈血栓的發生概率,而且具備較高的安全性[24-25]。
為提高TKA 手術效果,CPM 治療是臨床一種簡便、有效、經濟的康復治療方法。 只要臨床使用合理,CPM 治療在TKA 術后的臨床效果是明顯的, 可以改善關節屈伸活動范圍,降低下肢靜脈血栓的發生率及促進術后康復等。
[1] 姜儷凡,馮藝,安海燕,等.人工全膝關節置換術康復鍛煉期鎮痛方式對關節功能恢復的影響[J].中國疼痛醫學雜志,2014,20(2):90-94.
[2] 樊繼波,覃勇,唐曉松,等.老年性骨質疏松癥患者全膝關節置換術后康復評估與治療研究[J].中國骨質疏松雜志,2014,(10):1207-1211.
[3] Van der Merwe JM,Haddad FS,Duncan CP. Field testing the Unifi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periprosthetic fractures of the femur, tibia and patella in association with knee replacement: 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J]. Bone Joint J,2014,96(12):1669-1673.
[4] 李玉芳,周秀梅.持續被動運動干預對人工全膝置換術后患者康復的作用[J].中國醫藥指南,2012,10(17):471-472.
[5] 劉詠蕓.全膝關節置換術前康復訓練干預的效果分析[J].中國社區醫師,2014,(34):143-144.
[6] 段勇將,唐教波,王華祥,等.綜合運動訓練對全膝關節置換術功能及預后的影響[J].西南軍醫,2011,13(5):821-823.
[7] Cunic D,Lacombe S,Mohajer K,et al. Can the Blaylock Risk Assessment Screening Score (BRASS) predict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need for comprehensive discharge planning for patients following hip and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Predicting arthroplasty planning and stay using the BRASS [J]. Can J Surg,2014,57(6):391-397.
[8] 寧麗欣,徐燕,李東文,等.持續被動活動在全膝關節成形術后的應用進展[J].中國康復醫學雜志,2007,22(3):286-288.
[9] 張淑環,李春柳,吳曉萱,等.康復體操在全膝關節置換術患者康復中的應用研究[J].護理實踐與研究,2013,10(5):11-12.
[10] 劉陽,張衛國,于光耿,等.人工全膝置換術后持續運動干預效果分析[J].中國臨床康復,2006,10(8):25-27.
[11] 沈紅星,陳裔英,馬彬,等.早期綜合康復療法對全膝關節置換術后膝功能和ADL 能力的效果[J].中國康復醫學雜志,2010,25(6):577-579.
[12] Rodriguez-Merchan EC. Medial Unicompartmental Osteoarthritis(MUO)oftheKnee:UnicompartmentalKneeReplacement(UKR) or Total Knee Replacement(TKR) [J].Arch Bone Jt Surg,2014,2(3):137-140.
[13] 陳凱敏,于哲一,謝青,等.不同運動療法對全膝關節置換術后功能恢復的影響[J].中國康復醫學雜志,2010,25(1):50-52.
[14] Kim YH,Park JW.Comparison of highly cross-linked and conventional polyethylene in posterior cruciate-substituting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n the same patients [J]. J Bone Joint Surg Am,2014,96(21):1807-1813.
[15] 肖琳,孫小科,王軍虎.中西醫結合康復治療人工全膝關節表面置換術45 例臨床觀察[J].中醫藥導報,2014,20(9):60-62.
[16] 劉偉,吳宇黎,叢銳軍,等.全膝置換后早期持續主動功能鍛煉有利于關節功能的恢復[J].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2011,15(35):6509-6513.
[17] 趙斌,曾憲輝,豐新建,等.持續被動運動在全膝關節置換術后康復中的應用[J].中醫正骨,2014,26(9):19-20,24.
[18] 夏潤福,李劍鋒,閆金玉,等.全膝關節置換修復老年重度膝骨關節炎:療效及生活質量評估[J].中國組織工程研究,2014,18(40):6438-6443.
[19] 葉川,劉日光,湯晉,等.膝骨性關節炎雙側同期全膝關節置換和單側膝關節置換的比較[J].中國組織工程研究,2014,16(35):5583-5588.
[20] 姜義琴.全膝關節置換術后手術自行鍛煉與CPM 鍛煉對膝關節功能的影響[J].中國衛生標準管理,2015,6(8):153.
[21] 李玉芳,周秀梅.持續被動運動干預對人工全膝置換術后患者康復的作用[J].中國醫藥指南,2012,10(17):471-472.
[22] 段勇將,唐教波,王華祥,等.綜合運動訓練對全膝關節置換術功能及預后的影響[J].西南軍醫,2011,13(5):821-823.
[23] 李小六,趙曉鷗.人工全膝關節置換后持續被動關節運動:48 例分析[J].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2010,14(4):665-668.
[24] 陳凱敏,于哲一,謝青,等.不同運動療法對全膝關節置換術后功能恢復的影響[J].中國康復醫學雜志,2010,25(1):50-52.
[25] 崔建勝.膝關節置換后被動關節運動訓練療效評價[J].中國誤診學雜志,2011,11(15):3640-3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