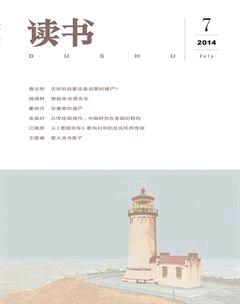湘江流絕唱
原湖南師范大學教授林增平,在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領域,思想深邃而致遠,人格高尚而含蓄,堪稱一代師表。時值先生九十冥誕,特以此小文追思。
初識林公,是在一九七八年冬。當時,中南地區(qū)辛亥革命史研究會在廣東省中山縣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宣告成立,我作為會務人員得以目睹國內(nèi)如姚薇元、章開沅、林增平等學者之風采。時際改革之風初拂,學術春天乍到,人文復蘇,大家都想開懷小酌幾杯,以慶祝一番。但學人工薪不高,會議經(jīng)費有限,不知是誰提議湊錢買酒—教授五元、副教授二元,得到與會者一致贊成。林公笑嘻嘻地第一個掏出錢來:“王杰(說的是不咸不淡的廣州話,而且僅會勉強講這兩個字),收銀。我?guī)ь^!”我生平第一次聽林公講“廣州話”,南腔北調(diào),廣東同人笑得前仰后翻。很快湊齊了二十幾元酒資,晚餐的氣氛自不待言。
事后始得知,林公好酒,最佳水平“是未見他醉過”(林公弟子鮮于浩教授語),飲酒有度也是出了名的。一次,有幸單獨與林公談酒,請教喝酒的學問有多大,林公不假思索地回答:“酒量大,學問就大!”隨即娓娓而談“酒經(jīng)”:與同人飲酒,有一種歸屬感,可以開懷暢飲,互通信息,獲取真知,積淀知交。與陌生人碰杯,乾坤大,學問深,得先行察言觀色,如考辨史料一般,審視其真?zhèn)危骑L正者大抵人品亦正,酒桌上多心計的,交往時要多留點神。偕知己者小酌,一定要講真心話,嚶鳴知音。同話不投機者把盞,有兩種方式可擇應對,或隨之哈哈呵呵,適可而止,或大塊吃肉,作壁上觀,切記酒量千萬別過度,以免酒后“吐真言”,出洋相。二人對飲,不是知己不相聚,當推心置腹。至于一人自斟自飲,那就是擁抱清靜、享受孤獨,借以馳騁思維,做無邊際的思考,求無意中的創(chuàng)獲。
這便是林公的酒道。老子曰:“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人能“七善”便是“道”。哲人認為,任何東西都有“道”,比如醫(yī)道、茶道、商道等等。任何人都處在三種維度中,除了時間、空間,還有一個就是“道”。“道”字由“首”字和走字底構成,在古文字庫,“首”就代表著一個人,走字底是一個十字路口。“道”者,乃人生抉擇之智慧。
思想從孤獨中來,把學問播及民間,惠澤大眾,需要功力。或許,林公的《中國近代史》,林公的資產(chǎn)階級研究,林公的湖湘文化研究,都是由此感悟得來?
林增平教授是江西萍鄉(xiāng)蘆溪鎮(zhèn)人,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于安源煤礦。他曾憶及其早歲啟蒙:“小學階段,我的學業(yè)成績一直是中下水平,僅免于留級而已。畢業(yè)后,考入江西頗有名氣的南昌心遠中學。盡管僥幸跨進了中學的門檻,但畢竟經(jīng)不起那嚴格的篩選,所以,念完一年級,就因為考試不及格的課程達到了留級的界線,于是當了‘降班生,重讀一年。” (林增平:《治史瑣言》,載《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九輯,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天資并不出眾的他,靠著勤奮刻苦,卓然成家。
一九五三年秋,中南區(qū)進行院系調(diào)整,林公調(diào)入湖南師院歷史系,承擔專科、本科中國近代史課程的教學,經(jīng)過“四次輪回”、“五易其稿”,一九五八年,洋洋六十萬言的講義,以《中國近代史》冠名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后來回憶:“為把講義修訂好,我一般地說得上是專心致志,埋頭苦干。除了三伏天,午睡這個程序是被我從日常生活里排斥出去了的;而且還經(jīng)常捐棄了文娛活動,開夜車是每日例行功課。……做學問,在年富力強的歲月,是應該下點苦功夫的。”林公夫妻兩地分居十幾年,多少憂愁牽掛被拋于一邊。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長沙,亦屬全國有名的“火爐”。坐冷板凳,過清貧生活,做硬功夫,養(yǎng)浩然正氣—個中甘苦,恐怕只有如林公他們那一輩人方能體味其真。到了一九七九年,該書竟重印了五萬部,一九八四年初第四次重印,又發(fā)行了三萬多部,同時被多所高校及社會科學院指定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必讀參考書。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像林公這樣的忠厚長者,居然也會遭到橫蠻的批判,受盡了身心的折磨:他在批判會上被打掉了門牙、祖墳被人刨挖,接著是毫無例外地在湘西花垣等地的“牛棚”勞動改造,直到一九七六年,《辛亥革命史》編寫組才硬從平江的農(nóng)田里把他要回長沙來。從“牛棚”出來,林公說:“過去了的事,就讓它永遠過去吧!唯一無法挽回的是,白白浪費了十個春秋!”以寬容豁達的心態(tài),投入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的撰寫和修改定稿。林公淡泊致遠,不爭名利,寬厚和善的人品,在這部作品最后順利完成的過程中得到最充分的體現(xiàn)。章(開沅)林配,堪稱史學界的佳話,其間推心置腹、精誠合作之互動,當令正氣之師感之系之,而足令雞腸氣量之輩省之思之!
一九八八年,全國史學界代表大會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與會者都在認真討論如何擺脫史學危機,走出史學低谷的有關問題,有位高人突發(fā)奇論,語驚四座:“有辦法,我們承擔整理了全省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歷史資料,賺了一筆錢,走出了低谷!”平素溫和的林公聽完,拂袖離座,用很高的嗓門對鄰座的楊慎之先生說:“混蛋!這叫什么走出低谷?庸俗低級!” (楊慎之:《林增平教授的人品和學品》,載《文史拾遺》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林公對時下傳媒、出版物和學界的粗制濫造、請人捉刀、剽竊抄襲、冒充“通才”的丑惡現(xiàn)象深惡痛絕,每每與同仁談及,都旗幟鮮明地表示,要像對待偽劣商品一樣,把偽劣作品和書刊抖摟出來曝光,儒不必坑,書可以焚,絕不能讓那些以權謀私、不學無術的文化掮客褻瀆了神圣的學術事業(yè)。
畢生以“教書匠”為職志的林公,在教育戰(zhàn)線上辛勤耕耘了四十五年,也無私奉獻了四十五載。他從來不以大家、長者、尊者自居,更不是夸夸其談、嘩眾取寵的侃爺。即便擢升為副院長乃至校長,仍堅持為本科生開課,并不斷吸收史學界的前沿信息,認真?zhèn)湔n,一方面向?qū)W生推介學術殿堂的前沿信息,灌輸學術研究的理念方法與技能,一方面又接受學子的思想碰撞,進一步完善自身的學術觀點。
名心重而巧偽生,利欲昏而神智冥,則其學必難以自立,亦無以諭之于人。人脈“處下”,這或許是老子哲學在林公身上的外爍。他總是虛心學習他人長處,不斷臻思想至升華。黃河、長江納百川,就是因為地勢低洼,高山上的流水都往那里匯合—“處下”恰恰是一種進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