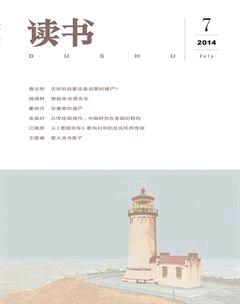把書讀對
熊秉元
西風東漸之后,把西方思想論著帶進華人社會,當然是很重要的使命。然而,誤讀誤解在所難免,先舉幾個明顯的例子。
首先,《Charles Dickens as a Legal Historian》這本書,譯者何帆把書名譯為《作為法律史學家的狄更斯》(上海三聯書店二零零九年版)。然而, 狄更斯早年輟學, 在社會底層掙扎多年,他是一位小說家、文豪,與學院相隔十萬八千里或更遠,而絕對不是一位“法律史學家”。比較正確的譯名當為《視狄更斯為法律史學家》―由法律史的角度, 闡釋狄更斯的作品(view Dickens as a legal historian)。
其次, 法學重鎮波斯納的力作《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朱蘇力教授譯為《道德和法律理論的疑問》(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然而,作者不是提出問題,而是指出道德哲學和法學理論的根本問題, 而且提出完整的分析。“Problematics”的意義和數學(mathematics)一樣,是指“問題的結構”。因此,根據書中的內容,較好的書名是《解構道德哲學和法學理論的根本問題》。再其次,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一段話:“peace, easy taxes, and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賀衛方教授引述為“有包容性的司法”。然而, 斯密的原意是指:“只要不打仗, 輕稅,和‘可堪忍受的司法,民眾就可以各得其所、自求多福。”可堪負荷(tolerable)的主體,是一般老百姓;有包容性(tolerant)的主體,是政府和公權力。因此,翻譯成“有包容性的司法”,前后意義不連貫,也扭曲了斯密的原意。
何帆、朱蘇力和賀衛方三位, 都是大眾所尊重的學者;對于知識普及化,他們都有重大的貢獻。然而,他們對原著的誤讀誤解,也是事實。何況,孰能無過。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斯蒂格勒(G. Stigler, 1911-1991)嘗言:“有人曾說, 學養可觀的人,也可能犯可觀的錯誤。馬歇爾不是例外。”(It has been said that highly educated persons can be highly mistaken. Marshall was no refutation.) 馬歇爾, 是奠定當代經濟學基礎的大家; 連經濟史上的大家都曾犯嚴重錯誤,我輩孰能無過?
而且,斯蒂格勒的言下之意,是最好先成為“學養可觀”的人,才有條件犯下“可觀的錯誤”。當然,不做事更不做“可觀”之事的人自然不會犯錯誤,更沒有資格犯“可觀的錯誤”。
與何、朱、賀三位不同, 梁治平的翻譯有“化平凡為神奇”之效,而且,影響更大。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這句話出自美國著名的法律學者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J. Berman,1918-2007)。出處是他一九七一年在波士頓大學的演講。這次演講后來輯為一本小書,一九七四年出版。中文版即梁譯之《法律與宗教》 (三聯書店一九九一年版)。
根據谷歌的搜尋,“法律必須被信仰……”這一項,有近九百五十萬條資料。而且,有篇文章表示,這是中國大陸法學界最著名的一句話。可是,伯爾曼真是這么說的嗎?根據原文,他的說法是“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 or it will not work”,中文譯文是“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兩相對照,頗有趣味。由字面上看,伯爾曼的意思只是:人們要相信法律,否則法律發揮不了作用。然而,在譯者的生花妙筆之下,中文譯本添加了不少額外的涵義。
就英文而言,伯爾曼的這句話其實很平常普通,毫不起眼;這句話的背景,要更為重要。當他發表演說時,正是美國社會處于極端動蕩的狀態。一方面深陷越戰,一方面有反戰、反社會、反體制的各種運動。大學校園里游行示威,嬉皮各地串聯,反文化大行其道。而且,不但宗教力量式微,法律這道防線也岌岌可危,瀕于崩解。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對法律秩序抱著嘲諷訕笑的態度。在這種背景之下,伯爾曼苦口婆心,希望挽救體制于既傾。因此,“人們要相信法律,否則法律發揮不了作用”,平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情境,也透露出伯爾曼心中的憂慮。他訴求的對象,不是主政者,而是一般社會大眾。
在另外一個層次上,對于法律和宗教,伯爾曼長期關注,也論著頗豐。他強調,在西方文明里,有很長一段時間,至少有幾個世紀之久,法律和宗教幾乎是合而為一。可是,十九世紀以降,宗教和法律似乎逐漸分道揚鑣;特別是美國開國以來,標榜政教分離,宗教的影響力迥異從前。伯爾曼像是法學界的傳教士,念茲在茲,希望能補綴和重砌法律與宗教之間的連結。
然而,中文譯本把法律和信仰放在一起,卻有可議之處。一九九一年中文本問世時,大陸剛剛改革開放不久,思想上幾乎是真空,對外來的知識求知若渴。不起眼的序文,經過中文的巧妙轉換,成了帶有哲學意味、又隱含想象空間的警句─“法律必須被信仰”。而這正是曲折所在:西方文明里,宗教和法律密不可分;在華人文化里,卻并沒有這種傳統。華人文化里法律和政治緊密結合,法律和宗教卻幾乎是各行其是的兩個體系。既沒有宗教的傳統,而希望“法律必須被信仰”,近乎緣木求魚。
因此,大陸法學界的共鳴,與其說是呼應伯爾曼,不如說是反映了某種普遍存在的“幽微意識”。文化大革命十年,“四人幫”呼風喚雨,紅衛兵打砸搶燒,社會法紀蕩然無存;改革開放讓社會重新起步,民眾希冀有基本的法治。而且,是合于公義的法治,能得到民眾的支持。“法律必須被信仰”想表達的,或許是“法律必須能被民眾所相信”,呼吁的對象,不是一般民眾,而是執政者。這種解讀,似乎更符合歷史經驗和社會現實。
伯爾曼已經作古,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大概也很難想象:他不經意的一句話,經過某種巧妙轉換,觸動了另一個古老文明里千百萬個心弦!
我曾當面向梁治平教授請益, 他也客氣地自謙: 譯文確實稍過原文!但是, 其中至少有兩點還是值得留意:首先,如果譯書時,梁教授化平凡為神奇不過是無心之過, 而其他學子卻是不加深思, 以致眾口鑠金。其次, 如果譯文真的反映了譯者和眾多法學界的學者及學子,對法律的認知或期望,問題可能就不是太簡單了。當然, 對法學如何有平實深入的認知, 是個大哉問, 有待來者。
順便多聊兩句。伯爾曼有過這樣一段話: 當小童說“她先打我”,這是《刑法》;當他說“你答應我的”,這是《契約法》;當他說“玩具是我的”,這是《財產法》;當他說“媽媽說我可以”,這就是《憲法》。 就文字來說, 要把這段話讀對, 應該很容易! 就內涵來說, 要把這段話讀對, 倒是要有可觀的學養。—他年過八十接受訪問時,自言從小就學法律,這些就是他舉的例子。
伯爾曼的說法,是半開玩笑的認真,是著作等身宿儒的智慧結晶,也是真佛只講家常話的典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