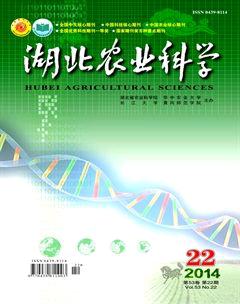湖北棉田雜草的種類、分布與群落特征
褚世海 李儒海 常向前
摘要:采用七級目測法調查了湖北省3個棉花(Gossypium Spp.)主產區的雜草種類、分布,并分析了雜草的群落特征。結果表明,湖北省棉花主產區有雜草86種隸屬32科,優勢雜草有10種,分別為千金子(Leptochloa chinensis)、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旱稗(Echinochloa hispidula)、鱧腸(Eclipta prostrata)、鐵莧菜(Acalypha australis)、香附子(Cyperus rotundus)、牛筋草(Eleusine indica)、碎米莎草(Cyperus iria)、馬齒莧(Portulaca oleracea)和水花生(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物種豐富度以江漢平原最高,襄陽-隨州地區最低。3個棉花主產區的雜草優勢種有一定差異,襄陽-隨州地區以旱稗+鱧腸+馬唐+碎米莎草為優勢種類;江漢平原以千金子+馬唐+鐵莧菜+旱稗為優勢種類;黃岡地區以千金子+馬唐+鱧腸+水花生為優勢種類。襄陽-隨州地區與江漢平原地區雜草群落最為相似,而襄陽-隨州地區與黃岡地區雜草群落相似性最低。
關鍵詞:棉田雜草;種類;分布;群落特征
中圖分類號:S45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4)22-5411-05
棉花(Gossypium spp.)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湖北省是中國主要的棉產區之一,2013年湖北省棉花種植面積47.29萬hm2,占全國種植面積的10.12%;產量53.15萬t,占全國總產量的8.55%[1,2]。然而,我國棉田雜草危害嚴重,常年造成損失達到14%~16%,嚴重影響了棉花的優質、高效生產[3]。湖北省地處我國中部,氣候溫和、雨量充沛,這也更有利于雜草的生長,容易帶來更大危害。因此,開展本地區棉田雜草群落的監測與防除等工作非常必要,而對棉田雜草的發生現狀做全面、準確的調查研究是進行其他研究的基礎。近年來,對棉花產區雜草做了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工作[4-8]。湖北省棉田雜草調查研究開展較早[9],但調查不夠翔實和全面,而且隨著種植制度、環境條件的變化,棉田雜草的發生規律也在逐漸改變。基于這一現狀,本研究對湖北省主要棉產區的棉田雜草種類、分布及危害現狀進行了調查研究,以利于更好地對棉田雜草進行有效的治理。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地概況
湖北省位于中國中部,長江中游,東經108°21′~116°07′、北緯29°01′~33°16′,地貌類型復雜。其中江漢平原及沿長江向東延伸的黃岡市大部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1 100~1 400 mm,≥10 ℃活動積溫為5 100~5 400 ℃,旱地、水田并重;鄂北的襄陽-隨州地區為湖北省降水較少地區,≥10℃活動積溫一般不足5 000 ℃,年平均降水量在900 mm以下,也是全省溫差最大的地區,具有南北過渡的特點,是湖北省旱地集中分布區[10]。
1.2 調查方法
2011年,在湖北省襄陽-隨州地區、江漢平原、黃岡地區3個棉花主產區,隨機選擇地理環境、種植制度基本一致,面積不少于667 m2的田塊為單位樣方(由10個單位樣方構成1個樣點),采用七級目測法[11,12],記錄每一樣方中所有雜草的種類及相應的優勢度級數。雜草種類以《中國雜草志》[13]為鑒定依據。另外對調查地點的地形地貌、土壤類型等予以記錄。
1.3 調查地點
調查地點分布在17個縣市的21個鄉鎮,共22個樣點,220個樣方。包括:①襄陽-隨州地區,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本區內調查的5個樣點分別為隨州(曾都區)、棗陽(十里鋪)、棗陽(七方鎮)、襄陽(雙溝鎮)、宜城(鄔家沖);②江漢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調查的11個樣點分別為鐘祥(柴胡)、沙洋(小江湖)、天門(多寶)、天門(黃潭)、仙桃(鄭家場)、仙桃(張溝)、潛江(周磯聯豐)、潛江(周磯荊橋)、公安(斗湖堤)、公安(新口)、監利(汪橋);③黃岡地區,位于湖北省東部,6個調查點分別為黃梅(濯港)、武穴(余川)、浠水(丁司垱)、團風(但店)、團風(方高坪)、新洲(汪集鎮)。
1.4 數據處理及分析方法
雜草的綜合草害指數、頻度、群落物種豐富度及群落相似性用下列公式計算[12,14-16]:綜合草害指數(CII)=Σ(級別值×該級別出現的樣方數)/(最高級別值×總樣方數);頻度(F)=該種雜草出現的樣方數×100%/總樣方數;群落物種豐富度(S)=群落中雜草的種類數;S?覫rensen指數(Cs)=2j/(a+b),式中,j為群落A與B所共有的物種數,a、b分別為群落A、B含有的全部物種數。
2 結果與分析
2.1 雜草種類及危害性分類
調查結果表明,湖北省棉花主產區棉田雜草共有86種,隸屬32科(表1)。其中禾本科和菊科種類最多,分別為13種;其次為莎草科6種;莧科5種;大戟科、玄參科和蓼科分別有4種;其余各科包含雜草種類都在3種或以下。
依據綜合草害指數,可將這些雜草分為4類:優勢雜草、局部優勢雜草、次要雜草及一般性雜草。其中,優勢雜草(CII≥3)有10種,按綜合草害指數從高到低依次為千金子(Leptochloa chinensis)、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旱稗(Echinochloa hispidula)、鱧腸(Eclipta prostrata)、鐵莧菜(Acalypha australis)、香附子(Cyperus rotundus)、牛筋草(Eleusine indica)、碎米莎草(Cyperus iria)、馬齒莧(Portulaca oleracea)、水花生(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這10種雜草在各棉區普遍發生,綜合草害指數及頻度都較高,對棉花生長發育和產量的影響顯著,防除較困難,為湖北省棉田的惡性雜草。
局部優勢雜草(2≤綜合草害指數<3)有7種,依次為反枝莧(Amaranthus retroflexus)、刺兒菜(Cephalanoplos segetum)、日照飄拂草(Fimbristylis miliacea)、通泉草(Mazus japonicus)、水竹葉(Murdannia triquetra)、火柴頭(Commelina bengalensis)、丁香蓼(Ludwigia prostrata)。這些雜草具有較高的綜合草害指數和頻度,但在各個棉產區差異較大,部分雜草在某些地區具有優勢,在另外的地區卻危害較輕,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制定防除對策。
次要雜草(0.8≤綜合草害指數<2)有8種,依次為打碗花(Calystegia hederacea)、地錦(Euphorbia humifusa)、異型莎草(Cyperus difformis)、粟米草(Mollugo stricta)、酢漿草(Oxalis corniculata)、青葙(Celosia argentea)、波斯婆婆納(Veronica persica)、爵床(Rostellularia procumbens)。整體來看,這些雜草危害相對較輕,個別雜草在某些地區有一定優勢。
其余61種為一般性雜草,這些雜草綜合草害指數及頻度都較低,某些雜草雖然分布較廣,但危害很小。
綜合草害指數高的雜草一般具有較高的頻度,二者呈明顯正相關。例如10種優勢雜草中,有8種頻度在50%以上,馬唐和鱧腸最高,頻度為88.51%,最低的碎米莎草,頻度也達到38.51%;而在一般性雜草中,絕大多數頻度在10%以下,最低的僅0.57%。這說明,分布廣泛的雜草通常更具有優勢,危害更大,應作為防控重點。
2.2 各棉區雜草發生特點及群落組成
各棉區雜草的物種豐富度有明顯差異。3個棉花主產區共調查到雜草86種,其中江漢平原種類最多,有62種,其次為黃岡地區54種,襄陽-隨州地區最少,有47種。在所有的86種雜草中,3地共有的雜草有28種。
調查的所有雜草中,綜合草害指數在1以上的雜草有22種。這22種主要雜草在各地區的綜合草害指數和頻度既有一致性,也有明顯差異(表2)。
3個棉花主產區的雜草優勢種有一定差異。按照前述標準,襄陽-隨州地區優勢種有13種,雜草群落以旱稗+鱧腸+馬唐+碎米莎草為主要優勢種;江漢平原優勢種有11種,雜草群落以千金子+馬唐+鐵莧菜+旱稗為主要優勢種;黃岡地區優勢種有10種,雜草群落以千金子+馬唐+鱧腸+水花生為主要優勢種。可見,3個棉區的雜草群落組成區別明顯,如江漢平原和黃岡地區前兩位的優勢種均為千金子和馬唐,而襄陽-隨州地區前兩位的優勢種為旱稗和鱧腸。這一結果與3個地區的耕作制度密相關,襄陽-隨州地區的棉田多為旱地,因此以旱生型雜草旱稗和鱧腸為主;而江漢平原和黃岡地區則多為水旱輪作,因此以喜濕性雜草千金子和馬唐為主。3個棉區10種優勢雜草中,襄陽地區有10種,江漢平原有9種,黃岡地區有8種。可見,各棉區的雜草優勢種多數重合,但又有本地特有的優勢種,如襄陽-隨州地區的火柴頭和粟米草、江漢平原的刺兒菜、黃岡地區的日照飄拂草和通泉草。
S?覫rensen指數可以體現各地區雜草群落的相似性。襄陽-隨州地區與江漢平原共有種37種,S?覫rensen指數0.679,江漢平原與黃岡地區共有種34種,S?覫rensen指數0.586,襄陽-隨州地區與黃岡地區共有種29種,S?覫rensen指數0.563。可見,襄陽-隨州地區與江漢平原地區雜草群落最為相似,其次為江漢平原地區與黃岡地區,相似性最低的為襄陽-隨州地區與黃岡地區。這一結果表明了地理位置的差異對雜草群落相似性的影響,距離越近,雜草群落相似性越高,反之越低。
3 小結與討論
本研究反映了湖北省棉花主產區雜草發生現狀,包括湖北省棉花主產區的雜草種類、各種雜草的分布與危害、各地雜草優勢種、3個棉區雜草群落的特點及區別等。86種棉田雜草中,優勢雜草有10種,局部優勢雜草有7種,這些雜草為湖北省棉花主產區的惡性雜草,應作為研究及治理工作的的重點。本調查研究采取普查方式,所查棉田大多采取過相應的化學防除措施,結果反映的是在目前普遍的防除水平下的草害狀況。
棉田雜草的種類及優勢種是在逐漸變化的。與20世紀90年代的結果[9]相比,湖北省棉田主要雜草的種類類似,但其優勢度排序已有較大變化,最明顯的就是千金子已成為本次調查最具優勢的雜草,但當年危害最重的雜草為馬唐。這與耕作制度的變化、雜草對除草劑的敏感程度密切相關。因此,應根據田間雜草發生的具體情況及時調整雜草管理措施。
雜草種群發生狀況及群落組成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環境條件,湖北省3個棉產區在自然地理環境及生態條件上就有較大差異。如襄陽-隨州棉區以崗地為主,且多為旱地,降雨相對偏少,因此雜草以旱生雜草為主;江漢平原為地勢低平的沖積平原,是湖北省土壤條件最好的農業區,土壤為油砂土,適合各種雜草生長,且雨量豐富,因此本區雜草種類豐富,各種旱生、濕生型雜草均廣泛分布;黃岡地區與江漢平原緯度相似,但本區內低山丘陵分布廣泛,砂泥土壤性質明顯,土壤質地粗松,有機質及全氮含量較低,細砂、小石較多,因此本地區與江漢平原地區的雜草有一定相似性,又有本地特有的優勢種。
影響雜草發生狀況的另一重要因素為耕作制度。有研究認為水旱輪作改變了土壤水分狀況,有利于喜濕性雜草如鱧腸、千金子等的發生,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稻田雜草如稗、異型莎草等的危害。水稻種植時灌水導致土壤中旱生性雜草的繁殖體腐爛,大大地降低了這些雜草的種群數量[7,17]。江漢平原及黃岡地區的千金子最具優勢,應與水旱輪作的耕作制度密切相關,兩地的部分旱生型雜草如馬齒莧、粟米草的綜合草害指數及頻度明顯低于襄陽-隨州地區,但并非所有旱生性雜草均表現出這一趨勢。
其他影響雜草發生狀況的因素還有很多,如施肥影響雜草種子庫[18],不同除草劑的使用影響雜草種群演替[19]。隨著將來抗除草劑轉基因棉的推廣,棉田雜草群落還會有新的變化。總之,在明確棉田雜草的發生危害特點及群落結構的基礎上,應當結合耕作方式、水肥管理方式及除草劑使用的變化,采取有針對性的雜草管理措施,從而實現棉田雜草的可持續治理。
參考文獻:
[1] 湖北省統計局,國家統計局湖北調查總隊.湖北省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3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3] 馬小艷,馬 艷,彭 軍,等.我國棉田雜草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J].棉花學報2010,22(4):372-380.
[4] 馮宏祖,王 蘭.新疆南部棉區棉田雜草調查[J].安徽農業科學,2008,36(7):2819-2820,2986.
[5] 劉生榮.關中棉區棉田雜草分布及化學除草技術[J].陜西農業科學,2004(5):96-97.
[6] 王榮龍,劉定忠,陶碧慶,等.贛北棉區棉田雜草調查初報[J].江西棉花,2000,22(1):23-25.
[7] 強 勝,魏守輝,胡金良.江蘇省主棉區棉田雜草草害發生規律研究[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00,23(2):18-22.
[8] 張澤溥.我國棉田雜草種類、分布及防除[J].雜草科學,1994(3):7-9.
[9] 朱文達,胡祥恩,錢益新,等.湖北省棉田惡性雜草的調查及綜合治理[J].湖北農業科學,1996(6):40-46.
[10] 《湖北農業地理》編寫組.湖北農業地理[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11] 強 勝,李揚漢.安徽沿江圩丘農區水稻田雜草群落的研究[J]. 雜草學報,1989,3(3):18-25.
[12] 強 勝,雜草學[M]. 第二版.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9. 261-262.
[13] 李揚漢.中國雜草志[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
[14] 馬克平,劉燦然,劉玉明.生物群落多樣性的測度方法Ⅱ β多樣性的測度方法.生物多樣性,1995,3(1):38-43.
[15] 魏守輝,張朝賢,翟國英,等.河北省玉米田雜草組成及群落特征[J].植物保護學報,2006,33(2):212-218.
[16] 強 勝,李揚漢.安徽沿江圩丘農區水稻田雜草群落的研究[J]. 雜草學報,1989,3(3):18-25.
[17] 強 勝,沈俊明,張成群,等.種植制度對江蘇省棉田雜草群落影響的研究[J].植物生態學報,2003,27(2):278-282.
[18] 馮 偉,潘根興,強 勝,等.長期不同施肥方式對稻油輪作田土壤雜草種子庫多樣性的影響[J].生物多樣性,2006,14(6):461-469.
[19] 吳競侖,李永豐,王一專,等.不同除草劑對稻田雜草群落演替的影響[J].植物保護學報,2006,33(2):202-205.
(責任編輯 屠 晶)
其他影響雜草發生狀況的因素還有很多,如施肥影響雜草種子庫[18],不同除草劑的使用影響雜草種群演替[19]。隨著將來抗除草劑轉基因棉的推廣,棉田雜草群落還會有新的變化。總之,在明確棉田雜草的發生危害特點及群落結構的基礎上,應當結合耕作方式、水肥管理方式及除草劑使用的變化,采取有針對性的雜草管理措施,從而實現棉田雜草的可持續治理。
參考文獻:
[1] 湖北省統計局,國家統計局湖北調查總隊.湖北省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3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3] 馬小艷,馬 艷,彭 軍,等.我國棉田雜草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J].棉花學報2010,22(4):372-380.
[4] 馮宏祖,王 蘭.新疆南部棉區棉田雜草調查[J].安徽農業科學,2008,36(7):2819-2820,2986.
[5] 劉生榮.關中棉區棉田雜草分布及化學除草技術[J].陜西農業科學,2004(5):96-97.
[6] 王榮龍,劉定忠,陶碧慶,等.贛北棉區棉田雜草調查初報[J].江西棉花,2000,22(1):23-25.
[7] 強 勝,魏守輝,胡金良.江蘇省主棉區棉田雜草草害發生規律研究[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00,23(2):18-22.
[8] 張澤溥.我國棉田雜草種類、分布及防除[J].雜草科學,1994(3):7-9.
[9] 朱文達,胡祥恩,錢益新,等.湖北省棉田惡性雜草的調查及綜合治理[J].湖北農業科學,1996(6):40-46.
[10] 《湖北農業地理》編寫組.湖北農業地理[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11] 強 勝,李揚漢.安徽沿江圩丘農區水稻田雜草群落的研究[J]. 雜草學報,1989,3(3):18-25.
[12] 強 勝,雜草學[M]. 第二版.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9. 261-262.
[13] 李揚漢.中國雜草志[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
[14] 馬克平,劉燦然,劉玉明.生物群落多樣性的測度方法Ⅱ β多樣性的測度方法.生物多樣性,1995,3(1):38-43.
[15] 魏守輝,張朝賢,翟國英,等.河北省玉米田雜草組成及群落特征[J].植物保護學報,2006,33(2):212-218.
[16] 強 勝,李揚漢.安徽沿江圩丘農區水稻田雜草群落的研究[J]. 雜草學報,1989,3(3):18-25.
[17] 強 勝,沈俊明,張成群,等.種植制度對江蘇省棉田雜草群落影響的研究[J].植物生態學報,2003,27(2):278-282.
[18] 馮 偉,潘根興,強 勝,等.長期不同施肥方式對稻油輪作田土壤雜草種子庫多樣性的影響[J].生物多樣性,2006,14(6):461-469.
[19] 吳競侖,李永豐,王一專,等.不同除草劑對稻田雜草群落演替的影響[J].植物保護學報,2006,33(2):202-205.
(責任編輯 屠 晶)
其他影響雜草發生狀況的因素還有很多,如施肥影響雜草種子庫[18],不同除草劑的使用影響雜草種群演替[19]。隨著將來抗除草劑轉基因棉的推廣,棉田雜草群落還會有新的變化。總之,在明確棉田雜草的發生危害特點及群落結構的基礎上,應當結合耕作方式、水肥管理方式及除草劑使用的變化,采取有針對性的雜草管理措施,從而實現棉田雜草的可持續治理。
參考文獻:
[1] 湖北省統計局,國家統計局湖北調查總隊.湖北省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3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3] 馬小艷,馬 艷,彭 軍,等.我國棉田雜草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J].棉花學報2010,22(4):372-380.
[4] 馮宏祖,王 蘭.新疆南部棉區棉田雜草調查[J].安徽農業科學,2008,36(7):2819-2820,2986.
[5] 劉生榮.關中棉區棉田雜草分布及化學除草技術[J].陜西農業科學,2004(5):96-97.
[6] 王榮龍,劉定忠,陶碧慶,等.贛北棉區棉田雜草調查初報[J].江西棉花,2000,22(1):23-25.
[7] 強 勝,魏守輝,胡金良.江蘇省主棉區棉田雜草草害發生規律研究[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00,23(2):18-22.
[8] 張澤溥.我國棉田雜草種類、分布及防除[J].雜草科學,1994(3):7-9.
[9] 朱文達,胡祥恩,錢益新,等.湖北省棉田惡性雜草的調查及綜合治理[J].湖北農業科學,1996(6):40-46.
[10] 《湖北農業地理》編寫組.湖北農業地理[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11] 強 勝,李揚漢.安徽沿江圩丘農區水稻田雜草群落的研究[J]. 雜草學報,1989,3(3):18-25.
[12] 強 勝,雜草學[M]. 第二版.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9. 261-262.
[13] 李揚漢.中國雜草志[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
[14] 馬克平,劉燦然,劉玉明.生物群落多樣性的測度方法Ⅱ β多樣性的測度方法.生物多樣性,1995,3(1):38-43.
[15] 魏守輝,張朝賢,翟國英,等.河北省玉米田雜草組成及群落特征[J].植物保護學報,2006,33(2):212-218.
[16] 強 勝,李揚漢.安徽沿江圩丘農區水稻田雜草群落的研究[J]. 雜草學報,1989,3(3):18-25.
[17] 強 勝,沈俊明,張成群,等.種植制度對江蘇省棉田雜草群落影響的研究[J].植物生態學報,2003,27(2):278-282.
[18] 馮 偉,潘根興,強 勝,等.長期不同施肥方式對稻油輪作田土壤雜草種子庫多樣性的影響[J].生物多樣性,2006,14(6):461-469.
[19] 吳競侖,李永豐,王一專,等.不同除草劑對稻田雜草群落演替的影響[J].植物保護學報,2006,33(2):202-205.
(責任編輯 屠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