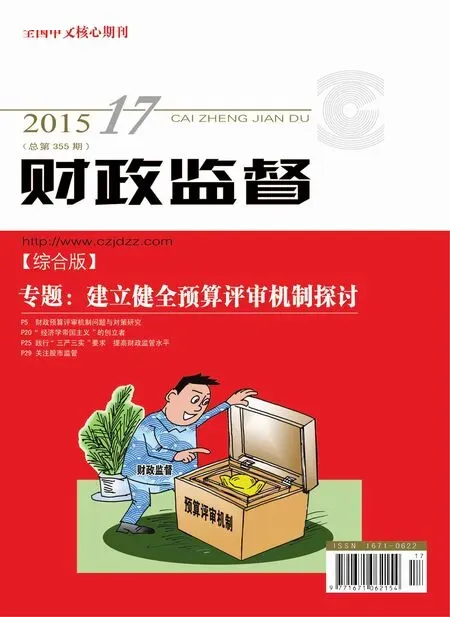“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創立者
——記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
●本刊編輯部
“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創立者
——記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
●本刊編輯部


1992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將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以表彰他在人類行為分析方面所做出的四大貢獻——人力資本投資的分析、家庭行為分析、犯罪與懲罰的經濟學分析、對勞動力和商品市場上的歧視行為的經濟學分析。這是諾獎史上罕見的以四個領域的成就摘此桂冠者,加里·貝克爾也因其將經濟理論擴展到以前僅屬于其他社會科學如社會學、人口學和犯罪研究的人類行為研究而被稱為諾獎得主中最具創新意識的經濟學家之一;其對經濟學研究疆界的擴展也讓他成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創立者而聞名于世。
加里·貝克爾,1930年生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1951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學位,1953年獲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55年在其25歲時獲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57年至1968年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1969年至2014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學。他是1967年美國經濟協會頒發的克拉克獎章獲得者、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2000年美國國家科學獎章獲得者,同時也是2007年美國總統自由勛章的獲得者,被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什稱為“過去百年來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2014年5月4日,貝克爾在芝加哥大學醫院因手術并發癥辭世,享年83歲。這位“理論創新者”、多產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因善于把經濟理論運用于對人類行為的研究以及過去同市場力量沒有聯系的領域開拓了經濟分析的新視野而在孕育他的芝加哥學派中獨樹一幟,也以其 《生育率的經濟分析》、《人力資本》、《家庭論》等具有深遠影響的代表作而被人永久銘記。
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教授拉爾斯·漢森評價貝克爾時說道:“貝克爾是杰出的知識領袖,他創造性的研究非常重要。在很多年里,他一直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對芝加哥大學和芝加哥經濟學派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的。”


然而這位為赫赫有名的芝加哥學派作出卓越貢獻的經濟學家最初對經濟學并不感興趣。生于1930年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煤礦小鎮波茨維爾的貝克爾,父母皆為只接受過初、中等教育的移民,家中書籍也寥寥無幾。在初高中時代他都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到16歲時相對智力活動他對運動更感興趣。父親對政治金融新聞的關注讓年幼的貝克爾對經濟學有了初步認識,但他坦誠“更多的感到的是枯燥”,而家庭中經常開展的政治和公平問題的討論啟發了貝克爾后來對社會學的關注。在普林斯頓大學期間的貝克爾對數學學習投入了大量精力,也為他進行經濟學研究的數理應用做好了充分準備,然而大三時的他依然失去了對經濟學的興趣,認為這門學科“看起來不能解決那些重要的社會問題”。幸運的是,在接下來的研究生學習時,他選擇了芝加哥大學,當1951年第一次聽到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微觀經濟學課程時,讓他重新對經濟學感到興奮。“他(弗里德曼)強調經濟理論并非聰明的學者們玩的游戲,而是分析現實世界的一個強大工具。他的課里同時充滿了對經濟學理論框架及其在實際意義重大問題上的應用的洞察”,貝克爾對初到芝加哥大學的印象以及弗里德曼課程的影響如是回憶道。此后,他與弗里德曼亦師亦友,結下了終生友誼,這對貝克爾的研究方向有著巨大影響。1955年,年僅25歲的貝克爾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他的博士論文基礎上撰寫的《歧視經濟學》在當時是一部具有首創性意義的重要經濟論著,但由于他的論題(對歧視的經濟分析)和研究方法(試圖計量“非貨幣”因素對市場運轉的影響)在當時的經濟學研究中太出格了,以至于過了兩年于1957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才出版該書,也正是從這部著作開始,貝克爾走上了將經濟學應用于社會問題的道路。
此后的12年間,貝克爾都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直至1969年,他又重返芝加哥大學,且迅速躋身現代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行列。他的學術思想與芝加哥學派創始人弗蘭克·奈特一脈相承,且與同時代的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劉易斯、舒爾茨、斯蒂格勒等有許多共同之處,都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成為芝加哥學派的重要一員。
貝克爾不僅濃縮了 “芝加哥傳統”、承繼了芝加哥學派理論精髓,與同行相比,他更是開拓了新的應用范圍——在運用經濟理論分析人類行為方面,貝克爾是一個成功的先驅者。這終將讓他為芝加哥學派做出獨一無二的貢獻。





“先不要管是不是經濟學問題”
為經濟學研究開疆拓土、運用經濟學方法工具分析研究人類行為是貝克爾一生著力的研究方向也是他最負盛名的學術成就所在。他的好友、同事斯蒂格勒在其回憶錄中專辟一章用“經濟學帝國主義”來贊揚貝克爾,在斯蒂格勒看來,正如醫學不能回答所有和疾病相關的問題一樣,經濟學家也不能解答所有的經濟問題,但是經濟學家對很多問題的解釋是富有競爭力的。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僅局限在金錢、人力和土地方面,其自身邏輯必然要求將經濟分析應用到更廣泛的社會現象中去。貝克爾基于理性人假設來研究所有和人的選擇有關的社會行為,包括歧視、犯罪、吸毒、教育、婚姻等,看上去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對政治學、社會學和公共政策領域的“侵入”,實際上也為這些重要社會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更為有效力的研究視角和方法。
我國著名經濟學者薛兆豐教授曾如是評論:“亞當·斯密時代的經濟學家都是廣博的,但后來專業的細化使經濟學家越來越只專注于與金錢相關的宏觀問題。而貝克爾卻替后人照亮了一片以人為本的微觀研究領域,使經濟學研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
更有學者斬釘截鐵地評價貝克爾,認為他很好地秉承了馬歇爾的傳統,即:“如果一個問題重要,就不要先管它是不是經濟學問題。”
1960年貝克爾寫就了當代西方人口經濟學的開山之作《生育率的經濟分析》;1964年初版、1975年再版了人力資本理論的經典《人力資本》一書,研究了一個人的教育和培訓投資如何獲得回報,并提出廣泛使用的一般人力資本和其他特定人力資本的概念,由此將人力資本這一重要的研究視角引入發展經濟學,他的這部《人力資本》著作也因此成為席卷當時經濟學界的“經濟思想上的人力投資革命”的起點;1981年完成的《家庭論》再次將貝克爾推向學術生涯的高峰,書中成功地將經濟學模型用到了家庭和婚姻行為,創造并普及了婚姻市場這一術語,系統討論了家庭內的資源配置問題,成為貝克爾有關家庭問題的劃時代之作以及微觀人口經濟學的代表作。這三本著作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經典性”論著,具有深遠影響。此外,貝克爾對犯罪和懲罰的研究啟示了法與經濟學的興盛;他的時間經濟學和新消費論也被西方經濟學者稱為“貝克爾革命”。


貝克爾作為經濟分析拓展到非市場領域的領軍人物:一方面對經濟學者研究工作開闊了新視野,同時也在激活其他領域學者的研究思維。這位對現實問題總是有著深刻剖析的學者曾有機會到美國政府出任內閣部長,但他卻選擇始終留在大學觀察社會、思考問題、筆耕不輟、著作等身,以他自己的方式對這個社會發揮著影響力。
除了專業著作之外,貝克爾還是面向公眾長期堅持寫專欄的經濟學家。從1997年至2004年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里為《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寫專欄,并出版選集《生活中的經濟學》、《反常識經濟學》,完成了秉持學術研究的同時又面向公眾寫作的理想,此后又一直與法律學者理查德·波斯納合寫博客,直到他去世前幾周。
貝克爾始終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在其八十歲高齡時依然在教大課做研究,其思維的敏捷、言辭的犀利和幽默始終呈現出一個頂級大師的巔峰狀態。《商業周刊》總編斯蒂芬·謝帕德認為貝克爾是我們時代最有原創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那富于思想性的聲音在一個到處都是喧囂的、充滿黨派之見的理論家的時代顯得很特別;他永遠是一個紳士,但也是一個站在不同于流俗的位置、敢于面對來自各個方向批評的紳士。”
他也始終秉持著堅定的學術信念,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回憶起近年來貝克爾在一次采訪中表達的看法:在他看來相比弗里德曼開始其學術生涯時,現在已沒有人認為國家主導是助推經濟增長最有效的方式——無論是在中國、巴西還是東歐,這是巨大的“思想上的勝利”。
“這能否影響政策?會的!”貝克爾說道,“每當我想到我的兒孫輩:是的,他們必須為此抗爭,自由不會沒有代價;但這不是一個看不到希望的抗爭……我基本上仍是個樂天派。”
貝克爾與中國

2005年6月2日,北大匯豐經濟論壇邀請貝克爾在北京大學演講
2005年貝克爾來訪中國,他在北京大學匯豐經濟論壇的演講中重申了他在1960年代做出的貢獻——將人置于經濟學研究的中心。這位老者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堅持著半個世紀前自己的學術理念,他向中國的學者和學子講道:“我們談論經濟時會想到機器和有形資本,看到經濟是由政府管理的,我們也可以從人力資本的角度來看問題。人力資本以人為主,所以一個經濟是否成功,要看它能否把個體所擁有的技能充分發揮出來,能否把人放在經濟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本帶來的最大的革命性突破就在這里。”
“將人置于經濟學研究的中心”是貝克爾學術思想的重要濃縮,這位經濟學人力資本理論的奠基人,用經濟學模型來研究教育、婚姻、生育等社會學課題的鼻祖,對中國的發展變化充滿興趣,曾在多個場合提起自己在讀中國歷史,并曾于1994年預言中國將成為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
但他更為關心關注的是中國的人口政策,2012年7月在他和波斯納的共同博客上發表了《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是時候結束了》,這是世界頂尖經濟學家首次撰文評價中國的人口政策,貝克爾表示 “中國一直是一個令人驚奇的國家,人口政策的改革是個頭等的經濟政策”;與此同時,他從2010年起為《財新新世紀周刊》撰寫專欄至2014年整50篇,其中三度就獨生子女政策撰文,認為中國實施市場化改革后獨生子女政策的弊端遠多于貢獻,呼吁中國盡早結束該政策。攜程網創始人、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人口政策研究者梁建章稱“貝克爾是中國人口改革的推動者”,貝克爾甚至曾計劃2014年夏天以83歲的高齡來中國參加關于中國人口政策的研討會,可惜他的離世讓他來中國參會的計劃再難成行。


布斯商學院在悼念信中寫道:“貝克爾在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做出歷史性變革,將經濟學原理用于闡釋廣泛的人類日常生活,在多個領域啟發了新的學術問題。”不僅如此,這位老者也身體力行為他國的經濟政策建言,啟發了更多的中國學人。
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曾于1982年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學位,當時貝克爾是他的授業教師之一。在林毅夫記憶中,貝克爾的高級微觀經濟學是每位博士生必修,也是最受學生歡迎、最具挑戰性和啟迪性的課程。“他沒有任何架子,總以開放的心態和學生進行平等的交流,他對真實世界的現象充滿好奇,又深具透徹的觀察和解析力”,林毅夫如是評價老師貝克爾,如何觀察現象、找準分析問題的切入點并把經濟直覺以嚴格的經濟邏輯表述出來的能力則是林毅夫在貝克爾課堂上更直接的獲益,影響其終生……
貝克爾深愛著經濟學這門被他改變的學科,每逢周末的下午,他常常出現在辦公室,或寫作,或回答比他小60歲的年輕學者提出的問題。他的學生以及同事都表示,聽貝克爾的課或者與貝克爾交流,最可能的結果不是掌握一種特定的正式技能,而是學到這位杰出經濟學家對于世界的看法。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齊默爾在悼念貝克爾的文章中這樣評價“加里是對整個世界產生重要影響的變革性的思想家,是一個非凡的人。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者之一,他將被永遠銘記”。

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的“世界經濟與中國發展”世界著名經濟學者研討會上發言
貝克爾曾對朋友說:“我的整體人生哲學一直是,在服飾這類問題上墨守成規,但在思想方面,我就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韙了:如果我認為自己是對的,受到批評我也不怕。”這也許就是加里·貝克爾為經濟學開疆拓土的原因所在,正是因為他在學術研究上敢于突破條框勇于創新、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韙”,終究創立了不可一世的“經濟學帝國”。■
(本欄目責任編輯:阮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