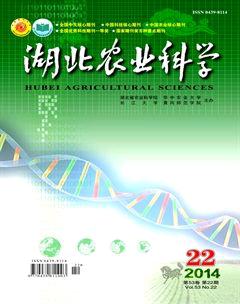基于供養人口探討中國農業勞動生產力
張燕 高翔 張洪
摘要:農業的基本功能是養活人,故度量農業勞動生產力的標準之一是1個農業勞動力能夠供養的人數。據此探討的結果是,按每人每日2 600kcal能量標準,有數十年時間,中國農業或無法供養全體國民或僅能勉強供養而無富余,至近10多年才有能力按8﹕2能量搭配的要求滿足國民的能量需要且有富余。在1952、1961、1969、1987、1991、2011年,1個中國農業勞動力分別可供養2.9、2.1、2.4、4.0、3.4、6.5個人。以能量搭配標準衡量,1997年前,受制于動物性農產品,1個農業勞動人口1975年以前只能供養不足0.5個人,1997年可供養4.0個人;1998年起,由植物性農產品決定,1個農業勞動人口1998、2011年可供養4.1、6.0個人;而幾個發達國家2006年1個農業勞動力平均至少供養72人,要縮小與之的差距,中國需付出很大努力。但只要能在2011年的基礎上,保持農業勞動生產力年均1.6%的增長率,就能實現至2020年60%城鎮化率的目標。
關鍵詞:勞動生產力;農業;供養人口;能量搭配
中圖分類號:F326.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4)22-5607-07
對農業勞動生產力已有長期的大量研究,并報道了大量研究成果[1-6],研究方法有用生產函數探討農業生產中各投入要素或全要素的技術進步、技術效率、規模效率的[1-4],或用灰色關聯方法分析農業產出與各投入要素間的關系的[5,6];很多學者還從生產與消費的角度分析了中國糧食生產與糧食需求[7-14],基于不同空間與時間尺度關注糧食安全問題[15-17]。然而,從農業供養能力角度探討農業勞動生產力的研究卻鮮見報道。
作為一個產業,農業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它具有“養活人”的基本功能,因此,有必要用供養能力來衡量農業勞動生產力的水平高低,這樣才能對農業的基本功能及其變化有相對正確的把握。本研究的探討即從此角度展開,即從能量角度探討中國農業供養能力的變化,希望可以較準確地度量中國農業生產的效果,并以供養能力為依據,提出提高中國農業勞動生產力的措施建議。
1 材料與方法
農業是養活人的產業,其提供的產品多數直接供食用,故衡量農業生產的效果時,標準之一是看其能供養的人口數,即在一定時期生產的植物性和動物性產品提供的能量能夠滿足多少人的需要,與當時的實際人口比較,是否有富余,因此,“養活”與否不應單純考慮糧食,而要關注農業綜合產出。農業勞動生產力也應如此度量。
1.1 建立模型
1)本研究用單位農業勞動人口可供養的人口數量來衡量農業勞動生產力E(t):
E(t)=P(t)/L(t) (1)
式中,P(t)為可供養人口數;L(t)為實際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
2)可供養人口數P(t)定義為:按一定標準,各種農產品提供的總熱量能滿足的人口數。本研究就用P(t)度量農業的供養能力。
P(t)=H(t)/AH (2)
式中,H(t)為各種農產品提供的總熱量;AH為在一定生活水平下,一定時間內人均需攝入的熱量,根據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01~2010年)提出的2010年食物與營養發展總體目標(小康標準),AH為人均每天獲得能量2 600kcal[18](即人均每年獲能949 000kcal)。
動物性能量的品質優于植物性能量,前者占比增加,表示農業供養能力的結構優化。如果用P1(t)、P2(t)分別表示植物性、動物性農產品能夠供養的人口數,則有
P1(t)=H1(t)/AH1 (2a)
P2(t)=H2(t)/AH2 (2b)
式中,H1(t)、H2(t)分別為植物性農產品和動物性農產品提供的熱量;按植物性農產品和動物性農產品提供能量8∶2的比例[18]及小康標準,每人每年從植物性農產品和動物性農產品獲得的能量平均應分別為AH1=AH植物=759 200kcal,AH2=AH動物=189 800 kcal。
只要P1≠P2,并以Pa表示實際人口數,則有如下含義的關系:
Pa>P1,P2,表示按一定標準,植物性、動物性農產品均不能滿足當時人口的需要,只能降低生活水平;
P1 P2 Pa 3)各種農產品都包含有人體生理需要的能量,但含量的多少不同。從量上看,各種農產品提供的能量之間具有互補性,可以相互替代,因此,農產品提供的總能量就是各種具體產品提供能量之和: H(t)=H1(t)+H2(t)= [a1M糧食(t)+a2M油料(t)+a3M糖料(t)+a4M蔬菜(t)+a5M水果(t)]+[a6M肉類(t)+a7M蛋(t)+a8M奶(t)+a9M水產(t)] (3) H1(t)=a1M糧食(t)+a2M油料(t)+a3M糖料(t)+a4M蔬菜(t)+a5M水果(t) (3a) H2(t)=a6M肉類(t)+a7M蛋(t)+a8M奶(t)+a9M水產(t) (3b) 式中,M糧食、M油料、M糖料、M蔬菜、M水果、M肉類、M蛋、M奶、M水產分別為糧食、油料、糖料、蔬菜、水果、肉類、蛋、奶、水產產品的物質量,其中前5種是植物性農產品,后4種是動物性農產品;a1、a2、a3、a4、a5、a6、a7、a8、a9分別為糧食、油料、糖料、蔬菜、水果、肉類、蛋、奶、水產單位產品包含的能量,ai(i=1、2、…、9)取值參照文獻[19]。
4)糧食產品作為食物直接使用的物質量M糧食并不簡單等于糧食產出量MC,因為糧食不僅可直接作為食物使用,還可間接使用于農業,包括飼料用糧MF和種子用糧MS,另外,還有糧食損耗MW,所以,作為食物直接使用的糧食M糧食需從糧食產出量中扣除間接使用與糧食損耗:
M糧食(t)=MC(t)-MF(t)-MS(t)-MW(t)=MC(t)-■Bi×Mi(t)-■Ci×Si(t)-D×MC(t) (4)
不同畜禽與水產養殖消耗的飼料量不同,根據畜禽產品、水產品的飼料報酬率計算飼料用糧MF:
MF(t)=■Bi×Mi(t)(4a)
式中,Mi分別為M肉類、M蛋、M奶、M水產;Bi則是一單位相應畜禽養殖產品的耗糧系數,肉類、蛋、奶、水產品耗糧系數取國家統計局歷年成本收益數據的平均數,分別為2∶1、1.7∶1、0.39∶1和1.02∶1[14]。
MS(t)=■Ci×Si(t)(4b)
種子用糧MS取決于主要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Si,根據歷年《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確定主要糧食作物水稻、小麥、玉米單位播種面積的種子用量Ci分別為52.5、235.5、45.0 kg/hm2[14]。
中國糧食產后損失約為9%~16%[20],參照文獻[20],本研究糧食損耗MW按糧食產量的12%計,即
MW(t)=D×MC(t),(4c)
其中D=0.12
1.2 數據主要來源
本研究中數據主要來源于《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21]、《新中國農業60年統計資料》[22]、《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9-2012)[23]等,從中獲取1949-2011年中國總人口、各種農產品產量;并參照了《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01-2010年)提出的營養目標[18]及主要農產品所含能量[19]。國外人口及農業數據獲自《國際統計年鑒》[24]。
2 結果與討論
2.1 中國人口與農業發展概況
由圖1可見,建國60年來,中國總人口除1960年與1961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均在增長,1951~1960、1961~1970、1971~1980、1981~1990、1991~2000、2001~2010年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99%、2.54%、1.89%、1.58%、1.09%、0.58%。可見,執行計劃生育國策近40年,人口增長率有效降低,控制了人口過快增長,從2002年的128 453萬人到2011年的134 735萬人,只凈增了6 282萬人。
從圖1還可看出,建國60年來,中國農業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有5個增長期(1959~1964年增長快速,年均增長率達6.30%,1966~1969年與1980~1982年則增長緩慢,年均增長率為1.05%與1.14%;1988~1990年增長較快,年均增長率達5.80%,1998-2002年是極緩慢增長期,年均增長率僅0.24%),其余時間是下降期(1970~1979年與1983~1987年是緩慢下降期,年均降幅為1.27%與0.72%,1991~1997年是較快下降期,年均降幅2.46%,2003~2011年為快速下降期,年均降幅達3.42%)。1991年前,除少數年份外,農業勞動人口都在不斷增長,其后盡管1998~2002年有小幅增加,但總趨勢仍是減少的,尤其近10年減少速度加快(2003-2011年年均降幅3.05%),以致農業勞動人口數量從2002年36 640萬人減少到2011年26 594萬人,凈減少1億多人。主要原因是機械化解放了農業勞動力,城鎮化與外出務工又消化了大量農業勞動力。
機械化與化肥施用量提高使糧食產量保持持續增長。從圖2可見,糧食產量在1949年為1 131.8億kg,1966年起便穩定超過2 000億kg,1978、1989年分別超過3 000、4 000億kg,1996年首次達到5 045億kg,2007年起穩定超過5 000億kg,只有1959-1961年因災和1999-2003年因糧食相對剩余和庫存充盈而對農業進行結構性調整[12]導致糧食連續減產。同時,油料產量也在提高,特別是以糧食為基礎的畜禽與水產養殖業快速發展,產量連續增長,主要農產品提供的熱量因此也在快速增長。
2.2 農業可供養人口與農業勞動生產力
依據2 600kcal標準,用式(2)-(4)算出歷年主要農產品提供能量可供養的人口數(圖3),并用式(1)算出歷年農業勞動生產力(圖4)。
對比圖3中農業可供養人口與實際人口,60多年來,按照人均每天2 600kcal能量的標準,1949~1978年中國農業產出不能供養實際人口,只能節衣縮食地在更低水平生存;1979~1981年則可勉強養活當時的人口,但基本沒有節余;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農業產出不僅能養活當時的人口,還有相當的節余。
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農業產出及可供養的人口數量雖然在增加,但是,一方面這種增長靠的是農業勞動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因總人口也在快速增長,所以,農業增長的成果還是被更快的人口增長所消耗掉,兩者只能達到勉強平衡,仍無多少節余可用來進一步改善國民的生活。
參照圖4,從供養數量看,60多年來,中國農業勞動生產力的變化情況是:1個農業勞動人口1952年可供養2.9人,1958年可供養4.0人,而1961年卻降至只能供養2.1人,1966年能供養2.7人,1969年可供養2.4人,1987年可供養4.0人,1991年可供養3.4人,1996年可供養4.2人,2003年可供養3.5人,2011年可供養6.5人。
從增長率看,60多年來,中國農業勞動生產力下降的時段有:1959~1961年,災害導致農產品產量大幅下降,農產品提供的總能量年降幅11.9%,農業勞動生產力也快速下降,年降幅高達18.6%;1967~1969年,農業勞動生產力下降主要是因這期間農產品提供的總能量下降;而1988~1991年總人口快速增長,3年間總人口增加了0.48億,農業勞動人口增加近0.68億,雖然此期間農產品提供的總能量有所增長,但農業勞動生產力仍在下降,年均降幅3.1%;1997~2003年,農業進行結構性調整[12]導致糧食產量下降,農業勞動生產力小幅下降,年降幅2.0%。60多年中,農業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時段有:1952~1958年、1970~1987年、1992~1996年、2004~2011年,這些時間里,農產品提供的總能量不斷增長,同時,農業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卻在下降,從而帶來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增長,增長最快速的是2004~2011年,7年的年均增幅達8.4%,該期間農產品總能量的年增長率為3.1%,農業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年降幅為3.7%;而1962~1966年,盡管農業勞動人口快速增長(年均增幅3.6%),但因農業生產恢復使得農產品提供的總能量大幅提高(年均增幅11.6%),從而農業勞動生產力快速增長(年增幅達7.1%)。如果不考慮其間的起伏,1952~1960、1961~1970、1971~1980、1981~1990、1991~2000、2001~2010年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66%、0.54%、3.06%、0.18%、0.21%、6.18%。可見,很長時間里,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增長并不快,直到近十年才有較大增長。endprint
2.3 考慮合理能量搭配的農業可供養人口與農業勞動生產力
根據《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01~2010年)》,為保障合理的營養攝入,每個人應按8﹕2的比例[18]分別從植物性農產品和動物性農產品獲得需要的能量。可以按這樣的標準獲得能量的人口,稱之為得到合理供養的人口。
用式(2a)、(2b)分別計算植物性產品與動物性產品能供養的人口數P1、P2,從P1、P2中選一小者即為按合理標準可供養的人口,并據此計算合理能量搭配標準下的農業勞動生產力。結果見圖4、圖5。
由圖5可見,中國農產品提供的能量構成在60多年中逐漸發生改變,植物性農產品提供的能量在總能量中的比重不斷減少,從1952年的97%,到1980年的95%、1990年的90%、2000年的77%、2010年的75%,相反,動物性農產品提供的能量比重在不斷增加。
根據小康膳食能量的標準和圖5及1.1(2)所述關系,1949~1951年、1959~1965年及1968~1970年,植物性、動物性農產品提供的能量均不能供養當時的人口。1952~1958年、1966~1967年及1971~1995年,植物性農產品提供的能量能夠滿足需要且有富余,但動物性農產品提供的能量不足,如1975年的人口是9.24億人,當年植物性農產品提供的能量可供養10.6億人,即植物性農產品尚有富余的能量。然而,動物性農產品提供的能量卻只夠1.83億人的需要,即如果按8∶2的合理能量搭配比例計算,有7.41億人得不到合理的能量;而在1975年以后,動物性農產品提供的能量持續增加,得不到合理能量的人口不斷下降。1996年,中國基本達到膳食營養小康水平,從那時起,動物性農產品提供的能量出現過剩;除2000、2002、2003年植物性農產品提供的能量稍有不足外,其余年份植物、動物農產品均有過剩,且動物性農產品提供能量的過剩遠高于植物性農產品。現在,中國農業不僅養活了13.47億人,還有能力不斷改善國民的營養結構,提高國人的生活水平。
參照圖4和圖5,從供養數量看,60多年來,按8∶2的合理能量搭配比例,1997年前,農業的供養能力主要受制于動物性農產品,由于動物性農產品匱乏,1個農業勞動人口1975年以前只能供養不到0.5人,1980年可供養0.9人,1990年可供養1.9人,1997年可供養4.0人;而從1998年起,供養能力主要取決于植物性農產品,1個農業勞動人口1998年可供養4.1人,2000年可供養3.4人,2005年可供養3.9人,2011年已供養6.0人。由圖4可見,隨著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國農產品提供的能量搭配趨向于合理,特別是近10多年來,按合理能量搭配標準可供養的人口與農業提供總能量可供養的人口數量越來越接近。
從增長率看,以8∶2的合理能量搭配比例為標準來衡量,近30多年中,1999-2003年為農業勞動生產力下降時段,年均降幅4.2%;其余時段均在增長,2004~2011年的年均增長率達10.8%。不考慮其間的起伏,1952~1960年、1961~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0年,合理標準下的農業勞動生產力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99%、2.00%、9.03%、9.83%、8.49%、5.66%。可見,從20世紀70年代起,合理標準下的農業勞動生產力才有較大的增長率,尤其90年代后,在基數已經很大的基礎上仍能以較高的增長率增長。
2.4 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國際比較
由《國際統計年鑒》[24]得到世界一些國家的農業生產相關數據(表1)。表中涉及的國家是世界上農產品的重要出口國,據此可認為,它們的農業產出已能滿足本國國民的需要,才有富余的農產品供出口。
從表1數據可以看出一些發達國家農業勞動生產力的情況,如2006年,1個農業勞動力在美國至少可供養111.1人,在法國與加拿大至少可供養90.9人,荷蘭、澳大利亞、新西蘭分別為71.4、45.5、22.2人,由于它們的農產品還大量出口,因此,可以認為,它們一個農業勞動力能夠供養的人口比這些數值還要大。相比之下,中國農業勞動生產力存在著顯著差距,如前所述,2006年中國的一個農業勞動力最多供養4.6人,甚至到了2011年,也只能供養不足7人,這還不是按合理能量搭配標準得到的數值,若按植物性產品和動物性產品供能8﹕2的要求,2006年,中國1個農業勞動力只有能力供養4.2人,2011年亦僅能供養6.0人,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更大了。不發達國家則與中國相似,單位農業勞動力的供養能力也較低。
根據表1中的數據,2006年發達國家平均1個農業勞動力至少可供養72人,即使中國只達到這個平均值的1/5,1個農業勞動力也可供養14.4人,這已經高出中國現有農業勞動生產力1倍有余,就算只按2011年農業供養能力計,也能節約1.46億人的農業勞動力。可見,要達到這樣一個發達國家農業勞動生產力的水平,還要經過許多的努力。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國要推進城鎮化。這就意味著將有大量人口從農業產業中退出,要實現此目標,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在農業勞動人口減少時不減少農產品供應,以滿足供養還將繼續增加的總人口的需要,并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據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人口發展“十一五”和2020年規劃》,到2020年中國總人口將達到14.5億,如果2020年的城鎮化率達到60%[25],則城鎮人口將為8.7億,農村人口為5.8億。假定農村人口的構成(2011年農業勞動力占農村人口40.51%)按近10年的變化趨勢(農業勞動力占農村人口的年均降幅1.15%)延續,則2020年時的農業勞動力將只有2.11億人,那時,1個農業勞動力要供養的人口應不會少于6.9人。與2011年的6.0人比較,農業勞動生產力要增長14.7%,也就是2011~2020年,中國農業勞動生產力年均增長不能低于1.6%,才有可能實現60%的“城鎮化率”目標。從歷史情況看,中國60年來農業勞動生產力平均增長率為5.16%,應該認為,1.6%的年均增長率并不算高,只要努力,且方法得當,完全有可能達到。endprint
通過與國際比較,要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實現農業能供養中國人口的目的,須做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與美國、加拿大等土地豐裕的國家相比,中國耕地資源稀缺,加上人口眾多,人均耕地面積和單位農業人口擁有的耕地少,要依靠有限的耕地資源供養眾多的人口,首先就必須加強對耕地的保護,防止破壞耕地,減少耕地流失。
2)中國農業現行經營體制主要是家庭承包責任制,耕地分散,農戶生產規模小,普遍輕視農業基礎建設,農業機械化推廣相對滯后。中國單位耕地農機使用量不僅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印度和泰國。因此,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應鼓勵成立各種專業合作社,合理規劃農田、平整土地、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擴大生產規模,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
3)除荷蘭與新西蘭外,中國單位耕地化肥施用量遠高于多數發達國家,甚至遠高于印度和泰國,說明中國不宜單純依靠提高化肥施用強度來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過多施用化肥還會產生一系列環境問題,如剩余化肥的流失將引起湖泊富營養化。因此,為提高土壤肥力和增產,應推行精準施肥與先進的栽培技術,加強農業環保和農業生態建設。
4)另外,中國農民文化素質較低,農、林、牧、漁業從業者受教育程度的構成為:未上過學8.2%,小學38.2%,初中47.9%,高中5.4%,大學專科0.3%,大學本科0.04%[26]。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需加強對農業勞動力的文化與農業技術的培訓,用現代文化、科學技術來武裝農民。
3 結論
1)按小康膳食能量標準,中國農業現有產出已可供養現有人口,如2011年中國農業提供的能量按小康標準可供養17.19億人,按8∶2的合理能量搭配比例也可供養15.92億人。因此,即使只達到2011年的生產水平,屆時的中國農業也有能力供養預測到2020年的人口,且有富余。
2)從供養數量看,60年來,不考慮合理能量搭配,中國1個農業勞動人口1952年、1958年、1961年、1966年、1969年、1987年、1991年、1996年、2003年、2011年分別可供養2.9、4.0、2.1、2.7、2.4、4.0、3.4、4.2、3.5、6.5人。如果按8﹕2的合理能量搭配比例為標準衡量,1997年前,農業的供養能力主要受制于動物性農產品,1個農業勞動人口1975年以前只能供養不到0.5人,1980年、1990年、1997年分別可供養0.9、1.9、4.0人;1998年起,供養能力主要取決于植物性農產品,1個農業勞動人口1998年、2000年、2005年分別可供養4.1、3.4、3.9人,2011年增至已可供養6.0人。
從增長率看,1952~1960、1961~1970、1971~1980、1981~1990、1991~2000、2001~2010年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66%、0.54%、3.06%、0.18%、0.21%、6.18%。在8∶2的合理能量搭配比例標準下,相應時段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年均增長率則分別為-0.99%、2.00%、9.03%、9.83%、8.49%、5.66%。
3)與一些主要農業大國(尤其發達國家)對比,中國農業的供養能力存在著很大差距,尤其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差距更為顯著。2006年幾個發達國家平均1個農業勞動力至少可供養72人,而同年,中國1個農業勞動力最多供養4.6人,2011年也只能供養不足7人。若按8∶2的植物性產品和動物性產品供能的要求,2006年中國1個農業勞動力只有能力供養4.2人,2011年亦僅能供養6.0人。
4)要提高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力,須加強耕地保護,防止破壞耕地,減少耕地流失;鼓勵成立專業合作社,合理規劃農田、平整土地、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擴大生產規模,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要推行精準施肥與先進栽培技術,加強農業環保和農業生態建設;并要加強農業勞動力的文化與農業技術培訓,用現代文化、科學技術武裝農民。
參考文獻:
[1] 速水佑次郎,弗農·拉川.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2] 李 靜,孟令杰.中國農業生產率的變動與分解分析:1978-2004年——基于非參數的生產率指數的實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5):11-19.
[3] 陳衛平.中國農業生產率增長、技術進步與效率變化:1990-2003年[J].中國農村觀察,2006(1):18-23,38.
[4] 郝水平.農業系統生產要素的投入對產出的影響[J].生產力研究,2006(3):27-28.
[5] 何 霞,夏建國,龔一鴻,等.灰色關聯分析在糧食產量影響因素分析中的應用——以川東地區為例[J].中國農學通報,2012,28(9):150-153.
[6] 黎雪林,呂永成.廣西農業投入與農業增長灰色關聯分析[J].廣西科學院學報,2002,20(2):88-91.
[7] 傅澤強,蔡運龍,楊友孝,等.中國糧食安全與耕地資源變化的相關分析[J].自然資源學報,2001,16(4):314-319.
[8] 封志明.中國未來人口發展的糧食安全與耕地保障[J].人口研究,2007,31(2):15-29.
[9] 賀一梅,楊子生.基于糧食安全的區域人均糧食需求量分析[J].經濟理論研究,2008(7):6-8.
[10] 馬永歡,牛文元.基于糧食安全的中國糧食需求預測與耕地資源配置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9(3):11-16.
[11] 封志明,史登峰.近20年來中國食物消費變化與膳食營養狀況評價[J].資源科學,2006,28(1):2-8.
[12] 梅方權.2020年中國糧食的發展目標分析[J].中國食物與營養,2009(2):4-8.endprint
[13] 胡小平,郭曉慧.2020年中國糧食需求結構分析及預測——基于營養標準的視角[J].中國農村經濟,2010(6):4-15.
[14] 唐華俊,李哲敏.基于中國居民平衡膳食模式的人均糧食需求量研究[J].中國農業科學,2012,45(11):2315-2327.
[15] 張利國.我國區域糧食安全演變:1949-2008[J].經濟地理,2011,31(5):833-838.
[16] 徐志宇,宋振偉,陳武梅,等.基于縣域的三大糧食作物生產優勢的空間特征分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2,17(5):21-29.
[17] 李 晶,任志遠,周自翔.區域糧食安全性分析與預測——以陜西省關中地區為例[J].資源科學,2005,27(4):89-94.
[18] 國務院辦公廳.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01-2010年)[N].國辦發[2001]86號.中國食品報,2001-12-07(第1版).
[19] 許世衛.中國食物發展與區域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1.20-22.
[20] 張永恩,褚慶全,王宏廣.城鎮化進程中的中國糧食安全形勢和對策[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9,30(2):270-274.
[21]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22]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編.新中國農業60年統計資料[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9.
[23]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編.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9-2012)[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2012.
[24] 中華人民國和國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05-2010)[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2010.
[25]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面向2020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12,(43):4-34.
[26] 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編.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09)[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 羅亞軍)endprint
[13] 胡小平,郭曉慧.2020年中國糧食需求結構分析及預測——基于營養標準的視角[J].中國農村經濟,2010(6):4-15.
[14] 唐華俊,李哲敏.基于中國居民平衡膳食模式的人均糧食需求量研究[J].中國農業科學,2012,45(11):2315-2327.
[15] 張利國.我國區域糧食安全演變:1949-2008[J].經濟地理,2011,31(5):833-838.
[16] 徐志宇,宋振偉,陳武梅,等.基于縣域的三大糧食作物生產優勢的空間特征分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2,17(5):21-29.
[17] 李 晶,任志遠,周自翔.區域糧食安全性分析與預測——以陜西省關中地區為例[J].資源科學,2005,27(4):89-94.
[18] 國務院辦公廳.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01-2010年)[N].國辦發[2001]86號.中國食品報,2001-12-07(第1版).
[19] 許世衛.中國食物發展與區域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1.20-22.
[20] 張永恩,褚慶全,王宏廣.城鎮化進程中的中國糧食安全形勢和對策[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9,30(2):270-274.
[21]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22]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編.新中國農業60年統計資料[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9.
[23]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編.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9-2012)[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2012.
[24] 中華人民國和國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05-2010)[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2010.
[25]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面向2020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12,(43):4-34.
[26] 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編.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09)[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 羅亞軍)endprint
[13] 胡小平,郭曉慧.2020年中國糧食需求結構分析及預測——基于營養標準的視角[J].中國農村經濟,2010(6):4-15.
[14] 唐華俊,李哲敏.基于中國居民平衡膳食模式的人均糧食需求量研究[J].中國農業科學,2012,45(11):2315-2327.
[15] 張利國.我國區域糧食安全演變:1949-2008[J].經濟地理,2011,31(5):833-838.
[16] 徐志宇,宋振偉,陳武梅,等.基于縣域的三大糧食作物生產優勢的空間特征分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2,17(5):21-29.
[17] 李 晶,任志遠,周自翔.區域糧食安全性分析與預測——以陜西省關中地區為例[J].資源科學,2005,27(4):89-94.
[18] 國務院辦公廳.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01-2010年)[N].國辦發[2001]86號.中國食品報,2001-12-07(第1版).
[19] 許世衛.中國食物發展與區域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1.20-22.
[20] 張永恩,褚慶全,王宏廣.城鎮化進程中的中國糧食安全形勢和對策[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9,30(2):270-274.
[21]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22]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編.新中國農業60年統計資料[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9.
[23]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編.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9-2012)[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2012.
[24] 中華人民國和國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05-2010)[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2010.
[25]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面向2020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12,(43):4-34.
[26] 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編.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09)[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 羅亞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