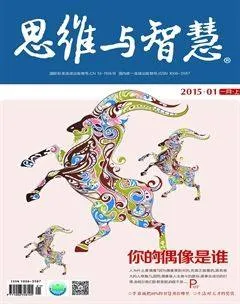婉如清揚
朱衛國
迷離,倉皇,帶著墮落的壞。像一只只青花瓷碗,可以敲得清脆作響,卻又極易碎裂,這是我們那時的青春。
為了緩解分配壓力,我們中師畢業后留于本校再讀兩年大專。三十幾張課桌,七零八落地散在教室里,陽光永遠逃避著那塊空間,我們像一個末路的草臺戲班,照例是花紅柳綠的面孔,卻只是燈火闌珊,紛亂斑駁。
蓬勃的叢竹搖曳枝條,試探著伸進窗子,三三兩兩的綠影在講臺一角自戀般地跳躍,想要把可愛的生動摻進灰色的世界里。
直到她的出現,我們慵懶頹廢的十九歲才褪去云翳般的眼瞼。一襲白衣,青黑的發絲光亮地綰在腦后,沒有豪言壯語,她說,我姓李,教古典文學的,是你們的班主任。她溫潤、嫻靜、明亮,泛著太陽下奔跑的光芒。
她像一個高明的畫師,把我們灰暗的青春涂抹得云蒸霞蔚,每一張面孔都點染著她親手調制的赤橙黃綠。我們開始手忙腳亂,她一個個地布置任務,微笑著,望著你,直至你點頭應允。演講會,辯論賽,專題閱讀,準備講稿,查閱資料,撰寫征文,我們被她那根看不見的微笑之鞭追逐得竭力奔跑,每個人都無暇去憂傷自己的前程,也無暇去追問奔跑的目的,需要的是不停息的行進。我們倉皇的青春不再迷離。
她總是微笑著,調配著每一張面孔,像正午的陽光,讓你的陰影無處藏匿。
我裹挾在這青春肆意明媚的洪流里,無處安放自己。我心儀多年的女生分配去了市里最好的學校,而我,縱然再過兩年,仍只能回到鄉下,守著蒼白與虛無。十九歲的心里盛不下任何理想與人生的歡娛。面對眼前奔跑的燦爛身姿,我猶如坐在月冷風高處的孤獨者,嘲笑似地看著一群螞蟻熱熱鬧鬧地追逐,心里悠然劃過一絲不去理會的淡漠,熱鬧是他們的,我能有什么?枯坐成了我心里自得的參禪。
她笑容可掬地找到我,要我幫她,做她的專職校對,她說,我以前在《師范生周報》上讀過你的文章,感覺不錯,你完全可以的。我不習慣于去拒絕一張寫滿真誠的笑臉,我成了她文稿的第一閱讀者。她寫的文章很多,多為古典名篇的解讀,每周總有一厚沓打印的初稿交到我手上。我不得不去努力看懂每一篇,逐字逐詞找出極少的錯誤,校勘好引文的出處,我還力求能發現文章語言、結構或觀點方面的可商榷處,盡管大多時候,我一個字也改不了。
忙碌而充實的校對漸漸地填補了心里的虛幻,那個沉湎于坐看云起的我已展開張揚的姿態,我會為某個詞的準確性向她提出質疑,為她引文的可靠性查閱多種版本,更會為她某個不俗的觀點拍手叫好。每一次,她的臉上都泛起光亮的笑靨,直至我疑竇已解,心悅誠服。
整整兩年,我完成了她近三十篇文稿的校對,猶如給了我一雙隱形的翅膀,浩瀚的世界任我越度。我的青春之色已然褪變,不再蒼白,不再灰暗,回頭過往,已是風華正茂。
我也成了校內外小有名氣的寫手。
懷著怕和愛,我無法說出她給予我的東西。
直到那一次,我終于答應替她講一堂《詩經》鑒賞課,我選的是一首《鄭風·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 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
我在講臺上緩緩地描述著那個畫面:陌上花開,蔓草青青,女子徐徐而來,婉如清揚,她的出現讓普通的田畈變得美不勝收……
她站在教室最后面,臉上閃現燦爛的光芒,輕輕的笑意悠然劃過,婉如清揚。那個鮮有陽光照進的教室一直生動著,那叢喜歡竄進來的青竹也愈發愛上了這塊兒天地。因了她,我們的畢業季在豐潤、充盈、晶亮中顯得格外燦爛,兩年的歷練,我們已不是當初的少年郎,不再易碎,錚錚有聲。
我們慶幸在暮靄沉沉的青春路口,遇見了她,她抖落一地的陽光,揚起手臂,劃開一條灑滿碎金的曠野小徑,引著我們走向水草豐美的遠方。
像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棵草搖動另一棵草,人生的很多際遇是一顆心靈去喚醒另一顆心靈。畢業離別的那一天,講臺上,她哭了,青黑的發絲有些凌亂地散著,那是她第一次在我們的時空里迷離蒼茫,我們手足無措。
她說,兩年前遇見你們,是為了喚醒我自己,那時,我離婚了,重回到了單身,我的每一天烏云密布,像當初的你們一樣,我必須重新找回自己。這兩年,我做到了,你們也做到了,請允許我感謝和你們的相遇,感謝彼此相攜相勵,走過一段不能蹉跎的年輪。你們是我生命的救贖。
校園的梔子花香馥郁沁人,彌漫著淡淡的憂傷。我們起身鼓掌,為我們共同的奔跑與飛翔,一路的陽光一程的歡笑。
她雙眼濕潤地微笑著,零露 ,泛著溫潤的光芒。
那一年她考取了華中師大的博士,我們也帶著閃亮的青春邁向四方,開始越度自己的天空。
陌上青,陌上蒼。她的笑臉與光芒穿越四季的變幻,總是浮現于眼前:野有蔓草,零露 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編輯 之之)
?有大花,也有小花,那些美麗的花,都是大花嗎?”
“只要有心開花,無論大花還是小花,都是美的。”小李說。
“人們贊美花,贊美的,都是那些大花嗎?”
“只要花美,無論大花還是小花,都會得到人們的贊美。”
“一個人如果用心做小事,為什么不能把小事做漂亮呢?把小事做漂亮了,為什么不能得到人們的贊美呢?”上司說。
(編輯 慕容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