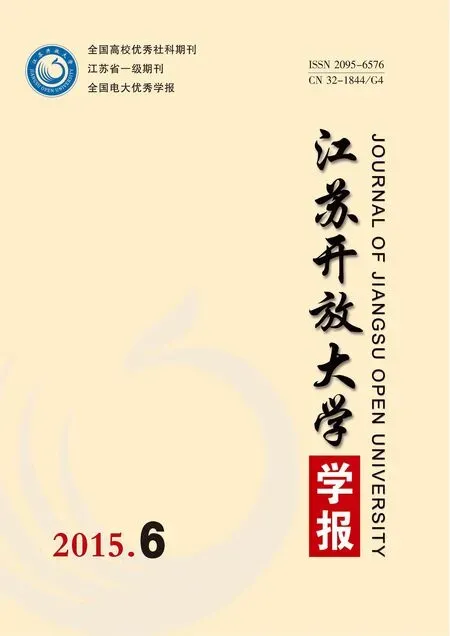論法治文化建設中的公民自覺
姜 璟
論法治文化建設中的公民自覺
姜 璟
“人”的要素是法治文化建設的根本和關鍵。公民擁有的精神品格和法律素養是評價一國法治文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準。現代法治社會的公民品格,主要體現為以主體身份歸屬為前提、以法治認同為心理基礎、以守法習慣為外在表現的公民自覺,其通過主體力量的支撐、價值理念的認同,以及公民與法律之間的情感鏈接,實現其對法治文化的推動作用。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中,傳統倫理文化的影響、新時期盲目自發的民眾訴求,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法治秩序的生成。因此,有必要塑造公民自覺,實現公民身份、價值觀念及國家治理模式的轉型,為法治文化建設提供支撐力量。
法治文化;公民品格;公民自覺
當今世界,法治的建立無疑已成為社會現代化的文明成果和重要標志。但法治絕不僅是規則體系的簡單架構和法律條文的堆砌,而更需要深層次的社會基礎的支撐,需要制度運行機制、社會管理模式及公民生活方式的引導。法治既是一種制度規范,也是一種文化現象。[1]法治要在社會中落地、生根、開花,需要將其作為一種文化觀念來引導和影響社會民眾的生活、精神與心態。而作為文化的法治,一方面它的生成以人的日常行為為原型,另一方面它亦為人的社會交往提供樣本,由此可見,“人”的要素是法治文化建設的根本與關鍵。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當代中國建設法治社會,處于社會轉型的同時也遭遇了傳統的巨大抵觸,尤其體現在人身上的文化抵觸:社會主體身上明顯的“中國文化印記”與西方法治精神之間存在著反復的糾結與難解的沖突。因此,中國的法治建設,制度變革固然重要,但更應當引起重視的是社會主體——“人”的變革,塑造其公民品格,培養其法治自覺,以支撐法治文化建設。
一、公民自覺的內涵
“公民”的概念最早發端于西方的古希臘雅典和古羅馬城邦時期。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及這樣的“公民”:都有充分的資產,能夠過小康的生活,實在是一個城邦的無上幸福。[2]隨著歐洲進入封建時期,奴隸制的民主共和消失,“公民”的概念也不再使用。直至17、18世紀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爆發,自由平等的交換關系確立,社會成員從封建桎梏中被解放出來,從原先的等級關系轉變為平等的契約關系。在這一重大變革過程中,制度的現代化直接帶來了文化的現代化,資產階級政黨運用憲法將“公民”概念固定下來。此時的“公民”,不代表任何階級,是具有一國國籍并在法律范圍內享有權利并承擔義務的個體,真正具有了“公”的特性。“公民”概念在憲法中的確定,使得社會成員在法律的框架內理性的交往、行動,參與政治生活,而作為一名與憲政共同而生的合格公民,以自由平等的精神為基礎,以權利義務為行為約束,擁有著現代公民品格的顯著特征即法治自覺,成了構建法治社會的重要動力和支撐。“自覺”不同于“自發”,自發是不受任何約束或影響自然產生的,自覺是人認識并掌握一定客觀規律時的一種活動,是人們有意識、有計劃、有目的的活動[3],因此,公民自覺應當是社會成員以公民的身份和角色,認同并接受現實法律制度,自主參與法律生活,積極促進民主與法治的主動理性行為。
1.主體身份歸屬是公民自覺的前提
社會個體對其公民主體身份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是生成公民自覺的基本前提。人以兩種狀態存在于社會之中:一種是不隸屬于任何人的個體的獨立存在;另一種是個體與其他人組合成集合體的共同存在。亞里士多德認為,“群居互動,以謀自足”是人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生活樣式,這就意味著我們既要生活得真正有尊嚴和有意義;同時也要充分認定自我歸屬于社會中基于某些紐帶而組成的群體,或是血緣,或是文化。所以,公民所具備的主體身份既包括了其對于自身為人的最基本特征的理解,要求社會尊重其個人獨立價值;同時也是對其所歸屬群體的認同,需要將群體中的其他成員同樣尊重為獨立個體的存在。主體身份歸屬為公民的獨特個體特征提供穩固的核心,也將公民之間的交叉關聯以共同利益的形式固定下來,從而公民擁有了追求自身權利的強烈愿望,同時也承諾了對他人責任與義務的承擔;公民具備了自我發展的長遠追求,也構建了成員間相互得益的社會責任體系。所以,每個理性公民都能夠認同自己和他人的公民身份,能夠接受與他人共有的血緣及文化上的共同體歸屬,[4]這一前提不僅僅能激發公民發揮社會成員的潛能,更能引導其對法治及生成的秩序產生情感,進而以主體的姿態參與社會法治建設。
2.法治認同是公民自覺的心理基礎
在法治文化建設中,基于公民承認其主體身份的前提下,公民自覺還需要以現代社會心理為其生命力的支撐,而這一支撐就是法治認同。所謂認同,可解釋為認可或同意,是社會主體在互相了解的基礎之上產生的來源于內心的親近感,進而表現出外在行為或選擇上的一致甚至是模仿。而法治認同,即是公眾通過實踐經驗和理性對法律進行評判,因法律順應民眾的價值期待,滿足民眾的需要,民眾從而認可法律,尊重和信任法律,愿意服從法律的過程。[5]只有在內心真正承認和尊重社會法律制度的公民,只有將自身作為法治建設主體的公民,才有可能形成法治文化所要求的公民自覺。因此法治認同,是形成公民自覺所必備的心理要素。
其一,法治認同是公民的主體性認同。主體性相對于客體性而言,即公民將自身作為社會法治的參與主體,以主人翁的姿態,積極參與法治建設的各個方面。首先,公民將自我發展、個體權利的保護作為法律制度的基本價值判斷;其次,公民將自覺作為國家法治的主要內驅力,政府的推動雖然也不可小覷,但只有依賴民眾才能有效推行;最后,公民以法治主人翁的姿態,積極參與到各個法治環節,比如參與立法草案的討論、參加聽證等,以實際行動真正地成為法治的主體。
其二,法治認同是公民的普遍性認同。實現“法治”,即實現良法的普遍遵從。既然法治需要良法的普遍遵從,那么法治認同也應當是得到社會普遍民眾的認同。因為我們所謂的“認同”,首先必須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其本意就體現為法律服從主體的廣泛性和普遍性,一國之內的任何公民、政府機關及社會組織都必須遵守法律,都必須在法律的框架范圍內交往、行動,不享有任何的法外特權。
其三,法治認同是公民的價值性認同。作為公民自覺的法治認同,不僅僅是一種工具主義的認同,更多的是社會公民對社會法律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基于公平、正義、民主等基本價值進行審視、判斷之后,得到的對法律的承認和信任,是公民的價值性認同。法治從萌芽之時,就要讓人們意識到獲得普遍的公平、正義,必須訴諸一種理性的治國方式,通過社會運行機制來約束人們行為,限制公權力,因此,公民對于法治的價值性認同,來自于其內心對于運用法律維護自由、權利的希望和期盼。公民自覺的形成,來源于公民內心對于法治價值、法治文化的認同,它是社會主體對法治文化中的正義觀念、良好的社會秩序觀念、公民作為人的觀念、制度正義原則以及關于合作性美德的共識。[6]
3.守法習慣是公民自覺的外在表現
建立在主體身份歸屬基礎之上,擁有了法治認同的強大內心力量的社會公民,應當在外在行為上表現出對法律的習慣性遵守和積極主動的服從,因此由主體身份和法治認同而派生的守法習慣,構成了公民自覺的外顯層面。川島武宜指出:法秩序沒有法主體者積極自覺地遵守法、維護法的話,法秩序是得不到維持的。……如果沒有守法精神,依靠權力,是不能得以維持的。[7]所以法治的實現,依賴于社會民眾對法律的自覺遵守,體現為外在行為方式與內心自覺自愿相一致。公民養成守法習慣,是將法律的他律性與強制性束縛,轉變為自律性與主動性遵守。守法,不再是公民經過利益衡量與功利計算的結果,而是其在事先認知法律規則的基礎之上,在做出行為選擇前,實際已經“忘卻”規則,自然而然習慣性的不假思索的結果。因此,擁有法治自覺的公民,不僅是要求人權、自由和民主權利的主張者與維護者,同時也必然是自覺的以理性精神和法律意識進行自我約束和定位的自律者。[8]
二、公民自覺對法治文化建設的支撐
評價一國法治文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準就是在相應的文化氛圍下生活的公民擁有怎樣的精神品格和法律素養。因此,有必要依靠培養公民自覺,通過公民主體力量的支撐、公民價值理念的認同、公民與法律之間的情感鏈接,實現其對法治文化的推動作用。公民自覺是個體與國家之間的鏈接與潤滑,國家通過法律規范公民應有行為的同時,公民亦自覺塑造著國家法治文化。其實,世界上成熟的法治國家一直在致力于公民精神與品格的塑造與培養,同時強調在國家與公民互動的基礎上建立相應的保障以保證公民精神與品格的發揮。例如,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出版了《公民的形成》系列叢書,近期又開始強調“民主政治的生機和活力來自新一代有能力和負責任的公民”;法國也在強化以學校教育為依托的基礎上,開展“公民意識教育活動周”活動。[9]西方發達國家都有意識地將公民品格的培養,納入其社會文化和價值觀的建設中,以此推動國家法治的建立健全。因此,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當國家逐漸減少其職能,退居幕后,強化公民品格的養成,強調公民主體自覺性的充分發揮,無疑成為法治文化建設的核心力量。
1.公民自覺為法治文化建設提供實踐主體
法治文化的建設,需要制度層面斐然的成績作為鋪路石,但更需要讓制度能夠真正運行起來的社會主體強有力的支撐,只有有了人的支持,文化的追求得到了人的響應,它才能真正落到日常社會生活中。而與法治文化相匹配的公民,具備的不是被動服從、簡單遵守的依附性人格,而是主動參與、自主守法的公民自覺型人格。在上述關于公民概念的發展歷程中,我們不難發現,古希臘時期孕育的公民概念,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后伴隨憲政制度逐漸成熟的公民文化,直至當代西方公民品格的塑造,這一切都成為社會法治發展的重要動力。法治文化建設,只有依托于公民,讓其自由平等的要求內化為法律的基本價值;只有依賴于公民守法的習慣成為社會行為的導向與示范,才能夠逐漸形成并得到長遠發展。因此,要培育法治文化,首當其沖要塑造現代公民品格,培養公民自覺,為法治秩序的生成打下堅實的主體根基。
2.公民自覺為法治文化建設尋求情感認同
法治文化在社會中的形成實際表現為社會成員能夠普遍自覺地遵守法律,對于法律的尊重成為社會的共識。而要讓人們能夠達到上述要求,必須源自于人們對他律性的法律有著來源于內心的自愿與認同,因此我們需要塑造與培養公民自覺。讓法律對于公民而言,實現從他律向自律的轉化,從被動服從的工具向完全信任的情感轉化,讓公民自覺為法治文化提供情感認同,否則法治文化乃至法治秩序會因為最終缺乏情感基礎而無法真正實現。
法治文化的情感認同,是社會主體對于法治從內心產生的親近感和信任感,這些情感因子集合成為法治認同的主觀意識基礎。當公民個體與社會法律制度之間存在著較高的信任度時,公民就會按照法律規范的要求指引自己的生活行為,引導自我的價值判斷;相反,如果當公民對法律制度產生懷疑甚至不再信任時,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抵觸情緒,甚至會放大某些表面“不合理”的因素,選擇規避制度或另行選擇,逆法而行,從而導致法律運行喪失了基本的民眾信任,也就無法落實于實際生活,更有甚者還會滋生出反抗的潛在力量,長此以往,法治秩序無法建立,社會穩定也是危在旦夕。因此,法治文化需要依靠民眾對其的情感體認,需要在民眾的觀念上達成共識。通過公民自覺的培養,公民以主體身份參與法治運行,在充分了解規則的基礎上產生法治認同,進而內心自覺自愿、習慣性地遵守法律,能夠有效培養與加強公民與法律之間的親近感、信任感,為法治文化的形成找到情感上的歸屬與認可,這樣的文化建設才能更持久、更有力量。
三、塑造中國公民自覺的路徑選擇
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讓中國穩健地邁入了世界經濟市場,法制體系的日益完善,讓中國開始了法治化進程。雖然改革開放、社會進步一方面帶來了民眾訴求的萌發與活躍,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矛盾與不協調,社會主體的公民品格更傾向于自發而非自覺,對法治秩序的構建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困擾和影響。因此,塑造公民自覺,對于中國社會的法治文化建設乃至法治秩序的建構有著重要的意義。
1.增強國民教育,實現“臣民”“人民”到“公民”的身份轉型
中國傳統社會,有著十分深厚的臣民文化和德治傳統,在這種典型的東方專制主義文化下,社會成員以“臣民”“草民”的身份,更多的是對天子皇權的服從與膜拜,主體角色、民主參與也就無從談起了,自覺自律的公民理性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更是相當匱乏,平等自由的人權觀念自然無法扎根生存。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社會成員在憲法上獲得了公民身份,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公民的概念并未深入人心,社會宣傳與教育中經常出現的是“人民”“主人”“群眾”。這些實際上都以“人民”的政治身份替代“公民”的法律地位,用政治人角色替代社會人角色。而在這種長期的政治引導下,一旦產生利益沖突,“人民”無法體現人民自以為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時,就會對法律及社會制度產生極大的質疑,進而價值觀念迷失方向。其實在民主法治較為健全的國家中,社會主體很少扮演“神圣殿堂”里的“人民”和“主人”,更多的是體驗著現實生活的“公民”。因為只有將公民身份賦予社會成員,給予其法律定位而非政治定位,給予其個體角色而非整體角色,社會成員才能真正地按照權利義務的要求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以自覺行動保護私權利、制衡公權力,從而形成公民對法律的信任和認同,即使公民對制度產生疑問,也會在規則框架內基于公民身份尋求解決途徑。“不管自利是如何地誘人,都必須讓位給更高(事實上是至高無上地)無私之公民責任的要求,這便是典型公民之表征。”[10]因此,當下中國要培養公民自覺,應當重視國民教育,轉變社會成員的政治角色,建立國家和社會的互通渠道,讓公民真正成為法治的受惠者、參加者、推動者,從而培養出必要的公民責任和社會擔當。
其一,在國民教育中專門設置公民教育課程。我國目前針對中小學生及大學生主要是以開展思想政治課程為主的品德教育課程,在這樣的課程中,缺少對于青少年關于公民認知、公民參與及公民品格的專門化、系統化教育。要培養公民自覺,最直接的途徑就是在學校教育中開設專門的公民教育以及專門的法治教育課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因此,十分有必要在現有的教學課程體系中,設置獨立的公民教育課,由專業法律人士編寫專門的公民教育及法治教育教材,并由其負責相關的課堂教學,以此來引導學生形成公民的身份觀念,擺脫“臣民”的傳統束縛,替代“人民”的政治角色,真正地了解法律、知曉規則,培養其在規則范圍內的理性精神,為現代法治社會中公民自覺的形成打下堅實的基礎。
其二,加強政府公務人員對自身身份的認知。公民自覺的實現,還需要社會中特殊群體的引領,對政府公務人員開展身份教育,顯得緊迫而重要。政府公務人員是政府工作的窗口,他們的行為、理念對于其他社會成員而言,有著較強的示范作用,對于全社會公民自覺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引領作用。因此,需要針對政府公務人員開展公民常規性的通識教育,增強其對于自身公民身份和政府雇員身份的準確認知。在此基礎之上,使其認識到自身對于維護公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重要作用,從內心自覺擯棄“以權壓法”“權力至上”,追求民主平等的法治精神,為公民自覺的形成發揮積極示范作用。
其三,促進廣大社會成員形成公民的身份定位與角色認知。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公民自覺的形成源自于公民對法律的普遍遵守,因此要讓法治文化成為社會主流價值文化,必須讓廣大社會成員逐漸形成公民的角色定位,通過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擴大公民的民主參與范圍。當法律及其運行機制確實成為公民的保護神,它的價值理念自然會得到每個公民的自覺認同,自然會贏得每個公民的主動維護,為公民自覺在全社會的形成拓寬有效的受眾層面。
2.轉型價值觀念,培育公民的合法性認同
中國傳統社會注重綱常禮教,有著深厚的儒法倫理傳統,社會成員將改變命運的希望往往寄托在“明君賢臣”之上,民主與法治的傳統闕如,因此,現代法治理性與傳統倫理文化存在著明顯的緊張與沖突。隨著經濟變革、制度演進,一部分人不加選擇、盲目接受西方極端個人主義思想,誤讀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價值追求。無論是傳統倫理觀念的阻礙,還是現今價值觀念的迷失,都影響了公民自覺的形成,使得現代公民品格難以建立,法治秩序的構建困難重重。川島武宜曾指出:傳統社會向現代商品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基于利益計算的法的非倫理性必然與傳統倫理相沖突,因此要實現現代法治,就必須把現代法精神內化為市民社會成員的法意識,并在正義原則上使法與倫理相統一,從而使法秩序得以建立和維持。[7]
現代法治的價值取向是弘揚人作為社會主體的自由理性,追求社會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人權保障、權力制約、司法獨立,實現社會的善治和人類的善業,乃是法治文化的根本意義和價值。[11]由此可見,現代法治弘揚的價值,既不是簡單的被動、奴性的服從,也并非是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和無政府,它是公民對于權利義務在法律框架內形式的自覺認同,是公民參與民主政治的理性行為,是自由與責任的有機統一。在當今思想多元化的時代,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確立現代民主法治的價值取向,培養公民對社會法律及其運行機制的認同與信任,對于塑造公民自覺非常關鍵。當然這種重建并非依靠自上而下的強制灌輸,而應當著眼于社會民眾的權利主張,立足于其對于權力制約的強烈要求,建立民主有效的互通機制實現公民的有效參與,讓自由、平等、人權等基本法治價值真正落到實處。唯有如此,才能化解不同思想觀念的沖突,整合社會中不同的價值訴求,統一為民主法治的主流意識形態,形成公民對法治的認同與信任,養成現代公民自覺的品格,進而真正建立起法治運行所需要的價值觀和文化,對公民的社會行為進行正確的價值引導,最終建立公民普遍遵守的法治秩序。
3.轉變國家治理動力,實現公民品格“自發性”向“自覺性”轉型
中國法治進程的啟動,是以國家為主要動力的,政府以其公權力的優勢制定了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節約了建設成本,加快了運行速度。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一方面由于缺乏社會文化土壤的基礎,社會權利無法實現對公權力的有效制約;另一方面鑒于公權力自我擴張的本性,越到法治進程的關鍵節點,它越本能地抗拒針對自己的規則約束,遭遇“自己的刀無法削自己的把”的困境,這些都給法治秩序的生成產生了阻礙。因此,隨著法治建設的不斷推進,其推動力量應該逐漸由國家轉向民間,國家治理的模式也應當由單純的政府管理轉變為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雙重治理框架。
令人擔憂的是,當前中國社會運行機制中,由于尚未形成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之間良性的互動機制,在網絡等公共媒介的呼吁和倡導下,公民精神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激情掩蓋了理性,暴戾代替了遵守。這種自發的公民品格并非理性自覺的守法精神,更非權利與自由的真正渴望。因此,法治建設需要民間力量的推動,不能依靠自發性的公民品格,而需要現代法治意義上的公民自覺。為此,國家一方面要“以人為本”,讓法律制度設計服務于社會成員,讓法治成為公民內心的認同和期待;另一方面,要拓展公民的參與途徑,提升公民的參與能力,積極回應民眾的合理訴求,給予公民自覺生成和發展的空間;特別是給予各種民間組織寬容的發展環境,使其成為政府與社會成員之間的橋梁,為公民自覺的塑造和公民參與能力的培養提供重要的社會平臺。
英格爾斯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夠賦予這些制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著這些現代制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上都經歷一個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現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一群傳統人的手中變成廢紙一堆。[12]事實表明,一國公民品格如果缺失,即便有著再完善的法律制度,法治也終將只是美好的夢想。我國的法治化進程一直重視法律體系的構建,而法治文化的建設缺乏足夠的力度和深度,普法宣傳停留在簡單的守法教育,公民自覺的精神品格在社會中并未形成。公民的身份不是一個簡單的符號,更是一種主體獨立及相互尊重的規范;公民自覺也絕不僅僅是單純地遵守法律,而是更深層次意義上的理性參與、法治認同與守法習慣的養成。因此,在當代中國,迫切需要推進公民自覺的品格塑造,為法治文化建設提供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強大的心理支撐,進而讓法治秩序的美好藍圖成為現實。
[1] 謝暉.法治與法治公民政治智慧[J].東方法學,2014(4):128.
[2]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
[3] 喬耀章.和諧社會與公民自覺[J].濟南大學學報,2006(2):4.
[4] 張翠梅.公民德性的三維建構[J].學術交流,2014(11):58.
[5] 李春明,張玉梅.當代中國的法治認同:意義、內容及形成機制[J].山東大學學報,2007(5).
[6] 龔廷泰.法治文化的認同:概念、意義、機理與路徑[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4(4):42.
[7] 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M].王志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8] 馬長山.公民意識:中國法治進程的內驅力[J].法學研究,1996(6):10.
[9] 袁聚錄.論中國民主文化的理性化[J].學術論壇,2009(1).
[10] Derek Heater.公民身份[M].張慧芝,郭進成,譯.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87.
[11] 龔廷泰.法治文化的認同:概念、意義、機理與路徑[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4(4):48.
[12] 阿歷克斯·英格爾斯.人的現代化[M].殷陸君,編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
責任編輯 虞曉駿
On Civil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w Culture
JIANGJing
/JiangsuOpenUniversity
The element of human is the root and key to the law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citizen's spiritual character and legal literacy are the important standards for evaluating the level of a country's law culture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civil character is mainly reflected by the civil consciousness: taking the subjective identity as the premise, legal identity as the psychological base, a law-abiding habit as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The civil character will promote law culture through the support of the subjective force, the value concept identity, and the emotional link between the citizens and the law.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culture, and the spontaneous and mindless appeal of common people's in the new period, have hindered the generation of legal order to some extent. Consequ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the civil consciousnes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vil identity, value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l, and provide a support for law construction.
law culture; civil character; civil consciousness
D621.5
A
2095-6576(2015)06-0077-06
2015-09-10
姜璟,江蘇開放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法學碩士,主要從事法社會學研究(17803387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