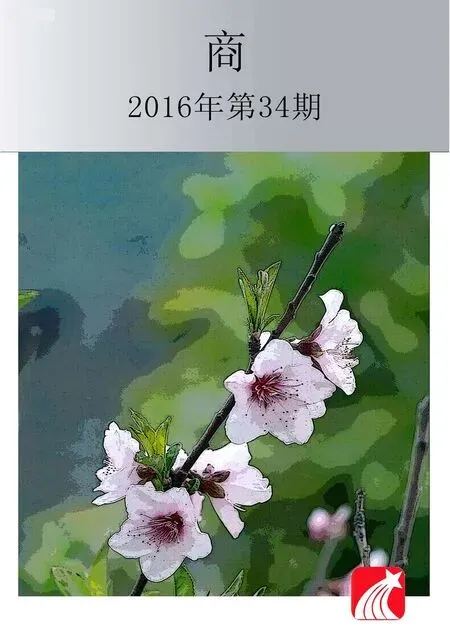對我國刑法目的的思考
盛振全
摘 要:刑法目的理念對刑事法治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目前理論界對我國“刑法目的是什么”的論斷仍然莫衷一是。筆者認為,刑法目的應當滿足具體性與宏觀性,進程性與終極性的要求,以實現目的論實踐性與理念抽象性的統一。預防犯罪應當與懲罰犯罪一道,成為我國刑法的手段目的,人權保護是我國刑法的終極目的,三者有機銜接、貫通,共同構成我國刑法目的金字塔形三元結構。
關鍵詞:刑法目的;預防犯罪;懲罰犯罪;人權保護;三元結構
一、理論界論點爭鳴
刑法目的的界定是刑事立法、司法及刑法理論研究的重要課題,“研究刑法的目的有利于促使司法人員時刻考慮自己的司法活動是否符合刑法目的,從而有利于將刑法目的貫穿于刑事司法活動的始終。”①目前我國對刑法目的究竟是什么、該怎樣構建,仍然沒有強有力的觀點統一思想。筆者認為,刑法目的是一個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理念,任何觀點的提出都將以不同形式促進我國科學刑法目的論的最終形成。
目前學界眾說紛紜,觀點大致包括:
1.雙重目的理論。該觀點的代表為我國刑法學界泰斗高銘喧教授,他認為根據我國《刑法》條文第一條的規定,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民是刑法目的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又是密切聯系,有機統一的。②該論點從法律本身出發,將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民作為刑法的雙重目的。
2.統一化目的理論。認為刑法的目的是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民的統一。懲罰犯罪從其最直接的意義上來說,也可以是刑法的目的,但是,它不是獨立的目的,不能為懲罰而懲罰,而是為了保護人民才懲罰犯罪,從這一點來說,它又是實現保護人民這個根本目的的手段。③也有人認為“刑法的目的是預防人們犯罪和維護統治秩序的統一。前者是實現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的最終目的。”④
3.法益保護理論。張明楷教授認為,我國《刑法》第2條規定了刑法的任務,也即是刑法的目的。認為“各種犯罪都是侵犯法益的行為,運用刑罰與各種犯罪行為作斗爭,正是為了抑制犯罪行為,從而保護法益;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之所以要預防犯罪,是因為犯罪侵犯了法益,預防犯罪是為了保護法益,這正是刑法的目的”。⑤
4.相對規范維護理論。代表人物是周光權教授,他認為刑法的目的具有時代性、相對性,穩定規范,確保規范的適用,是刑法的現實目的,保護法益則是刑法的最終目的。在權利不清、規范關系混亂、國民規范意識薄弱的時期應強調刑法的現實目的,而在社會轉型之后,社會整體高度穩定的情況下,刑法的目的轉換為法益保護。⑥
5.刑法目的區分理論。“刑法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直接目的則包括保護法益、預防犯罪、確認刑罰權和限制刑罰權。”⑦另有學者認為“刑法的目的包括制定和適用刑法所直接追求的目的以及制約并通過這種直接目的最終所要達到的目的兩個方面。詳言之,刑法的直接目的是預防犯罪,而最終目的是維護現存社會的生活條件。”⑧
6.目的多元理論。刑法的目的應該是多元化的,由于刑法本質上的多元化以及轉型期人們思想的多元化等原因,刑法的目的不應該僅僅限制在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民的范圍內,還應該包括:正義;法的穩定性;追求公共利益。⑨
總的來看:
首先,大多數學者認為刑法目的應當是多元的。刑法目的理論應當是綜合的系統化表述,既要兼顧宏觀上、終極性的指導意義,也要考慮具體性、實踐性要求,從而更好地發揮刑法目的理論的現實意義。
其次,刑法目的應加以區分,是有層次的。大多數學者贊同刑法目的應當包括第一層次上的直接目的、手段目的、現實目的等,進而實現第二層次上的根本目的、最終目的。由此可見,對于刑法目的的設置最好采用動態化、層次性的理念,力爭在理論內部實現目的功能意義上的銜接。
最后,目前來看,可以看作我國刑法目的理論通說的觀點有兩個:一是法益保護理論,二是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統一理論。
法益保護理論受到許多學者的正面或側面推崇,但也有學者正面批判。有學者認為由于法益的含義從來含混不清,法益保護的目的在實踐中很難實現;用法益標準來衡量所有犯罪有時難以奏效,反而使得法益概念高度抽象化、精神化;法益保護往往是事后行為,保護不力;可能帶來價值觀一元化問題;只看到現象,沒有揭示刑法目的的實質。⑩筆者也認為,僅僅用法益保護抽象概括刑法目的未免過于空洞,在立法及司法實踐中的指導意義不大,難以發揮目的理論應有的效果。
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統一理論多把懲罰犯罪作為直接目的或手段目的,是為了保護人權或保護人民這一最終目的而服務的。而對于預防犯罪,有學者加以涵蓋(上述區分理論),也有相當的學者對此專門加以批判,認為預防犯罪只是刑罰的目的,兩者應嚴格區分開來,要么把預防犯罪僅作為刑罰目的與刑法目的嚴格區分后加以排除,B11要么把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看作刑罰目的,而后歸入刑法目的之一,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B12。
二、對我國刑法目的三元論的設想
通過對我國刑法條文理念分析及學者理論探討的學習、總結,筆者認為,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權作為我國刑法的目的理論的組成部分較為可取,而且,預防犯罪也應當一道涵蓋在內,形成我國刑法目的金字塔形三元結構。金字塔頂端是我國刑法終極目的——保護人權,底端則由預防犯罪和懲罰犯罪來拱衛,三者之間非完全獨立,而是相互銜接、相互貫通,貫徹于刑事立法、司法全過程,從而有效發揮刑法的功能,實現刑法所追求的價值。在邏輯上,預防犯罪和懲罰犯罪是刑法的手段目的,保護人權是刑法的終極目的,手段目的為終極目的的實現提供保障,而終極目的的存在為手段目的的正確利用和發揮提供指導。有學者提出類似觀點,如提出一方面從微觀角度、階段性來看,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可以是、而且也應當是目的,只不過是刑法的淺層次的、直接的目的;保護合法權益和保障人權,維持法治秩序應當是刑法的深層次的、根本的目的。另一方面刑法目的并不等同于刑罰目的,刑罰目的是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刑法目的包括刑罰目的和人權保障兩個層次,應表述為為了懲罰和預防犯罪,保障人權,維護國家的整體法秩序。B13不過筆者對此亦有不同看法,待后文詳細論述。
在三元結構中,懲罰犯罪作為手段目的主要是從刑罰的角度來看的。刑罰制度是刑法的核心內容,刑法原則的貫徹、刑法功能的實現,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刑罰的有效實施:通過對犯罪分子科學量刑、施刑,實現打擊犯罪,保護人民利益和社會秩序,通過對無罪人的反向無罪不被追究的保護,實現司法公正權威和人權保障。應當說,刑罰目的的實現對于刑法目的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刑法目的在宏觀上也不應把刑罰目的排除在外。有學者提出“只要保證了刑罰的正義、做到罪責刑的均衡配置,這時,將懲罰犯罪作為刑法的直接目的就具有正當、合理性,從而不再有‘將犯人作為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之嫌。”B14筆者贊同這種觀點,而且筆者認為,懲罰犯罪作為手段目的之一有利于刑事立法、司法人員在理念上將懲罰犯罪、預防犯罪與人權保障更好地銜接后加以權衡,并以此作為指導。
保護人權作為刑法的終極目的,有學者對此已有專門的論述,一方面從刑法條文解釋角度提出刑法的目的在于“保護人民”,而保護人民的利益就是保護人權;另一方面從刑法特殊性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刑法保護人權的特殊性;最后歸結保護國家的整體法律秩序、保護人類社會的共同生活秩序,即保護人權。B15人權保護是當前國際法治的共同價值追求,保護人權作為終極刑法目的是可取的:一方面在內涵上,保護人民利益,維護司法、社會秩序等價值目標均能夠加以涵蓋;另一方面,人權保護不僅保護人民利益,也對包括犯罪人的合法權益加以維護,從而更好貫徹執行刑罰的基本原則,實現刑法打擊犯罪、預防犯罪、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功能。
三、預防犯罪作為刑法目的之一的理論分析及現實意義
如前所述,將預防犯罪也作為刑法目的受到很多學者的質疑,他們更多的把預防犯罪作為刑罰的目的,而后將刑法目的的宏觀性、正當性與刑罰目的的狹隘性、手段惡相區分,不把預防犯罪當作刑法目的之一,當然也有學者明確提出刑法的直接目的就是預防犯罪。筆者認為,預防犯罪不應當僅僅作為刑罰目的來看待,它是動態性、宏觀性的范疇,應當說在刑事法治理念上,在刑事立法、司法、刑罰執行以及宣傳上都應當貫徹預防犯罪理念。
在刑事法治理念上,應當看到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意義更大,因為刑事案件往往涉及人的生命、財產或者重大的社會關系、社會秩序,一旦遭到損害或者破壞,想要通過懲罰犯罪或者補償、賠償,根本難以實現社會關系或者秩序的修復。因此,在刑事法治理念上應當堅持預防犯罪優先,懲罰犯罪跟進。
在刑事立法上,貫徹執行預防犯罪理念有利于科學合理的配置犯罪與刑罰,以人權保護為根本指導,逐步去除不合理的重刑主義思想,構建合理、均衡的刑罰體系。
在司法中,貫徹預防犯罪理念在實踐中一個重要體現不得不提我國刑訴法新加入的“刑事和解”制度,對于民間糾紛引起的輕罪、輕微刑事犯罪、一般性的過失犯罪,如果當事人達成和解,達成賠償協議,可以對犯罪人從輕或減輕處罰。該制度也與國際范圍內倡導的恢復性司法制度相契合,在司法上意義一方面有利于更加側重維護受害人的利益,提倡救濟優先、保障人權,另一方面有利于犯罪人與受害人達成諒解、消除仇恨,通過輕微刑刑罰或者免除刑罰,避免再次犯罪的發生,修復受損的社會關系。可見,在司法過程中貫徹預防犯罪目的,有利于更好地實現刑事司法目標。
在刑罰的執行上,貫徹預防犯罪理念有利于科學、合理的利用社區矯正、緩刑、減刑和假釋制度,從而讓犯罪人能夠避免與社會隔離或者及時有效地返回社會,不致再次對社會產生威脅。也有利于合理規范監獄執法行為,減少或避免對罪犯的不合理對待。
在法制宣傳的角度上,堅持刑法目的預防犯罪、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權相結合,有利于提高民眾理性意識,逐步在理念上從原始正義、報復性正義向修復、恢復性正義轉變,促進社會和諧。(作者單位:吉林財經大學)
注解:
① 張明楷:《刑法學》,2007年第三版,第27頁。
② 高銘暄:《新編中國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
③ 參見何秉松:《刑法教科書修訂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頁。
④ 王剛:《刑法目的新論》,載《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第6-7頁。
⑤ 前引①,張明楷書,第27頁。
⑥ 參見周光權:《論刑法目的的相對性》,載《環球法律評論》2008年第1期,第33頁。
⑦ 轉引自王剛:《刑法目的新論》,載《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第5頁。
⑧ 張智輝:《刑法理性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頁。
⑨ 參見吳敏:《論刑法目的多元化》,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10期,第268頁。
⑩ 參見前引⑥,第34、35頁。
B11 參見彭輔順:《刑法目的的若干思考》,載《法學論壇》2009年第1期,第127、128頁。
B12 參見牛忠志:《刑法目的新論》,載《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6年第5期,第20、21頁。
B13 參見前引B12,第20、21頁。
B14 前引B12,第20頁。
B15 參見蔡英:《保護人權—刑法的終極目的》,載《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第107-1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