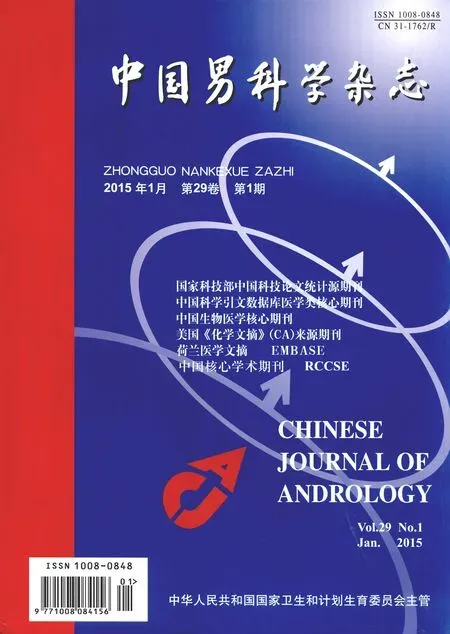早泄基因多態性研究進展
王俊龍 綜述 李 錚 審校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泌尿外科 (上海 200127)
早泄基因多態性研究進展
王俊龍 綜述 李 錚 審校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泌尿外科 (上海 200127)
早泄(Premature ejaculation , PE)是最常見的男性性功能障礙疾病,對患者及其伴侶的生活質量有著嚴重影響。近年流行病學研究顯示,PE的患病率約為20%~30%[1]。Revicki等[2]就PE對患者及其伴侶的生活影響進行了一項多國參與的、大樣本定量分析研究,顯示PE對各國患者及其伴侶的心理、性滿意度及其他多方面的生活都有著嚴重的負面影響。目前研究認為早泄的發生發展與患者的心理性、行為性和生物性等多方面因素有關,并提出了PE的心理學、神經內分泌學和神經生物學發病機制,但這些機制并不能揭示所有PE患者的病因,因此進一步闡明PE病因進而為更好治療PE提供思路具有重要意義。鑒于部分研究發現PE還受到遺傳因素的影響,最近一些研究開始關注PE發病與基因多態性之間的相關性。本文旨在綜述PE基因多態性方面的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
1943年Schapiro首次提出PE發病具有一定的遺傳性,他發現PE患者家庭的其他男性成員更易出現PE。Waldinger等[3]研究支持了上述觀點,他發現PE患者的一級男性親屬中PE發病率可高達91%。最近研究表明在早泄發病的多種因素中,遺傳因素占其中30%左右[4]。在PE的最新分類中,PE被分為4大類:原發性PE、繼發性PE、自然變異性PE和早泄樣射精功能障礙。4種類型PE的病因不盡相同,其中與遺傳學關聯最大的是原發性PE。當前,對PE發病的基因多態性研究主要集中在5-羥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相關基因和多巴胺相關基因上,在其他基因如催產素和后葉加壓素相關基因方面也有一定報道。
一、PEPE與5-HT5-HT相關基因多態性
大量動物研究和人類研究表明5-HT是射精活動中重要的神經遞質,在射精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調控異常會導致射精加快或延遲。5-HT相關基因也是PE基因學發病機制研究中被研究得最多的基因。迄今發現至少有3個亞型的5-HT受體即5-HT1A受體、5-HT1B受體和5-HT2C受體參與射精活動的調控。5-HT1A受體的激活可以加速射精,而5-HT2C受體的激活則會延遲射精[3]。研究表明PE與5 -HT神經傳遞降低有關,即5-HT1A受體功能亢進和(或)5-HT2C受體功能低下可導致PE的發生[5]。
5-HTT(5-HT transporter)是位于突觸間隙的跨膜轉運蛋白,為了防止突觸后膜5-HT受體的過度刺激,其能迅速地將5-HT從突觸間隙再攝取到突觸前神經元,5-HT在此進行代謝、失活,從而調控5-HT作用的時間與強度。人類5-HTT基因是由位于染色體17q12上的單基因SLC6A4所編碼,其轉錄區域的多態性是由一44bp長度的插入(‘ long allele ’ [L])和缺失(‘ short allele ’ [S])所致,表現出基因型為S/S、L/S、L/L的多態性。5-HTT不同的基因型轉錄活性亦不同,L等位基因的轉錄活性明顯高于S等位基因,兩者通過影響5-HTT蛋白的合成與作用進一步調控5-HT作用的時間及強度,相對于S等位基因,L等位基因可增加5-HTT的表達和5-HT的再攝取。
羅順文等[6]對119例原發性PE、60例繼發性PE和90例健康成年男性的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連鎖多態性區域(5-HT transporter gene-linked polymorphism, 5-HTTLPR)基因進行分析、比較發現,原發性PE組中S/S基因型的頻率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L/S基因型的頻率明顯低于健康對照組,S等位基因出現的頻率比健康對照組顯著提高。進一步研究將PE組按陰道內射精潛伏期(intravaginal ejaculation latency times,IELT)長短分成3組,發現各組間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頻率的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提示5-HTTLPR基因多態性可能并不影響PE的嚴重程度。Ozbek 等[7]對70例PE患者和70例正常成年男性的5-HTTLPR基因型進行分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5-HTT基因的L、S等位基因可以改變5-HTT蛋白的表達從而導致其功能上的差異,L等位基因的表達水平比S等位基因高3倍,即5-HTT基因啟動子區的多態性可以影響5-HTT的表達。由于S純合子與S雜合子在功能上表現出的差異并不明顯,從而推測出S等位基因可能在轉錄中占主導作用[8]。Janssen等[9]研究了89例原發性PE患者和92例正常男性的5-HTTLPR基因型,結果發現兩組的L、S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均無統計學差異,但在PE患者組中L/L基因型者的IELT明顯短于S/S、L/S基因型者,因此認為5-HTTLPR多態性與原發性PE患者的ELT相關。
由于L等位基因存在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ucleotide polymorphism , SNP),L等位基因可以進一步分為LA(常見類型)和LG兩種變體,前者表達產生的5-HTT蛋白多,而后者的作用基本等同于S等位基因,其表達產生的5-HTT蛋白少[10]。由于LG和S等位基因的基因表達水平幾乎相同(兩者的表達水平均低于LA等位基因),因此表現出功能性的三等位基因變異,先前相關研究中基因型為L/L或L/S的樣本就可能包含有LG等位基因的表達,從而掩蓋了5-HTTLPR的真實作用。鑒于此,Safarinejad[11]將PE患者和正常成年男性的5-HTTLPR基因的基因型更細化地分為/S、S/ LA、S/LG、LA/LG、LA/LA、LG/LG6類,并對它們進行分析和比較,發現5-HTTLPR基因型為S/S、G/LG或S/LG者PE的患病風險增加,而包含有LA等位基因者的患病風險并未增加。Safarinejad 等[12]進一步研究發現,5-HTT基因型不同的患者對選擇性5-HT再攝取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RIs)治療的反應性也不同,LA/LA基因型者對其反應性要明顯優于S等位基因攜帶者的反應性,這提示E患者的基因型或許可為未來臨床選擇用藥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結果認為5-HTTLPR的多態性與PE發病并不存在明顯相關性。Zuccarello等[13]對21例PE患者和100例健康成年男性的SLC6A4基因型進行分析,發現兩組5-HTTLPR、rs25531和STin2基因型頻率并無統計學差異。Jern 等[14]研究了1673例孿生兄弟及其非孿生兄弟的5-HTTLPR的多態性與PE之間的關系,發現5-HTTLPR多態性與男性的IELT及PE其他癥狀之間并無明顯相關性。鑒于5-HTTLPR多態性對PE影響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Zhu等[15]對部分相關研究作了薈萃分析,認為5-HTTLPR多態性與PE之間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并且L等位基因可以降低PE的患病風險。研究所涉及的樣本量相對較小、統計學分析各異以及PE診斷標準不甚統一等或許是導致部分研究結論相悖的原因。
5-HT1A受體功能亢進可加速射精,其基因存在多種多態性,其中研究最多的是5-HT1A受體基因的C (1019)G多態性,即1019位置上的胞嘧啶(C)被鳥嘌呤(G)所替換,G等位基因與5-HT1A受體高表達及5-HT 釋放減少相關[16-18]。Janssen等[19]對54例原發性PE患者的IELT與5-HT1A受體基因的C(1019)
多態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PE患者-HT1A受體基因基因型為GG和CG者的IELT分別為基因型為CC者IELT的2.5倍和1.9倍,表明5-HT1A受體基因多態性與原發性PE患者的IELT相關,CC基因型可以明顯縮短其IELT。
鑒于對動物和人類的研究均已表明5-HT2C受體的激活可以升高射精閾值和抑制射精,Luo等[20]通過對PE患者和正常男性的5-HT2C受體基因進行分析,推測5-HT2C受體基因兩種不同的多態性C-759T、G-697C與原發性PE之間的關系,發現病例組-759T/-697C基因型頻率高于對照組,而-759C/-697G頻率則低于對照組,攜帶有-759T和(或)-697C等位基因的男性PE的患病風險增大,表明-759T和-697C突變可能使5-HT2C受體基因啟動子的活性降低,進而使5-HT2C受體升高射精閾值的能力降低,導致攜帶者的PE患病風險增加。
二、PEPE與DATDAT基因多態性
5-HT系統對射精活動呈抑制作用,而多巴胺系統對其則呈興奮作用,并可對抗5-HT系統的作用[21]。多巴胺受體(dopamine transporter , DAT)通過快速地將DA重攝取到突觸前神經末梢來清除已釋放到突觸間隙的DA,從而及時終止DA對射精活動的興奮作用。多巴胺受體興奮劑可以促發射精,而其拮抗劑則會延遲射精。DAT基因(DAT1)編碼多巴胺受體蛋白,其位于染色體5p15.3,在其3’非翻譯區有一個長度為40bp并表現有多態性的數目可變串聯重復序列(variable number of tandem repeats , VNTR),其重復數目在3~12之間變化不等。DAT1最常見的兩個等位基因是9個重復(9-repeat, 9R)和10個重復(10-repeat , 10R),前者與DAT的低表達相關[22],而后者則與DAT的高表達相關[23, 24],這表明SLC6A3基因變化可以改變DAT的表達水平。
Santtila 等[25]對867例孿生兄弟及其非孿生兄弟(423例)的射精情況與DAT1多態性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研究,發現基因型為10R/10R的男性比基因型為9R/10R 和9R/9R的男性更易罹患早泄。Safarinejad 等[26]對PE患者和正常男性的DAT1-VNTR的多態性進行了基因分析,結果發現9R等位基因和9R/10R基因型都會增加男性PE的患病風險,而7R等位基因則會降低其患PE的風險。能導致高濃度DA的DAT1-VNTR多態性增加了男性PE的易感性,9R等位基因的存在導致DAT低表達,其對 DA的再攝取減少,使得突觸間隙內DA的濃度增加,從而加快射精活動。
三、PEPE與OXTOXT、AVPAVP受體基因多態性
對動物和人類的研究發現,催產素(oxytocin,OXT)和精氨酸后葉加壓素(arginine vasopressin,AVP)也參與射精活動的調控。在射精過程中,血漿OXT水平升高,OXT可以增加附睪、輸精管等參與射精活動的組織器官的收縮性,AVP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和OXT類似[27, 28]。AVP 受體基因共有6個AVP 1A 受體(AVPR1A)基因SNPs和1個AVP 1B受體(AVPR1B)基因SNPs,OXT受體基因共有12個SNPs。
Jern等[29]對1 517例孿生兄弟及其非孿生兄弟的射精功能、OXT和AVP受體基因的SNPs等進行分析研究,以了解OXT受體基因和AVP受體基因的多態性與射精活動之間的關系,發現OXT受體基因rs75775的SNP與PE相關,G/T基因型者相對于G/G基因型者或T/T基因型者的PE患病風險明顯增加,即這一SNP的雜合個體比其兩個純合個體有明顯增大的PE患病風險,而并未發現AVP受體基因的SNPs與PE之間有明顯的相關性。表明當射精反射開始后OXT和AVP的作用才開始顯得突出,而它們對觸發啟動射精這一生理過程的作用也許是比較有限的。
四、結語
PE作為最常見的男性性功能障礙疾病,近年出現的研究不斷揭示著其基因學,特別是基因多態性方面的發病機制。目前研究認為PE發病與5-HTTLPR、DAT基因和5-HT1A受體、5-HT2C受體、OXT受體、AVP受體基因的多態性均有關。其中部分研究還發現基因型不同的PE患者對PE藥物的反應性亦有差異,這初步顯示了PE基因多態性研究可為未來臨床選擇用藥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
由于參與射精過程的神經遞質(如5-HT)的表達通常是由多個基因共同調控的,單一基因及其多態性或許并不能直接決定其表達[30]。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Janssen等[9]的假說,即多個基因的多態性和(或)多個能加快射精活動的遺傳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了PE患者持續性的IELT過短,單一基因的多態性或許并不能揭示PE所有的潛在發病機制。同時由于射精活動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其中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基因-環境和基因-基因間的相互作用等,而基因多態性或許只能揭示PE發病機制的部分內容。因此,進一步研究PE的基因學發病機制及其與環境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對闡明PE病因并指導其治療具有重要意義。
致謝:本課題由上海市科委重大科研基金(09DJ1400400)項目資助
關鍵詞早泄; 基因多態性
參 考 文 獻
1 St Lawrence JS, Madakasira S. Int J Psychiatry Med 1992; 22(1): 77-97
2 Revicki D, Howard K, Hanlon J, et al. Health Qual Life Outcomes 2008; 6: 33
3 Waldinger MD, Rietschel M, Nothen MM, et al. Psychiatr Genet 1998; 8(1): 37-40
4 Jern P, Santtila P, Johansson A, et al. Int J Impot Res 2009; 21(1): 62-67
5 Waldinger MD, Berendsen HH, Blok BF, et al. Behav Brain Res 1998; 92(2): 111-118
6 羅順文, 王峰, 解志遠, 等. 北京大學學報?醫學版2011; 43(4): 514-518
7 Ozbek E, Tasci AI, Tugcu V, et al. Asian J Androl 2009; 11(3): 351-355
8 Andersson G, Larsson K. Eur J Pharmacol 1994; 255(1-3): 131-137
9 Janssen PK, Bakker SC, Rethelyi J, et al. J Sex Med 2009; 6(1): 276-284
10 Hu XZ, Lipsky RH, Zhu G, et al. Am J Hum Genet 2006; 78(5): 815-826
11 Safarinejad MR. J Urol 2009; 181(6): 2656-2661
12 Safarinejad MR. BJU Int 2010; 105(1): 73-78
13 Zuccarello D, Ghezzi M, Pengo M, et al. J Sex Med 2012; 9(6): 1659-1668
14 Jern P, Eriksson E, Westberg L. Arch Sex Behav 2013; 42(1): 45-49
15 Zhu L, Mi Y, You X, et al. PLoS One 2013; 8(1): e54994
16 Huang YY, Battistuzzi C, Oquendo MA, et al. Int J Neuropsychopharmacol 2004; 7(4): 441-451
17 Lemonde S, Turecki G, Bakish D, et al. J Neurosci 2003; 23(25): 8788-8799
18 Molina E, Cervilla J, Rivera M, et al. Psychiatr Genet 2011; 21(4): 195-201
19 Janssen PK, van Schaik R, Zwinderman AH, et al. Pharmacol Biochem Behav 2014; 121: 184-188
20 Luo S, Lu Y, Wang F, et al. Urol Int 2010; 85(2): 204-208
21 Hsieh JT, Chang HC, Law HS, et al. Br J Urol 1998; 82(2): 237-240
22 Vandenbergh DJ, Persico AM, Hawkins AL, et al. Genomics 1992; 14(4): 1104-1106
23 Fuke S, Suo S, Takahashi N, et al. Pharmacogenomics J 2001; 1(2): 152-156
24 Mill J, Asherson P, Browes C, et al. Am J Med Genet 2002; 114(8): 975-979
25 Santtila P, Jern P, Westberg L, et al. J Sex Med 2010; 7(4 Pt 1): 1538-1546
26 Safarinejad MR. BJU Int 2011;108(2): 292-296
27 Filippi S, Morelli A, Vignozzi L, et al. Endocrinology 2005; 146(8): 3506-3517
28 Studdard PW, Stein JL, Cosentino MJ. Int J Androl 2002; 25(2): 65-71
29 Jern P, Westberg L, Johansson A, et al. BJU Int 2012; 110(11 Pt C): E1173-E1180
30 Albert PR, Le Francois B, Millar AM. Mol Brain 2011; 4: 21
(2014-07-08收稿)
doi:10.3969/j.issn.1008-0848.2015.01.019
中圖分類號R 6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