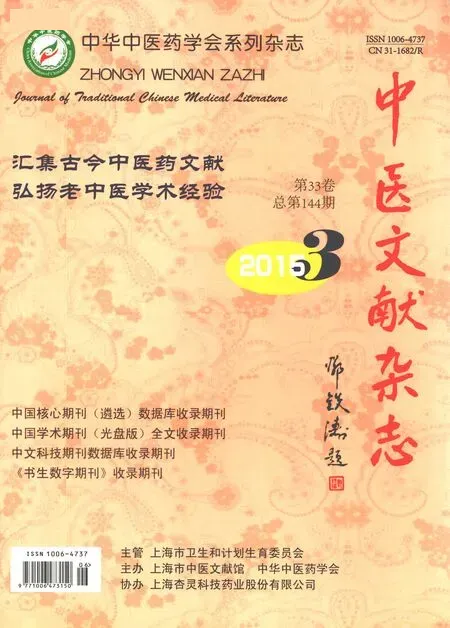老官山漢墓醫簡《六十病方》體例初考*
成都中醫藥大學(四川,60075) 和中浚 趙懷舟任玉蘭 周興蘭 王 麗 謝 濤
·文獻研究·
老官山漢墓醫簡《六十病方》體例初考*
成都中醫藥大學(四川,610075) 和中浚 趙懷舟1任玉蘭 周興蘭 王 麗 謝 濤2
老官山漢墓醫簡《六十病方》以15枚有病方編號的題名簡為目錄,約200支與題名簡編號相對應的病方簡為正文,二者共同構成了《六十病方》的主體結構。研究中發現《六十病方》的具體內容特點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主治病癥、藥物方劑、制用之法、禁忌事項書寫完整規范,多處有前綴中圓點的“其一曰”提示性文字運用,一些條文給出方劑的文獻來源等等。通過綜合考察《六十病方》的整體結構和局部特點,可以認為《六十病方》是經過加工整理后相對成熟的醫學文獻。此外,《六十病方》中存在的少數殘碎醫簡,因為具有潛在的文字辨識價值,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
老官山漢墓 六十病方 題名簡 病方簡 殘碎簡 體例 出土文獻
大約建成于西漢景帝(公元前188-公元前141年)、武帝(公元前157-公元前87年)時期的四川成都老官山漢墓M3中隨葬有736支醫學竹簡(今稱之為M3∶121)。相關考古工作者“依據擺放位置、竹簡長度、疊壓次序、簡文內容和書法風格等,大致可分為八部醫書和一部律令(《尺簡》)。”[1]M3∶137為《醫馬書》,共184支竹簡,本文并不涉及。
本文主要關注其中第106至342號竹簡(其中283~302,凡20簡并非醫書,暫不討論),舉凡217簡,所構成的醫書《六十病方》[1]。《六十病方》的體例問題非常重要,它是研究其具體內容的先導和綱領。
《六十病方》的整體情況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等相關機構極端細致認真的前期工作,使全面討論《六十病方》的體例問題成為可能。他們的保護工作除考古程序所必須經歷的諸如現場提取保護、實驗室清理、清洗和脫色、紅外線攝影、綁夾定形、脫水保護(乙二醛脫水加固法)、包裝入庫等文物保護常規操作之外,還同時進行了相當專業的學術探索研究工作。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在信息采集,主要指可見光攝影、紅外線攝影、紅外線掃描等過程中,相關工作人員事實上同時完成了全部竹簡的分類、編號、一定程度的綴合等極其重要的文獻保護和初步整理工作。
相關報道指出∶“竹簡‘整容’前后都拍照∶據肖璘稱,竹木器文物的保護一直是個難題,如果保護工作沒跟上,很容易導致文物損毀。面對這些在地下埋了2000多年的病嬌,成都市博物院決定一改以往的先考古后保護模式,轉而采取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同時進行,而這種模式的采用在西南地區尚屬首次。文保中心在竹簡出土之后即采取整體提取方式加以保護,考古工作移到室內,并在將變黑的竹簡脫色處理之前就對其進行紅外攝影,最大限度地采集簡上信息。在脫色之后,文保中心又對竹簡進行了第二次紅外拍攝,以查看竹簡是否在脫色過程中‘破相’。文保中心工作人員楊盛告訴記者,兩次照片對比來看,竹簡并未在脫色過程中受損。”[2]脫色處理前后的兩次紅外線攝影是相當必要的,它最大限度地保存這了批古簡的文獻特征,在這個過程中讓竹簡的毛筆字跡和編綸痕跡清晰再現;乙二醛脫水加固時的小心謹慎也是極端重要的,它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這批古簡的文物形態,在這個過程中讓竹簡的文物外形和毛筆字跡得以完整保存。
基礎性極強的信息采集、加工工作,為進一步探討《六十病方》的體例特征、學術內容提供了基本的物質條件。筆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竹簡殘片的保存和綴合是尤其難的一個過程,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做得相當出色。他們不但沒有落下任何一塊碎片,還在可能的情況下對其中的碎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拼接保存。比如189簡“撮”、“每”之間的拼接(因為有上下文字“白昌根”與“白昌”的相互映證,可以說明上述拼接準確無誤);275簡上端“魁合三分”右側原簡脫離,綴合拼接準確無誤。
我們對《六十病方》所進行的文字辨識、體例討論等工作就是在第二次紅外拍攝的基礎上進行的,所有竹簡編號也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的。
《六十病方》的體例討論
《六十病方》從文獻特征來分,有三類竹簡存在,分別是“題名簡”、“病方簡”和“殘碎簡”。其中題名簡和病方簡是據文獻內容特點進行的基礎性分類。對于若干出土后暫時難以準確歸入以上兩類,但有潛在辨識價值的殘碎醫簡,作為一種特殊的分類加以討論。
1.關于“題名簡”
謝濤等“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一文中已經指出∶“《六十病方》堆放在竹書上部較長的竹簡,長約34.5cm、寬0.8cm、厚0.1cm。分上、下兩層堆放,上層約175支,下層約40支,合計約215支,中間夾雜約20支較短的‘尺簡’(約22.7cm)。較長的簡(34.5cm)均為病方,包括15支題名簡,以及大約200支藥方簡。每支‘題名簡’分四欄,每欄先標出‘治某病’,次列出編號,15支簡四欄題名,共得60個病方。”[1]
謝氏文中用“藥方簡”的名稱稱謂《六十病方》的主體正文竹簡簡文,其實并無不妥。《六十病方》中也確有類似321、322簡的例子,僅羅列若干藥名,沒有炮炙加工,沒有份量記載,沒有組方跡象,但著意強調藥物的竹簡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六十病方》正文竹簡簡文給出了病癥描述,給出了方藥治法,給出了服法禁忌,因此本文擬用“病方簡”的名稱對其加以命名。使用“病方簡”的稱謂,除了這一名稱與其內容特點更為契合的客觀因素而外,也包含了主觀上盡量與《六十病方》的書名保持一致的想法。
謝氏文中并未明確言及所謂15枚“題名簡”,是存在于《六十病方》原始堆放層的上層(106~282),還是下層(303~342),但參照同書“病方簡”簡頭自書的編號與題名,對這15支“題名簡”進行了首次完整的復原[1]。在復原過程中使用了如下兩種格式∶其一,舉凡“題名簡”中所無,乃據“病方簡”輯復的文字用方括號括起;其二,舉凡“題名簡”中俗字、借字,皆將相應正字列出并用圓括號括起。上述兩種方法的使用不但方便了理解,也最大限度地再現了“題名簡”原貌。
上述15簡的簡號依次是276、280、351-378、266、187、186、137、136、319、308、332、324、328、342、
341簡。需要明確指出的是351-378簡已經超越了《六十病方》106~342簡的初步歸類,351簡今歸屬于《病源論》,實屬第3枚“題名簡”的上半段,其文曰“治瘕三、治腸山十八”;378簡今歸屬于《諸病癥候》,實屬第3枚“題名簡”的下半段,其文曰“治傷瘕卅三、治女子瘕卌八”。
由于《六十病方》的上層簡占用106~282之編號,下層簡占用303~342之編號,因此,如果我們先入為主地認為,現有排序基本上保存了出土前的原始排序,那么我們可以推測得知這15枚“題名簡”是分別保存于《六十病方》原始堆放層的上層(106~282,約175支)和下層(303~342,約40支)之中。
通過簡單分析可知,“題名簡”在上層者7枚∶276、280、266、187、186、137、136(其中甚至包含了排序比較靠前的136、137簡);“題名簡”在下層者7枚∶319、308、332、324、328、342、341(其中甚至包含了排在全書最末的341、342簡);“題名簡”在它層者1枚,斷為兩截分別是351簡和378簡。
如果考慮到《六十病方》下層竹簡數僅占全書竹簡的不足1/5(40/215或217),而存居下層中的“題名簡”卻與存居上層者相當(各為7枚),并且散逸在外的第3枚“題名簡”還在《六十病方》的更下方。我們甚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理應在全書之首的“題名簡”反而位居《六十病方》的下層者為多。這一現象,對于我們形象地理解古代簡策書籍的卷放方式有一定的幫助。如果有機會接觸實物細致觀察,或許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六十病方》全書排序問題的最終解決。
2.關于“病方簡”
“病方簡”是《六十病方》的主體內容,其具體行文大約還是以以病系方的條文方式為主,不同病種之間的相互關聯程度并不高。以189簡的行文格式最為常見∶“廿八∶治下氣。取白昌根七尺,圭尺,荝一果,并冶,三指撮,每旦□。白昌,一名曰三白。”其中病癥序號“廿八”與“題名簡”中的第二十八個病名相應。由于《六十病方》的病方簡總數在200枚上下,所以有超過半數以上的竹簡中是不存在病癥序號的,這對排序問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六十病方》所療之病多以“治某病(方)”的方式加以表達,個別竹簡以“已某病(方)”的方式加以表達。如207簡作“廿九∶已身病大疕方”;211簡作“卅∶已人身及四支攣詘不可信者方”。此后續接相應方藥組成及使用方法。個別條文尚有校勘考證、病案討論、藥物說明、詁訓解說、禁忌有無、試行情況、來源出處等內容。
需要指出的是,《六十病方》某些條文方藥制用之法后的討論和比較內容,是同時期相應著作中較為少見的。換言之,《六十病方》病方簡在體例層面有一個較為明顯的特點,那就是某些條文中包含了對比性的論述內容,并且所提示的內容(至少是一部分內容)往往出現在同一編號簡文內或編號相近的竹簡中。所謂提示語,多用“其一曰”(或“一曰”)的表達方式。在《六十病方》中出現10次“其一曰”的特殊行文體例,且此3字之前皆有中圓點冠其首。比如154(卌六)、156、164、173、177、209(十九)、220、223(五十八)、233、258等簡皆循此例。185簡有“一曰”云云之例,亦以一中圓點冠其首。337簡亦有“一曰”2字卻無點以冠其首,疑因此條“一曰∶取屏前弱涂丸之”云云為單獨一簡,“一曰”2字恰居簡端之故。需要指出的是,331簡中亦有“其一曰”3字,但我們初步判斷此簡并非《六十病方》的內容,故此處暫不予以討論。
如果能合理運用這一體例現象,對于《六十病方》的文字識別、條文排序等諸多方面均有益處。比如234簡治消止溺一方與220-227簡提示語“其一曰”所言之方有所雷同,可以互參;再如253簡凝水石圭畺一方與177簡提示語“其一曰”所言之方有所雷同,可以互參;再如156簡“直溫酒中酓之,衰益,以知毒為齊。其一曰∶治山,取榖大把二,干姜三果,圭二尺,勺藥五寸,棗半斗。”很顯然前后均有脫文。因其提示語為“其一曰治山”,故可暫置之于166簡“十六∶治頹山”條下。但并非所有的“其一曰”提示語所涉之方均可找到,說明這份文獻仍有所脫失。
3.關于“殘碎簡”
需要指出的是,前文述及的“題名簡”和“病(藥)方簡”之名在謝濤等“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一文中已經提出,而《六十病方》“殘碎簡”的名稱由本文首次提出。與“題名簡”、“病方簡”從竹簡的文獻內容角度命名不同,所謂“殘碎簡”是以竹簡的外在形制命名的。“殘碎簡”,顧名思義就是并不完整的殘碎簡片,究其實,“殘碎簡”是從原始整簡中脫落分離而成的。如果可以被復原,它們最可能是“病方簡”的一部分,也可能是“題名簡”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同置一處的《六十病方》以外的其他竹書斷簡的一部分。文中的“殘碎簡”特指有潛在辨識價值的保留筆畫殘存的零碎簡片。
《六十病方》中還包含了一些暫時缺乏辨識價值的無字簡。無字簡分兩類∶一類是無字整簡,如326簡系無字整簡,330簡系無字整簡(下上附系無字斷簡各2~3枚),就長度而言,254簡接近無字整簡,并附3~4枚無字斷簡,310簡亦接近無字整簡,并附5枚無字斷簡;另一類是無字斷簡,如131簡簡端、162簡右側(2枚)、163簡右側、168簡左側(2枚)、169簡右側(至少1枚)、188簡右側(3枚)、256簡(6~7枚)、274簡簡端、275簡簡尾、276簡簡端(6枚)、340簡簡尾(7枚)等處所隸之無字小碎簡片等。無字簡對于文獻內容的考察似無多少幫助,但對于體會原書的整體規模仍略有益處。本節并不擬細致討論無字之簡,而意在討論有潛在辨識價值的保留筆畫殘存的零碎簡片——“殘碎簡”。“殘碎簡”和“斷簡”還有所不同,“斷簡”中可以保留完整的文字,而“殘碎簡”僅余極少的點捺墨跡。
《六十病方》中包含若干僅遺存極個別筆畫殘留的零碎簡片,這些零碎簡片往往沒有單獨簡號標志,它是附在其他各簡簡號之下的,只有仔細觀察方可發覺。“殘碎簡”只有經過相當認真的拼合后方可辨識,短期之內很難確定其所從何來,但它們有潛在的辨識價值,不應當被忽略。十分可貴的是,這些包含筆跡殘留的碎片均得到了妥善的保存。為了給將來更加深入細致的研究討論提供相關信息,筆者擇要羅列相關殘字碎簡的所在位置。《六十病方》中保留個別殘留筆墨點畫的碎簡片斷分別出現在152簡簡端右側,163簡簡端右側,168簡簡端右側、中央各1枚,169簡簡端中央2枚,188簡右側所附2枚,252簡簡端左側,282簡簡端(倒置),330簡簡尾(倒置),340簡簡尾等處。由于所有辨識基于相應照片而非實物,故有所遺漏、錯認在所難免,希望有條件的讀者深入研究,最終得出比較公允的結論。
《六十病方》的拼接綴合
首先應當指出,《六十病方》紅外照片中絕大多數斷簡的拼接、綴合結果是準確可靠,甚至是精妙絕倫的,只有極個別斷簡的拼接位置需要有所討論。比如。
278簡∶“治風痹□……暴血,氣暴上腹盈痛方息者。壹酓藥病已,病已三日而復故。”在“治風痹□”和“暴血……病已三日而復故”之間,事實上是斷開的,暫從文意上考慮兩片斷簡之間似缺乏必然的聯系。筆者認為,這樣綴合拼接的理由還略嫌欠缺。
120簡∶“·治益氣□鹿腸、則各一分,犁如、牛膝、卑挈、山朱臾、桔梗、圭、蜀椒、白芷、細辛各二分。”相較于278簡的易于判斷,120簡的拼接現象,若非仔細審諦不易發覺。在“治益氣□鹿腸”與“則各一分”之間的拼接之痕,上下齟齬,似不能完全吻合。慎重起見,暫將此簡上下半段分屬不同條文處置。
此外,《六十病方》251簡簡端原先倒置一枚斷簡,其文曰“□毋汗”。很顯然,進行初步文字綴合的專家很快意識到這是個錯誤,于是以255簡的編號對“□毋汗”3字重新加以攝影存檔。
《六十病方》的成書推測
討論《六十病方》紅外照片的拼接偶誤和《六十病方》出土之后的殘碎簡片等等,是基于《六十病方》封存2000多年后重見天日的狀態,還不是《六十病方》寫定時的狀態。事實上,若能結合《六十病方》的具體文字特征,并對《六十病方》體例格局重新審視,我們有可能對《六十病方》成書的情況略作推測。
1.《六十病方》書寫格式規范
《六十病方》書寫格式較為規范,從全篇內容觀察,前有目錄(題名簡),后列正文(病方簡)。且目錄正文次序井然,有明確固定的一至六十編號。這種格式說明《六十病方》在編寫形式上較之《五十二病方》沒有病癥方藥編號更加成熟、規范和實用。若具體到每一個條文,其共性也極強。舉例如下。
(166)十六∶治穨山。取茈帚七分,少辛四分,厚柎二分,杏核中實、圭、蜀椒、蕉莢各一分。合和,以方寸半刀取藥。
(156)直溫酒中酓之,衰益,以知毒為齊。·其一曰∶治山,取榖大把二,干姜三果,圭二尺,勺藥五寸,棗半斗。
166-156兩簡是聯系在一起的兩個條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書寫格式其實是非常規范有序的,除平常可見的主治、藥味、服法,依次論述而外,我們可以看到此條條文對于藥物順序的排列非常講究,它是嚴格按照藥物分量由重到輕的順序安排的。這樣的藥味安排不一定是臨床醫家實踐過程中的標準程式,卻在醫理和文獻兩方面體現了《六十病方》輯錄者獨具匠心的學術才干。上述表達方式在醫理層面隱約照顧到了藥方君臣佐使和藥味輕重緩急的關系,在文獻編輯層面,有此順序不僅爽目醒神,而且相同分量以“各”字歸并一處也減省了筆墨簡片資源。這是學有章法、用有準繩的表現。
第二個需要注意的現象就是“·其一曰∶治山,取榖大把二,干姜三果,圭二尺,勺藥五寸,棗半斗”的存在。前已述及“其一曰”是一種提示性文字,它把醫學文獻中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非常明確地展現出來。這種從臨床實踐出發的寫作文字,事實上是對類似病證和處方進行了合理的對比和歸納,它不僅有利于保存不同醫家的學術經驗,而且對臨床醫家診病處方時拓展思路、選擇用藥都有切實的幫助,這是勤求古訓、學以致用的表現。然而能達到上述水準,似乎也在提示《六十病方》并非草創之品,而是在前人文獻基礎上經過相應的編輯、加工和整理而成。
2.《六十病方》文獻來源廣泛
《六十病方》所涉疾病種類齊全、內容廣泛,舉凡后世所言內科(109治風,121治沓咳,226治傷中)、外科[如img105-116治鼠(前一簡編號即為img105,與簡116兩簡拼接),143治金傷,166治頹山]、小兒(270治嬰兒間方)、婦產(197治女子不月,230治字難者,352治女山)、五官(127治風聾,167治目多泣,236治氣暴上走嗌)、皮膚(題名簡332治白徙,196治鮮,207已身病大疕方)各科均有涉獵,而湯藥(215治溫病發)、丸藥(154治消渴)、熨法(133治傷寒足清養者)、摩法(211-213已人身及四支攣詘不可信者方)、洗法(207已身病大疕方)、外治法(196治鮮)、內外合治法[143治金傷,151-147治湯(湯字疑誤),197治女子不月]、祝由(230治字難者)諸療法應有盡有。正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中所言∶“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3]
《六十病方》中既有廢丘庫里(193簡)、廢丘蒼里(201簡)、廢丘卜里(202簡)的診病紀錄,又有《息生生方》(158簡)、《濟北守丞方》(161簡)、《都昌跳青方》(196簡)、《公孫方》(213簡)等的引書提示,可謂原始文獻來源廣泛,注重實踐、博采眾長。
不論勤求古訓抑或是博采眾長,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六十病方》的成書過程。這一成書過程提示兩點∶其一,雖然《六十病方》隨墓主人入葬的時間是西漢早期,但其成書時間有可能上推更早一個時間段。其二,不除外今后發掘的秦漢醫簡、帛書中出現與其內容略有雷同的文獻資料。
李家浩教授指出∶“北京大學藏漢代醫簡共711枚,其中整簡516枚,殘簡185(疑是195之筆誤)枚。整簡長23~23.2cm,寬0.7~0.9cm,有些簡可辨上下契口及編痕;殘簡長短不一,最短的僅1.9mg……馬王堆《五十二病方》的書寫材料是帛書,有不少殘損,加上字體是由篆入隸的古隸,因此對其文字的釋讀有一定困難,而《北大醫簡》中的一些醫方和《五十二病方》內容相同,為校讀《五十二病方》提供了絕佳材料。”[4]筆者認為,《北大醫簡》不論書寫年代字體,還是體例格式等方面更接近《六十病方》而不是《五十二病方》。課題組成員趙懷舟曾在2015年1月4日和北京大學李家浩教授電話溝通,了解《北大醫簡》的相關出版進度。李教授告之目前他已退休,現由北京大學朱鳳瀚先生主其事,可相與聯系。此后課題組成員的確發現《北大醫簡》與《六十病方》有關聯的明確證據,希望《北大醫簡》早日出版。
[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J].考古,2014,(7):62-64.
[2]徐劍簫.2號墓主人可能是個“好吃嘴兒”——老官山漢墓挖出西漢織機簡牘追蹤[N].成都商報,2013-12-20(25).
[3]漢·司馬遷.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記[M].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993.
[4]李家浩,楊澤生.北京大學藏漢代醫簡簡介[J].考古,2011,(6).88-89.
Tentative Study on Medical Bamboo Slips ofLiu Shi Bing Fang in Lao Guan Shan Cemetery
HE Zhong-jun1,ZHAO Huai-zhou,REN Yu-lan1,ZHOU Xing-lan1,WANG Li1,XIE Tao2
(1.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ichuan 610075,China 2.Chengdu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Sichuan 610075,China)
Found in Lao Guan Shan cemetery,Liu Shi Bing Fangis one medical book made of bamboo slips.The main structure consists two parts:15 title-slips of catalog with prescription numbers,about 200 slips of text according the catalog.In further research,more features of concrete content are concluded as follows:rule of writing is integrated and standard in indication,prescription,direction,and contraindication;suggesting words of"qi yi yue"by many prefix dots;literature references of prescription given by some sentences.It can be summarized thatLiu Shi Bing Fangis one quite mature medical literature through processing and reorganizing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whole structure and partial characteristics.Besides,it should be put enough emphases on rare fragmentary slips due to their potential value of words identification.
Lao Guan Shan cemetery;Liu Shi Bing Fang;title slips;prescription slips;fragmentary slips;style;excavated document
R289.3;H121
:A
:1006-4737(2015)03-0001-05
2015-04-22)
四川省科技支撐計劃“成都市老官山醫學文獻文物的科學價值研究”(編號:2014SZ0175)1成都中醫藥大學項目組特邀成員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61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