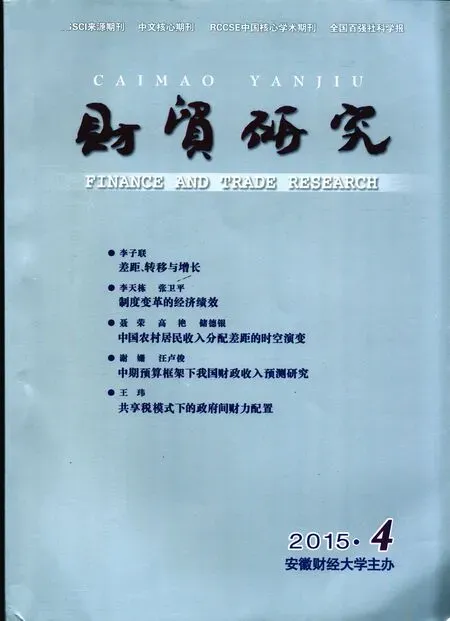環境不確定性、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
李勝楠 吳泥錦 曾格凱茜 解延宏
(1.天津大學,天津 300072;2.天津財稅智能化技術工程中心,天津 300072)
一、引言
公司的投資行為及其效果對一國經濟發展的各個層面都具有深遠影響。然而,眾多研究均表明,過度投資、投資不足、投資短視等情況普遍存在于各國的企業中(Jensen,1986;Malmendier and Tate,2005;楊華軍和胡奕明,2007;唐雪松等,2010;戴德明和王小鵬,2011)。Coase(1937)指出,企業管理者擁有最為重要的投資決策權力,對企業的經營理念及發展戰略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現有文獻分別從高管過度自信(張敏等,2009;Brown and Sarma,2007)、高管任期(Wiersema and Zhang,2011)、高管動機(May and Don,1992)、管理者背景(李焰等,2011;張兆國等,2013)、管理者個人特質(Bertrand and Mullainathan,2003;Huang and Kisgen,2013)等視角研究了管理者特征對公司投資行為的影響,成果豐碩。但是Coase(1937)的觀點存在一個重要的前提,即管理者要具備實質性的權力,否則上述管理者特征對投資行為的影響也就必然缺乏堅實的基礎。這也是本文從高管權力視角考察過度投資行為的一個重要考量。
此外,公司的投資決策還受其所處的內外部環境的影響。然而,針對不確定性環境中,不同終極控制人性質企業的高管如何使用其權力影響投資決策,現有文獻還缺乏深入探討。因此,本文以管理者權力為切入點,探討在中國特有的市場背景下,不同終極控制人性質企業的高管權力對過度投資的影響機制,以揭示環境不確定性影響企業投資的內部機制。本文的貢獻主要有:第一,現有對投資行為的研究更多關注企業微觀因素(如治理特征和財務特征等)對投資行為的影響,而較少從企業外部來考察企業投資行為的形成機制。本文將企業投資行為放到更廣闊的環境中進行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現實中公司的投資行為。第二,本文的實證研究證實,國有企業的高管權力越大反而會減弱過度投資。較之民營企業,國有企業的高管不僅受政府的監管更為嚴格,而且其更加關注政治升遷,所以權力較大的國企高管反而會主動降低過度投資行為。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
高管權力是指高管個人讓企業的戰略決策按照自己意愿方向發展的能力(Finkelstein,1992)。Hambrick和Mason(1984)指出,作為企業高管團隊的決定性成員,CEO 有權力和能力來做出對企業績效有最終影響的決定。根據委托代理理論,企業的管理者和股東之間存在典型的代理關系,管理層在決策時除考量企業發展外,也非常關心自身收入、社會地位和聲望。Rajan和Zingales(2001)認為,組織內部的權力配置關系重大,因為代理人擁有的權力越大,其獲得的“租金”就越多,而這反過來又會影響其激勵和決策。
大量研究表明,高管人員普遍偏好NPV 為負的投資項目,這樣能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使企業的投資決策行為無法與其個人能力分離,管理層為了建立被替代的保護機制將會進行過多投資(Shleifet and Vishny,1989)。代理理論預測,權力強大的高管有動機利用信息不對稱的有利條件和對董事會的影響,以犧牲股東的利益來擴大自己的財富(Morse,et al,2011),擴大投資對其而言是有利的選擇。眾多研究也已證實,經理人員的經濟收益與企業規模呈正比例函數關系(Conyon and Murphy,2000)。因此,在委托代理框架下,企業高管一般具有過度投資的意愿,通過控制更多的資源以獲取更大的私人利益,這種追求投資規模而非投資效益的特征被稱之為“經理帝國主義”(Jensen,1986)。此外,當CEO 較其他董事會成員擁有更多權力時,內外部董事的有效性將具有妥協性且企業績效會受到損害(Jiraporn,et al,2012;Liu and Jiraporn,2010),此時,CEO 較大的決策權力將有助于其進行過度投資以獲取個人經濟利益。所以,通常情況下,企業高管權力強度與過度投資正相關。
上述研究雖主要針對市場化經濟背景下的歐美企業,但其結論在相當程度上也適用于中國的民營企業,這是因為中國的民營企業一開始便面臨充分的市場化競爭。鑒于此,本文提出:
H1:在民營終極控制的企業中,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正相關。
然而,不同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不僅受市場的約束,而且還面臨更為嚴格的政治監管。首先,國有企業高管處于特有的政治背景下,其行政官員身份特征濃于職業經理人特征(Fan,et al,2007)。辛清泉等(2007)的研究表明,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員一般同政府官員保持著更為緊密的聯系,一方面,國企經營者會擔心因大量的過度投資導致業績過差,進而影響自身升遷;另一方面,政府也會顧慮因過度投資而造成國有上市公司股市融資能力的下降甚至是上市資格的喪失。因此,反映在國有企業高管的投資決策上,可能表現為對自身機會主義行為的自我節制,進而削弱代理問題導致的過度投資。其次,從政府管控角度出發,醋衛華和李培功(2012)進一步指出,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對高管的考核更加關注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等會計指標,并且其受到的監督更為嚴格,如來自審計署的審計等。通常,雖然國企高管權力大時很可能有過度投資的傾向,但是如果所選擇的投資項目不利于承擔社會性功能,政府將會采取強有力的監督措施加以嚴格篩選。
從法律層面來看,由于近年來國企高管濫用職權導致的惡果不斷浮現,中國政府于2003年制定并實施《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營決策行為禁令》,有針對性地制約擁有較高權力的高管的決策行為。從社會監督方面來看,由于國有企業承擔的社會性功能更大,國企高管通常備受社會輿論關注,特別是在當今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社會監督變得廣泛、及時且有效,企業的經理人傾向于選擇更加隱蔽的方式來獲取私有收益,如更加偏好在職消費而非過度投資(權小鋒和吳世農,2010)。辛清泉等(2007)也強調,國有企業經理人員在追求過度投資帶來的私人利益時,其也不得不承擔因股東利益受損而導致自身薪酬降低的后果,由此抑制了經理追求私人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因此,本文提出:
H2:在國有終極控制的企業中,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負相關。
(二)環境不確定性、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
關于不確定性與投資關系的主流研究普遍認為,當企業面臨環境不確定性條件時,決策會更加謹慎。根據投資的信息觀,Bernanke(1983)認為,不確定性增加了等待新信息的價值,只有當延緩項目投資的成本超過等待新信息的價值時,企業才會實施投資。Julio和Yook(2012)的研究發現,不確定性通常伴隨著未來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這會降低與投資相關的信息質量,增加外部融資成本,提高投資項目收益的未來不確定性,因而理性的管理層會延緩投資直至不確定性得以消除。Bloom等(2007)、Pasto和Veronesi(2012)構建的理論模型表明,在面臨不確定性時,企業的投資會更加謹慎,其通常會削減投資以應對這種不確定性。Yonce(2010)的研究表明,當企業的管理層擁有靈活選擇投資時機和投資規模的可能時,投資的門檻會隨著不確定性的增加而提高,即不確定性將對企業投資產生負面影響。Almeida等(2004)的研究發現,為了應對環境不確定性引發的突發事件,公司要平衡當前投資與未來支出,因此,更多的現金會被保留,經理人員將資金投資于凈現值為負的項目的行為也會得到抑制。總之,較高的環境不確定性將增加精確評估投資項目的難度,為盡可能避免投資失敗,管理層會更加謹慎地對待高風險項目。近期的一些文獻研究也提供了不確定性抑制企業投資支出的經驗證據(Juli and Yook,2012)。
Bloom等(2007)、Yonce(2010)認為,在未來環境處于不確定的情況下,對于企業尤其是處于弱勢地位的民營企業而言,延緩投資有助于其更好地了解和應對環境或政府政策的變化。由于實物投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因此這種不確定性會增加投資等待的價值,從而使得企業在是否投資的問題上變得更加謹慎。對于能夠自主選擇投資規模的民營企業來說,擁有較大權力的高管的理性選擇是延緩或減少投資。此外,不確定環境下,民營企業比國有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更為嚴重,這也會進一步降低高管過度投資的可能性;同時,投資失利還會給民營企業的高管帶來經營失敗的風險,影響其職業生涯,所以有權力的高管傾向于降低投資規模(申慧慧等,2012)。因此,本文提出:
H3:在民營企業中,環境不確定性會減弱高管權力引致的過度投資。
然而,外界環境不確定性的增加卻可能無助于減少國企的過度投資。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尤其當宏觀經濟低迷時,國有企業往往是政府推動投資的實施主體,各級政府為了實現穩定就業、增加稅收、提高GDP等目標,會引導國有企業進行投資。Xu等(2010)指出,當面臨極大的宏觀風險時,政府會讓國有控股企業增加投資水平以刺激經濟增長。從國企高管的角度而言,在環境不確定條件下,相比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經理人員更可能出于對自身能力或企業競爭力的過度自信而過度投資(Malmendier and Tate,2005)。同時,環境不確定性也會增加預測和監督管理層行為的難度,掩蓋國企管理層投資失敗時所需承擔的責任,因此,資金被用于謀取私人收益的無效率投資機會將顯著提升。Xu等(2010)的研究表明,與私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員確實擁有更多的機會將失敗的風險轉移至政府或者銀行。所以,相比民營企業,在復雜和動蕩的環境中,國企高管更容易轉嫁投資失敗的風險,擁有較大權力的高管反而會利用不確定性的環境進行過度投資以滿足私利。鑒于此,本文提出:
H4:在國有企業中,環境不確定性會加劇高管權力引致的過度投資。
三、實證設計
(一)樣本選擇
由于高管權力的一些重要信息(如高管在非股東單位的兼職信息)在2005年之后才公開披露,因此本文選擇2005—2012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在此基礎上剔除了金融行業以及數據缺失的公司。本文所使用的公司財務數據和公司治理數據主要來自CSMAR 數據庫,政治身份數據根據高管個人公開信息進行手工收集而得。在對各假設進行檢驗時,由于變量存在的信息缺失程度不同,因此不同模型中實際參與分析的樣本數略有不同,參與各模型回歸的具體樣本量在實證分析結果的表格中已詳細列出。
(二)變量設計
1.過度投資(OverInv)
本文借鑒Richardson(2006)的方法衡量過度投資,這是已有文獻最常用的方法。企業的投資支出(Inv)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與公司成長機會、融資約束、財務杠桿和行業等因素相關的正常投資支出;二是非預期的投資支出(Richardson,2006;Chen,et al,2011)。本文借鑒Richardson(2006)的公司投資模型,即模型(I),并根據該回歸模型的殘差數值判斷公司的投資效率情況,如果殘差為正,則認為公司存在投資過度(OverInv),否則為投資不足(UnderInv)。

其中,Invt代表公司第t年構建的固定資產、在建工程、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投資所支付的現金與平均總資產的比值;Growtht-1、Levt-1、Casht-1、Years_listedt-1、Sizet-1、Rett-1、Invt-1分別代表第t-1年公司的成長機會、資產負債率、現金持有量、上市年份、公司規模、股票收益率和投資支出。模型同時控制了年度和行業的影響。
模型(I)的準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公司成長機會Growth的判斷和預測。Richardson(2006)基于剩余收益框架,將市場價格信息與體現為賬面價值和目前盈余的公司資產價值指標綜合起來,構建了一個更為準確的成長機會指標。首先,假定公司價值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公司已有資產的價值VAIP和成長機會的價值VGO。因此,公司價值可表示為:

公司價值P是可以觀測的。然后,基于剩余收益框架估計VAIP。假定價格等于預期股利的折現,企業會計滿足凈盈余會計關系(Clean—Surplus Relation),即影響企業股票價值變動的因素全部反映在企業的損益表中。超額收益會遵循一個持續性參數為ω的自回歸過程,那么就可以把公司目前資產的價值VAIP表示為:

其中,BV 為普通權益的賬面價值;X 為扣除折舊后的經營收入;r是折現率;d是年度分紅;ω是固定的持續性參數,0<ω<1,并且a=ω/(1 +r-ω)VAIP。此時,VAIP反映了公司目前的賬面價值。這種估計方法同時捕捉了市場價值和公認的估值框架中的盈利,以此涵蓋會計和市場信息的成長機會,V/P 就可以表示為VAIP與市場價值之比,代替普通的托賓Q。本文借鑒Richardson(2006)對成長機會(V/P)的衡量方法,其中,α=ω/(1 +r-ω),r=12%,ω=0.62。
2.高管權力(Power)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有關高管權力的實證研究難于推進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高管權力難以衡量。Finkelstein(1992)提出的權力的四種類型為實證研究選擇適當的變量提供了思路。但是,目前相關文獻在高管權力指標的選擇上還存在一個突出問題,即混淆了權力本身和權力的約束機制。前者主要基于高管自身的特征選擇相關變量,如是否兼任董事長、在公司中的任職年限等;而后者則從對高管約束的角度選擇變量,如股權分散(Bebchuk and Fried,2002)、外部董事的比例等。由于高管權力具有非常強的內生性,因此,選擇權力約束變量直接作為權力指標并不合適。治理層面的權力約束機制并不能代表權力本身,這些約束機制需要我們通過實證研究檢驗其是否真正對高管權力發揮了作用。
Finkelstein(1992)完全從高管人員自身特征出發,將權力劃分為結構性權力、所有者權力、專家權力和聲望權力四個維度。本文在借鑒Finkelstein(1992)分類方法的基礎上,考慮到中國特有的制度環境和制度背景,將專家權力和聲望權力歸為聲譽權力,并且引入政治權力這一新的類型。參照Finkelstein(1992)和Eriksson(2005):在衡量結構性權力時,使用總經理的年齡(Age)、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Duality)和在本公司的職位數目(Numb_P)作為代理變量;在衡量聲譽權力時,使用總經理薪酬(Salary)、總經理在其他單位兼職的數量(Parttime)、總經理的任期(Tenure)和學歷(Education)作為代理變量;在衡量所有權權力時,使用總經理的持股數(Share_ceo)作為代理變量。對于政治權力的衡量,則參照田利輝和張偉(2013)、徐業坤等(2013),采用總經理是否是全國人大代表和政治委員(politics_state)、是否是省級人大代表和政治委員(politics_ prov)、是否是縣市級人大代表和政治委員(politics_city)作為代理變量。考慮到這些變量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將其合成為一個高管權力指標(Power)。具體的變量說明見表1。
3.環境不確定性(EU)
本文使用過去5年銷售收入的變異系數衡量環境不確定性。環境不確定性的根源存在于外部環境,而外部環境的變化將引起企業核心業務活動的波動,并最終導致銷售收入的波動(Bergh and Lawless,1998;Dess and Beard,1984)。因此,可以用公司業績波動衡量環境不確定性(Cheng and Kesner,1997;Habib,et al,2011)。在實證研究中,衡量環境不確定的指標最常使用公司銷售收入的標準差,為剔除行業的影響,Ghosh和Olsen(2009)運用過去5年銷售收入的標準差并經行業調整后的值來衡量公司的環境不確定性。然而,考慮到過去5年銷售收入的變化,其中一部分是公司的穩定成長所帶來的,因此,為了更加準確地衡量環境不確定性,還需要剔除銷售收入中穩定成長的部分,即每個公司運用過去5年的數據,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運行模型(II),分別估計過去5年的非正常銷售收入:

其中,Sale 為銷售收入;Year 為年度變量(如果觀測值是過去第4年的,則Year =1;如果觀測值是過去第3年的,則Year=2;依次類推,如果觀測值是當前年度的,則Year =5)。模型(II)的殘差即為非正常銷售收入。在此基礎上,計算公司過去5年非正常銷售收入的標準差,再除以過去5年銷售收入的平均值,從而得到未經行業調整的環境不確定性;同一年度同一行業內所有公司的未經行業調整的環境不確定性的中位數,即為行業環境不確定性。最后采用Ghosh和Olsen(2009)的方法,用各公司未經行業調整的環境不確定性除以行業環境不確定性,即為公司經行業調整后的環境不確定性,也就是本文所運用的環境不確定性(EU)。
(三)計量模型與研究方法
為去除潛在的由于個體效果引起的內生性問題,本文使用系統GMM方法分析高管權力對過度投資的影響。同時,按照Arellano和Bond(1991)的建議,使用一階段估計結果進行系數顯著性的統計推斷,采用兩階段估計給出的Sargan統計量進行模型篩選。另外,自由現金流和負債水平可能會對公司的投資狀況產生動態影響,即上一年度的自由現金流和負債比例可能會影響到本年度的投資狀況,因此,在進行系統GMM估計時,將這兩個變量作為內生變量處理。
同時,考慮到高管權力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可能是非線性的(McNichols and Stubben,2008),因此,在估計模型中加入兩個刻畫高管權力水平的虛擬變量,PowerH(當高管權力位于同年度同行業按降序排名的前1/3的位置時取值為1,否則為0)和PowerL(當高管權力位于同年度同行業按降序排名的后1/3的位置時取值為1,否則為0),以控制高管權力對企業投資效率的非線性影響。
對研究假設的具體檢驗方法是:首先,根據公司的具體情況,將過度投資樣本分為國有終極控股與民營終極控股兩個組;然后,使用下面的計量模型對存在過度投資的兩組樣本分別進行回歸;最后,通過考察主效應項的回歸系數檢驗假設是否得到證實。
使用模型(III)對H1 進行檢驗:

如果在民營企業過度投資樣本中,模型(III)中β2的估計值為正且在統計上顯著,則H1 得到證實;如果在國有企業過度投資樣本中,β2的估計值為負且在統計上顯著,則H2 得到證實。
對H3和H4 進行檢驗的模型為方程(IV)。該模型是在控制不同公司類型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影響基礎上,進一步檢驗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

如果在民營企業過度投資樣本中,模型(IV)中β4的估計值顯著為負,則H3 得到證實;如果在國有企業過度投資樣本中,模型(IV)中β4顯著為正,則H4 得到證實。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列示了各組樣本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最終控制人產權性質分組的結果可以看出,國有上市公司的高管權力平均水平為-0.011,低于民營企業的0.006,且二者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在存在過度投資的樣本中,國有、民營企業的過度投資水平無顯著差異,均值分別為0.09和0.086。從全樣本來看,環境不確定性的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1.046和8.64,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275.6和-620.4,說明不同公司環境不確定性變化差異很大,而且民營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程度顯著高于國有企業。
(二)回歸分析
1.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
對“過度投資(OverInv)”衡量的準確性除了取決于公司成長機會(Growth)的衡量,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企業現金持有量(Cash)的衡量。因此,為了檢驗模型的穩健性,表3中模型(1)-(3)在計算過度投資時使用資產負債表上的貨幣資金(Cash_1)代表現金持有量,而模型(4)-(6)則使用現金流量表上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Cash_2)代表現金持有量。從模型(1)可以看出,盡管對于全樣本而言,高管權力強度與過度投資之間并不存在顯著關系,但是進行國有和民營分類以后,模型(2)和(3)的結果表明,在這兩類企業中高管權力對投資行為有著不同影響。從模型(3)可以看出,民營企業中的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正相關,并在1%的置信水平顯著,結果支持H1,代理理論及經濟人假設等很好地解釋了民營企業高管的投資行為。但是在國有企業中,由于嚴格監督和政治升遷帶來的自律等因素,導致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負相關,并在1%的置信水平顯著,H2 得到證實。模型(4)、(5)和(6)在衡量過度投資時使用Cash_2 表示經營活動現金流,回歸結果基本不變。

表2 不同樣本組中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3 高管權力對過度投資程度影響的計量分析結果
2.環境不確定性、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
表4中,在衡量過度投資時同樣分別使用Cash_1和Cash_2 表示現金持有量。模型(1)的主效應項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的關系與表3 具有相同的結果;按照國有和民營進行分類以后,模型(2)和(3)的結果表明,在這兩類企業中環境不確定性與高管權力對投資行為存在不同影響。由模型(3)可見,民營企業環境不確定性與高管權力的交互項(EU* Power)與過度投資負相關,且在1%水平上顯著,這一檢驗結果很好地支持了H3,表明純粹經濟市場中,不確定性帶來的失敗風險增大以及信息不足等因素導致管理者投資謹慎的結論恰當地解釋了不確定性環境下高管的投資行為。而對于模型(2),雖然國有企業組在用Cash_1 表示現金持有量來計算過度投資的情況下,交互項(EU* Power)與過度正相關但不顯著;但是,使用Cash_2表示現金持有量來衡量過度投資時,交互項(EU* Power)與過度投資正相關,且在10%水平上顯著,因此,H4 得到證實。不確定環境下國有企業“援助之手”的扶持,經濟低迷時政府干預刺激經濟增長以及高管轉嫁責任的低成本、信息資源的優勢、外界對管理層行為預測和監督的難度等證據很好地闡釋了國有企業高管的投資行為。

表4 環境不確定性對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關系調節效應的計量分析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從投資效率估計模型的內在特征和主要變量測量偏誤兩個角度,考察它們可能對高管權力與企業投資效率之間關系的影響,從而檢驗本文結論的穩健性。具體如下:
1.考慮投資估計模型自身系統性偏差的影響
Richardson(2006)的估計新投資水平模型的一個假設條件是,上市公司整體不存在系統性的投資過度或投資不足現象。但是對于那些回歸殘差在0 附近的公司而言,由于模型偏誤所導致的系統性偏差會比較嚴重。為檢驗這種偏差是否會影響高管權力對投資效率的影響,借鑒已有學者的處理方法,如:陳運森和謝德仁(2011)把投資過度組和投資不足組分別分成10個組,剔除殘差離0 最近的兩個組,以考慮模型設置本身的偏誤可能帶來的影響;辛清泉等(2007)先是將模型的殘差按大小等分成三組并剔除掉中間一組,然后,將殘差最大的一組作為投資過度組,將殘差最小的一組作為投資不足組。本文按5%和2%兩種不同的方法,對回歸殘差位于0 附近的樣本進行刪除,然后重新檢驗假設。從回歸結果來看,與前文結論無實質差異。
2.考慮主要變量測量偏誤的影響
對于本研究涉及的部分變量,存在不同的衡量方式。鑒于此,本文使用不考慮現金紅利再投資的股票回報替代考慮現金紅利再投資股票回報;使用14%代替12%作為公司的折現率,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結論也沒有發生實質變化。
總體而言,本研究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五、結論及研究展望
本文以2005—2012年中國滬、深兩市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考察在不確定環境下上市公司高管權力對企業過度投資的影響。結果表明,高管權力的綜合指標對企業過度投資的影響與企業終極控制人的性質有顯著關系:在國有終極控制的企業中高管權力會削弱過度投資;而在民營終極控制的企業中,高管權力則會增加過度投資程度。國有終極控制企業的實證結果單純用委托代理理論是難以解釋的,原因之一是國有企業特有的政治背景使得影響其高管投資決策的機制更加復雜,國企高管除了追求經濟利益外更關注自身的政治前途,反映在行動上,則可能表現為對機會主義行為的自我節制。其次,由于承擔著更大的社會性功能,國企高管面臨的社會輿論壓力也更大,其在利用權力獲取私有收益時會更加隱蔽。
本文用銷售收入變化的變異系數值來測度環境不確定性,并對環境不確定性、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環境不確定性對高管權力與過度投資關系的調節效應也與企業終極控制人的性質有顯著關系:在國有企業中,環境不確定性會加劇高管權力引致的過度投資;在民營企業中,環境不確定性會減弱高管權力引致的過度投資。
本文未來可以改進之處在于:第一,由于中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股份公司存在著復雜的股權結構。不同類型的控制權對應著不同的權益主體,而不同權益主體又存在不同的行為特征。由于股權結構對經理的行為有著重大影響,不同的股東類型對公司過度投資的影響也就不同,未來應進一步細化國有企業的性質(中央控股、省級控股和地市級控股),以豐富這一主題的理論研究。第二,高管權力的測量指標十分廣泛,未來需要進一步細化高管權力,考察不同類型的權力對投資決策的影響,這有助于對比不同的結論,更為深入地了解不同類型高管權力所發揮的作用。
陳運森,謝德仁.2011.網絡位置、獨立董事治理與投資效率[J].管理世界(7):113-127.
醋衛華,李培功.2012.媒體監督公司治理的實證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1):33-42.
戴德明,王小鵬.2011.所得稅、自由現金流與過度投資:來自中國2008年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財貿研究(1):119-126.
李焰,秦義虎,張肖飛.2011.企業產權、管理者背景特征與投資效率[J].管理世界(1):135-144.
權小鋒,吳世農.2010.CEO 權力強度、信息披露質量與公司業績的波動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4):142-153.
申慧慧,于鵬,吳聯生.2012.國有股權、環境不確定性與投資效率[J].經濟研究(7):113-126.
唐雪松,周曉蘇,馬如靜.2010.政府干預、GDP增長與地方國企過度投資[J].金融研究(8):33-48.
田利輝,張偉.2013.政治關聯影響我國上市公司長期績效的三大效應[J].經濟研究(11):71-86.
辛清泉,林斌,王彥超.2007.政府控制、經理薪酬與資本投資[J].經濟研究(8):110-122.
徐業坤,錢先航,李維安.2013.政治不確定性、政治關聯與民營企業投資:來自市委書記更替的證據[J].管理世界(5):116-130.
楊華軍,胡奕明.2007.制度環境與自由現金流的過度投資[J].管理世界(9):99-106.
張敏,于富生,張勝.2009.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投資異化研究綜述[J].財貿研究(5):134-140.
張兆國,劉亞偉,亓小林.2013.管理者背景特征、晉升激勵與過度投資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4):32-42.
BEBCHUK L A,FRIED J M.2002.Pay without performance: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RGH D D,LAWLESS M W.1998.Portfolio restructuring and limits to hierarchical governance: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J].Organization Science,9(1):87-102.
BERNANKE B S.1983.Irreversibility,uncertainty and cyclical invest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l):85-106.
BERTRAND M,MULLAINATHAN S.2003.Enjoying the quiet lif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rial preferenc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11(5):1043-1075.
BLOOM N,BOND S,VAN REENEN J.2007.Uncertainty and investment dynamic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4(2):391-415.
BROWN R,SARMA N.2007.CEO overconfidence,CEO dominance and corporate acquisitions[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59(5):358-379.
CHEN F,HOPE O K,LI Q Y,et al.2011.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private firms in emerging markets[J].Accounting Review,86(4):1255-1288.
CHENG J L C,KESNER I F.1997.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shifts:the impac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patterns[J].Journal of Management,23(1):1-18.
COASE R.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4(16):386-405.
CONYON M,MURPHY K.2000.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CEO pay in the U.S.and the U.K[J].The Economic Journal,110(467):640-671.
DESS G,BEARD D.1984.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task environment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9(1):52-73.
ERIKSSON T.2005.The managerial power impact on compensation:some further evidence[J].Corporate Ownership & Control,2(3):87-93.
FAN J P H,WONG T J,ZHANG T Y.2007.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84(2):330-357.
FINKELSTEIN S.1992.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dimensions,measurement,and validation[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5(3):505-538.
GHOSH D,OLSEN L.2009.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managers use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ccounting[J].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34(2):188-205.
HABIB A,HOSSAIN M,JIANG H Y.2011.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pricing of earnings smoothness[J].Advances in Accounting,27(2):256-265.
HAMBRICK D C,MASON P A.1984.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9(2):193-206.
HUANG J,KISGEN D J.2013.Gender and corporate finance:are male executives overconfident relative to female executiv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08(3):822-839.
JENSEN M C.1986.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6(2):323-329.
JIRAPORN P,CHINTRAKARN P,LIU Y X.2012.Capital structure,CEO dominance,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42(3):139-158.
JULIO B,YOOK Y.2012.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cycles[J].Journal of Finance,67(1):45-83.
LIU Y,JIRAPORN P.2010.The effect of CEO power on bond ratings and yields[J].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17(4):744-762.
MALMENDIER U,TATE G.2005.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Journal of Finance,60(6):2661-2700.
MCNICHOLS M F,STUBBEN S R.2008.Does earnings management affect firms' investment decisions[J].Accounting Review,83(6):1571-1603.
MORSE A,NANDA V,SERU A.2011.Are incentive contracts rigged by powerful CEOs[J].Journal of Finance,66(5):1779-1821.
PASTOR L,VERONESI P.2012.Uncertainty about government policy and stock prices[J].Journal of Finance,67(4):1219-1264.
RAJAN R,ZINGALES L.2001.The tyranny of inequalit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76(3):521-558.
RICHARDSON S.2006.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11(2/3):159-189.
SHLEIFER A,VISHNY R W.1989.Management entrenchment:the case of manager-specific investment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5(1):123-139.
WIERSEMA M F,ZHANG Y.2011.CEO dismissal:the role of investment analyst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32(11):1161-1182.
XU L,WANG J,XIN Y.2010.Government control,uncertainty,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China's listed companies[J].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3(1):13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