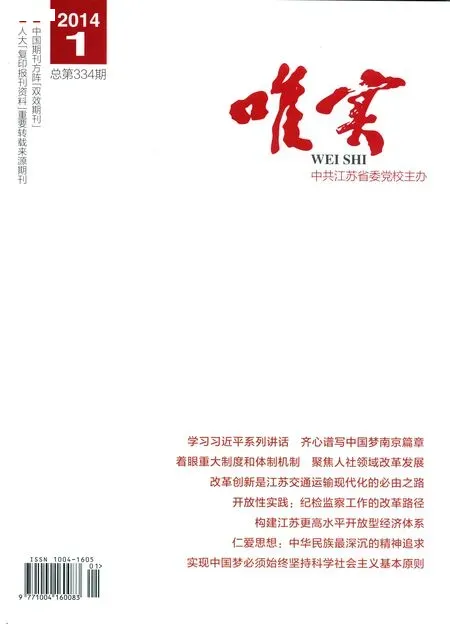東北亞地緣政治環境特點及中國應對
黃鳳志+武星
東北亞是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依托地區,東北亞海域是中國崛起走向世界的戰略通道,也是中國與美日等國交往的地緣政治互動的前沿空間,中美日地緣政治空間的折沖匯聚在此。而冷戰遺留未決問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走向前景問題、中日戰略抗衡問題凝聚了具有“火藥桶”意蘊的“朝核問題”、“釣魚島問題”,使得2014年東北亞政治與安全形勢仍將運行在安全困境“無解”的時空。
一、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與東北亞地緣政治困境
中美兩國位于地球東西兩端,中國是東北亞地區大國,美國是北美地區乃至世界大國,兩國存在著文明、發展、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美國依托自身超強國力和美日、美韓聯盟在東北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中國發展受到美國的多方掣肘,中美關系存在著霸權國與崛起國的競合要素,世界歷史上霸權國與崛起國殘酷競爭的案例,啟迪著中國努力走和平發展道路,在中美關系問題上致力于建構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2013年,中美國家元首兩次會晤,拜登副總統一次訪華,中美兩國進行了第五輪戰略與經濟對話,舉行了第四輪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兩國投資協定談判進入實質性討論階段。中美兩國進行了新興國家與霸權國家建構新型關系的嘗試,力圖走出二者由競爭走向對抗與沖突的歷史宿命。
中美關系發展的“過去時”與“進行時”主導方是美國,奧巴馬政府在處理當前中美關系問題時無疑擁有比中國更多的資源、手段和主動權,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有多重戰略目標:既有分享亞太地區新興國家經濟崛起成果的意圖,也有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應對中國崛起挑戰的動機,更有利用東亞地緣政治環境新變化實現鞏固盟友關系、擴大伙伴隊伍、確保其在亞太地區主導地位的目標,同時也含有封堵中國崛起地緣政治空間的意蘊。奧巴馬政府多次強調亞太再平衡戰略不指向中國,但美國欲將海空軍力的60%部署在亞太,越來越多的軍艦和飛機部署在中國周邊海域。中國凡與周邊國家出現任何領土爭端和利益矛盾,美國都做出了指責和不利于中國的立場選擇。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長,美國的感受如芒刺在背,視若挑戰和威脅。美國事實上扮演了遏制中國的幕后推手,日本、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充當了“角斗士”,美國的全球盟友則扮演了推波助瀾角色,在釣魚島爭端、南海爭端、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設立等問題上,西方輿論集體鼓噪,將中國護持國家主權的合理訴求抹黑為咄咄逼人的“強硬”者和“在海上伸展肌肉”等,美國幕后遙控將中國置于海疆爭端困局。事實上,中國周邊鬧海的震源來自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的戰略意圖是利用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恐懼來實現孤立和制衡中國的目標。
然而,隨著中國實力的發展,特別是中國軍事實力的增強,美國對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訴求正在呈現出緩慢與無奈接受的趨向。美國維系超強軍事強國的努力明顯受制于經濟發展緩慢和國家財政困難,隨著中美經濟實力的接近,兩國曾經嚴重失衡的軍事力量對比關系必將逐漸發生變化,美中關系格局美強中弱的權力失衡現象也將緩慢改變,中國擁有和平發展強盛國家的前景與希望。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面臨中國日益強大、中俄戰略協作(“權宜軸心”)和“增加軍費而不令國家破產”的三重挑戰。
中國和平發展戰略與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對沖將中美關系推向困境式新型大國關系。從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角色與戰略選擇的視角看,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國家,爭取和平發展機遇期是其外交戰略的重要任務。中國和平發展的基本國策要求其“對內求發展、求和諧,對外求合作、求和平”。“同發達國家加強戰略對話,增進戰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探索建立和發展新型大國關系,推動相互關系長期穩定健康發展。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友好的方針,發展同周邊國家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積極開展雙邊和區域合作,共同營造和平穩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地區環境。”[1]
中美關系在當代國際體系中雖然存在著崛起國與霸權國的矛盾,但中國和平發展的外交戰略目標規制了中國不會與美國爭奪亞太地區主導權。中美關系惡性競爭與對抗帶來兩敗俱傷的“雙輸”前景也將制約雙方進行零和博弈的政策選擇。兩國具有通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方式維系維護中美關系總體穩定的空間,“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中國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實力地位和發展潛能(英國智庫預測2022年中國經濟規模將可能增至美國GDP的83%)、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政治地位、在東亞地區的地緣優勢地位、多年來與亞太國家形成的貿易關系等,中國通過與亞太國家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和平發展效應惠及周邊國家,改善和深化周邊關系,化解崛起危機,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圍堵中國意圖將形成有力掣肘。中國應以自信心態歡迎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繁榮發揮作用,敦促美國尊重亞太各國國家利益與安全關切,以實力平衡美國刻意加強軍事部署、強化軍事同盟的不良用意。
二、中日政治、安全與外交抗衡關系的浮現
2013年東北亞地緣政治困境凸顯為中日關系困境,兩國戰略互惠關系已經名存實亡,代之而起的是中日戰略抗衡關系浮現。
安倍晉三再次當選日本首相后,不僅在釣魚島爭端中堅持對華強硬立場,導致釣魚島爭端持續、深度發酵,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也已不僅限于借助炒作“中國威脅論”來實現政治軍事大國抱負,而是傾向于視中國為戰略敵手。
首先,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安倍政府始終拒不承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聲稱在釣魚島問題上沒有談判余地,完全違背了當年與中國達成的擱置爭議這一重要共識和諒解默契,直接導致中日雙方政府高層交往陷入中斷,兩國民間對立情緒持續升溫,日本的購島行徑打開了中日關系走向惡化與抗衡的“潘多拉魔盒”。
其次,在釣魚島危機的處理方式上,中國堅持派遣公務船和公務飛機在釣魚島海域和空域進行“常態化”維權巡航執法行動,日本在應對中方的維權反制行動時,刻意突出軍事色彩,制造緊張氣氛,推動危機不斷升級。從2013年初宣稱對進入釣魚島空域的中國飛機使用曳光彈進行警告射擊,到炒作所謂的“火控雷達照射”和海監船機槍“瞄準”日方船只事件,再從日本首相批準對侵犯其領空的無人機采取包括擊落方式在內的強制措施,到日本艦機強行闖入中國軍事演習區事件,日本上述行為導致中日摩擦升級為軍事沖突的可能性變得越發現實。日本還大力發展軍備,強化軍事部署,以增強對釣魚島的控制和防衛能力。包括在釣魚島附近的與那國島部署監視部隊,在沖繩那霸基地部署E-2C偵察機,以增強對釣魚島的情報收集能力;籌建海軍陸戰隊,研發射程在400~500公里的短程彈道導彈用于釣魚島防衛,以提高快速部署能力;通過裝備的更新升級,提升防空能力;并動員陸海空自衛隊實施聯合演習,以增強“奪島”和“守島”的實戰能力。
第三,中日在釣魚島危機中的分歧面繼續擴大,已從海域拓展至空域,衍生出東海防空識別區問題。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符合中國《國防法》、《民用航空法》、《飛行基本規則》等國內法,也符合《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而日本則借題發揮,制造事端,挑釁中國。安倍就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涵蓋釣魚島表示,“這如同宣示尖閣諸島領空就是中國領空,完全不能接受”,并稱“正在要求中國撤銷一切措施”。日本參眾兩院也通過決議對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表示嚴正抗議。中日兩國防空識別區存在重疊,對于重疊空域內的飛行安全問題,中國表示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就有關技術問題與日方進行溝通,共同維護有關空域的飛行秩序和安全。而日本外相則稱,中國劃設涵蓋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的東海防空識別區“是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做法,是對飛行自由的侵害。日本不會考慮開展以此為前提的對話”。防空識別區問題上的爭議導致中日間的緊張繼續升溫。
第四,日本為謀求其在釣魚島爭端中的戰略優勢,在地區和國際層面對中國開展制衡,以爭取在釣魚島爭端中對中國形成牽制。日本希望借助美日同盟的力量,利用美國對其在釣魚島行政管轄權的支持,以及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的承諾,積極拉攏美國共同對中國施壓。安倍政府還在地區和國際上針對中國拉幫結派,挑釁滋事。就中國劃設防空識別區,安倍在日本東盟特別峰會上公開表示,中國欲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動以及限制國際航空秩序的行為十分令人擔憂,呼吁東盟各國對日本立場給予認同和理解,甚至提議在聯合聲明中將其寫入并稱之為安保上的“威脅”。
第五,在外交方面,安倍提出開展“戰略性外交”、“重視普遍價值的外交”以及維護國家利益的“主張型外交”,“戰略”、“價值觀”及“維護國家利益”這三個關鍵詞透漏出其針對中國的戰略意圖。具體來講,一是以日美同盟為基軸,拓展美日印、美日澳及美日澳印的多邊安全合作,試圖構建由美日澳印組成的遏制中國的“民主安全菱形”。安倍認為“世界最大的海洋國家美國與亞洲最大的海洋民主國家日本成為伙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進一步強化日美同盟的基軸,這應在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中最為優先”。為此,安倍政府著力修復美日同盟關系,推進普天間機場的遷移及嘉手納以南土地的歸還計劃,為駐日美軍重組掃清障礙,同時還加入了美國主導的TPP談判。在鞏固日美同盟的基礎上,安倍試圖推進與印度、澳大利亞的戰略關系,加強在海洋安全問題上的合作,擠壓中國的戰略空間。
近年東北亞政治與安全局勢的顯著特點是中日關系困境,隨著安倍政府推行日益強硬的對華政策和中國維護國家主權的應對政策,兩國戰略互惠日益消亡,戰略抗衡關系逐漸浮現,東北亞地緣政治困境舉世矚目,管控中日關系危機成為當務之急。
三、朝核問題與東北亞安全困境
朝鮮半島位于東北亞地緣政治的核心地帶。半個多世紀以來,大國戰略與利益的博弈建構了朝鮮半島問題,使其始終是東北亞地緣政治與安全困境的發酵場,亞洲的巴爾干火藥桶。朝鮮半島是大國戰略與利益的博弈場、平衡點,必然要催生出朝鮮半島問題,朝鮮半島問題集中表現為朝鮮時局問題(朝鮮對外政策走向)、朝核問題和朝韓對峙問題等。
朝鮮半島的核心問題是弱勢方朝鮮地處東北亞地緣政治博弈點敵強友寡,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平與發展時代主旋律中落伍于全球政治思潮與政治實踐變革的浪潮,國際政治處境孤立。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和家族世襲制的領導體制,使其內以先軍政治、外以擁核戰略立威強國。家族世襲統治和擁核戰略是朝鮮問題的主要特征。家族世襲統治使朝鮮無法走向改革開放道路,把握時代發展脈搏,融入國際社會,進而成為現代化國家。擁核戰略加劇了東北亞安全困境。2013年朝鮮半島問題集中表現為朝核問題。當年2月12日,朝鮮中央通訊社宣布朝鮮當天成功進行第三次地下核試驗。隨后,朝鮮采取了一系列危機邊緣政策,美韓兩國也因此強化了安全合作,提升了對朝威懾力,導致朝鮮半島局勢不斷升級,新一輪朝核危機再次爆發。朝鮮擁核戰略的意圖主要來自于朝鮮“主體思想”、“先軍政治”,也源于對現實區域環境的認知所產生的對國家安全上的疑慮,冷戰后,薩達姆政權和卡扎菲政權的覆沒及其悲慘結局進一步堅定了朝鮮擁核的決心。朝鮮擁核戰略是實現國家政治與安全戰略的一種手段,旨在通過擁核實現保障朝鮮的政治體制和國家安全,以擁核事實脅迫國際社會接受現實,最終達到解除制裁、實現“強盛大國”的戰略目標。然而,朝鮮堅持擁核戰略惡化了自身生存環境,加深了在國際社會的孤立處境,加劇了東北亞安全困境,催生了周邊各國對擁核朝鮮的反對舉措。
朝鮮擁核戰略對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環境提出了重大挑戰。朝鮮第三次核試驗場距中國邊境僅98公里,新投入使用的導彈發射基地距丹東市48公里。一旦朝鮮核試驗或導彈發射出現事故,地下水、地面土壤、空氣都將被污染,中國鄰近地區也會受波及。中國始終堅持使用和平方式處理朝核問題,以維護東北亞地區和平與穩定。朝鮮高調擁核打破了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局面,勢必會帶來擁核的“多米諾”效應,引起東北亞其他國家以安全為借口開發核武器。新一輪軍備競賽將會在中國周邊展開,為緊張的東北亞局勢雪上加霜。朝核危機加劇了半島緊張局勢,直接威脅了中國和平發展的國家利益,迫使中國做出戰略應對。
近年東北亞地緣政治環境的新變化是中國和平崛起進程中出現的地緣政治均勢效應作祟。中國崛起無論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還是對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都產生了重大影響,21世紀初的中國已經“站在世界聚光燈”下,成為國際體系結構演進和東北亞格局結構變遷的推動力量,中國崛起催生了他國聯美抑華平衡中國的戰略訴求,塑造了中國崛起背景下東北亞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與困境。東北亞地區各種力量都在對地緣政治環境與力量結構的變化做出反應: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是美國對中國和亞太地區新興國家崛起應對戰略,其強化美日、美韓同盟則直接劍指中國崛起,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不斷強化有防御美國“東方版北約”的意蘊,中日戰略互惠名存實亡代之而興的是兩國戰略抗衡(釣魚島爭端是導火索)。
為了在東北亞地區實現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目標,中國應堅定不移地推進和發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把深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作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優先方向,中俄關系和平友好是中國東北亞地緣政治環境穩定的基石。深化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中國東北亞地緣政治環境穩定的保障,通過提升中美戰略對話、增加中美戰略互信、減少中美戰略互疑、發展中美戰略互惠的途徑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關鍵是兩國“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贏”。我們應將中美關系建立在務實合作和利益紐帶的堅實基礎上,超越兩國間存在的分歧,實現相互尊重與包容。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要求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發展中韓、中朝友好關系,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與無核,對于東北亞地區各國和平、繁榮、共贏意義重大,朝鮮無核化是東北亞地區和平的需要,擁核朝鮮不符合東北亞地區各國安全利益,深化中朝友好合作關系的前提是朝鮮棄核。中韓經濟合作基礎堅實,發展中韓友好合作關系有益于雙方在東北亞地區的安全環境,節制日本安倍政府的右翼化和軍事化走向。中日關系危機和戰略抗衡關系的發展要求兩國強化危機管控能力,把握中日關系大局走向,避免對抗局勢失控引發戰爭風險。
參考文獻:
[1]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201109/t1000032.htm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東北亞地緣政治局勢新變化與中國的戰略應對研究”(13AGJ003)成果〕
(黃鳳志: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星: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黃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