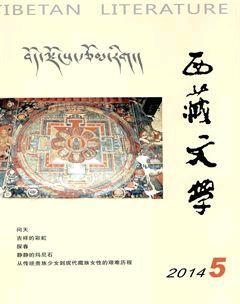向生命作證
2015-01-27 08:39:09唐翰存
西藏文學
2014年5期
唐翰存
我對散文詩的最初印象,來自于魯迅的《野草》。那種幽微之美,那種陌生化表現,那種語詞的精粹,使它成為我的枕邊之書,常讀常新。魅力不減。《野草》是很內向的文字,以“獨語”的方式,隱現了作者的生命哲學。作為中國散文詩這一文體的開創者,魯迅給后來者以諸多啟發,可惜至今無有超越者。魯迅本人在散文詩方面的成就,也超越了他在新詩上的成就。他的新詩,語多拗口,有時打油的意味重,與同時期一些優秀詩人相比,藝術上不很成熟。可是,一旦他轉化形式,將散文的因素引進詩歌里,就生質變,讓人仰慕不已。這個現象,是值得研究的。
當代散文詩里也許不乏佳作,可惜甚少,大多平庸泛泛。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喜歡翻閱印刷精美的《散文詩》雜志,后來再也不看了。原因在于,那上面發表的作品,大多華而不實,唯美則唯美,可那種唯美的語言背后,實則沒有什么內容,實則是蒼白和空洞。可以不客氣地說,散文詩在當代,已經完全淪落為一種“花瓶”。偶爾賞玩一下,覺得愉悅,看的時間長了,難免心生厭煩。
就在這個花瓶即將在我心目中破碎的時候,真是無獨有偶,甘南青年詩人王小忠寄來幾本新出的書,其中有他的兩本詩集,還有一本,是他們合出的散文詩集《六個人的青藏》。這本綠皮小書,在我書桌上輾轉了近一年,有時也徘徊到床邊,睡前翻讀一二。盡管看了這本書我心生歡喜,可我懶散,還時常不忘提醒自己,要冷靜、低調,我不能因為這么一本書,就輕易改變我對當今散文詩的看法。……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