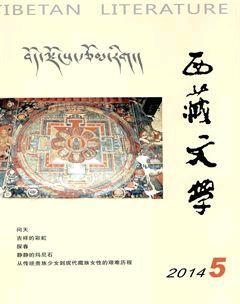回歸:洼西文學創作的一種傾向
2015-01-27 08:37:33馬傳江朱霞
西藏文學
2014年5期
馬傳江 朱霞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四川藏族作家洼西彭錯的《雪崩》等作品,歸納出其文學創作的一種傾向:回歸。這種回歸,體現在敘述上,是向故事回歸;體現在修辭上,則是以互文的手法回歸世界豐饒的本相;在精神指向上,則體現為其向“家園”回歸的努力。
【關鍵詞】回歸;故事;互文性;家園
“講故事的藝術行將消亡”,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里不無留戀地哀嘆。在網絡不斷滲入生活,面對面的交流經驗被日益剝奪的當下,我們聽到好故事的機會越來越少。那些故事總是長著相似的面孔,以難以辨認的模樣佇立在我們的閱讀經驗中。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四川藏族作家洼西彭錯的作品顯得別有意義。
一敘述:回歸故事
《鄉城》是洼西彭錯近幾年發表的小說,散文等作品的結集,我們重點說小說。洼西彭錯的小說,重新將關注的焦點投射向故事本體。花樣翻新的敘述手段,相較于故事本身的跌宕起伏而言,他選擇后者。如此一來,他的小說敘事便體現出以下幾個特征:
1、底本時間的長度增加。底本時間與述本時問,是四川大學著名學者趙毅衡先生提出來的概念吲。大略相當于我們平時所說的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在當代中短篇小說中,由于寫作者對于生活片段的愈加重視,小說對于生活橫截面的書寫愈來愈多,相應地,就導致小說底本時間在不斷縮減,在極致之處,幾秒鐘發生的故事也可能構成一部中篇小說的描述對象,西方意識流小說可以推為代表。……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英語文摘(2022年9期)2022-10-26 06:58:32
音樂教育與創作(2022年6期)2022-10-11 01:15:22
少兒美術(2021年4期)2021-04-26 13:45:40
人民周刊(2016年15期)2016-09-28 09:2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