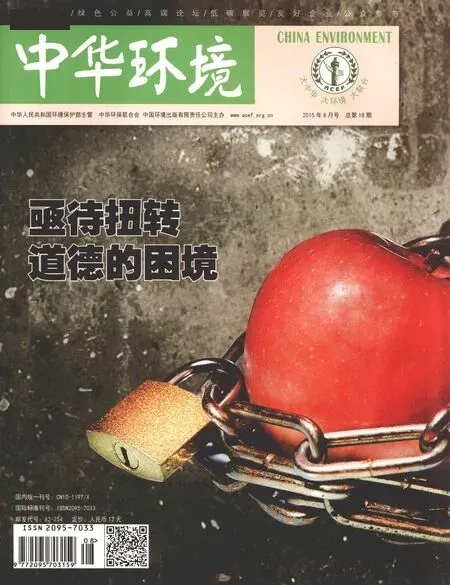道德的生態化
楊朝霞 張忠利
(楊朝霞,北京林業大學生態法研究中心;張忠利,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據統計,自1993年以來,我國共發生3萬多起突發環境事件,而重、特大突發環境事件則達到了1000多起。與此同時,環境群體性事件也與日增多,躍升至各類全國群體性事件的第九位。
從表面上看,這一系列環境污染事件和環境群體性事件之所以頻頻爆發,是由于部分政府部門決策不當和執法不力、企業環境守法意識不強和生產經營行為不法、公眾環保認知不深和參與無序等原因造成的,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各類社會主體的環境道德缺失。
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謂環境道德,是指基于對環境污染、資源短缺和生態退化三重危機的反思,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相對決定的,以善惡為評價標準并依靠人們的內心信念、社會輿論和傳統習慣維持的,為了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所有以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為價值取向的道德觀念、原則和規范,是對傳統道德的精髓繼承和生態化發展。
事實上,我國古代就有樸素的環境道德意識。譬如,白居易在《鳥》中就寫道:“誰道群生性命微, 一般骨肉一般皮。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在當前形勢下,大力推動環境道德建設,意義更為重大而深遠。
首先,加強環境道德建設,是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實現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體現。正如孟子所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道德與法律不可偏廢。
其次,加強環境道德建設,也是培育生態文化,建設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環境道德是生態文化的核心內容。對于個人而言,環境道德是其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內心信念,是指導和規范其從事開發、利用、適應、保護和改善自然等各類活動的內在“法律”,相對于國家立法機關依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而言,這種內在的“法律”憑借守法主體對生態環境的尊重和敬畏往往能夠得到更加有效、主動和徹底地遵守和執行。因此,培育環境道德,發展生態文化,對于切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而言彌足重要。正所謂“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路漫漫其修遠,篤定目標上下而求索
如何才能培養良好的環境道德,運用環境道德觀的養成來促成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的實現呢?
首先,制定專門的《環境教育法》,將環境道德教育作為環境教育、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通過環境道德的法律化,逐步在全社會確立環境道德觀。事實上,早在2004年,國家林業局就發布了《關于加強未成年人生態道德教育的實施意見》,其目的就是使未成年人從小就樹立環境道德觀,使環境道德的理念和規范融入未成年人的心靈。我們認為,環境道德教育固然需要從娃娃抓起,但也不應忽視對其他社會群體的教育,特別是要加強對公務人員和企業高管的教育。
當前,國家應進一步提高對環境道德教育的重視程度,借助每年3月22日世界水日、5月22日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和6月5日世界環境日等時機大力開展環境道德教育活動。正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只有堅持不懈、日積月累,才能一步一步實現全社會道德評價體系的生態化,最終真正在全社會形成保護環境、節約資源和善待生命的道德風尚。
其次,加強對黨政官員和企業管理層的環境道德教育,實現政府公共決策和公司經營管理的生態化,推動環境監管者和生產經營者自覺履行法定職責和義務。
之所以要特別加強對黨政官員的環境道德教育,是因為各級黨委和政府決策失誤、在環境保護方面不作為、干預執法等是造成環境頑疾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對黨政官員進行環境道德教育,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對黨政官員特別是“一把手”進行生態文明理論和環境法律法規方面的培訓,促使其將環境法律規定化為內在的環保意識和道德觀念,從而正向實現環境法律的道德化。二是加強對黨政官員的環境問責,通過嚴厲的問責和輿論宣傳,倒逼官員們自覺履行監管職責,從而反向實現環境法律的道德化。
之所以要特別重視對企業管理層的環境道德教育,除了企業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最主要的“罪魁禍首”之外,更重要的是因為企業管理層作為企業經營戰略的實際決策者和直接管理者,很多時候不需為其決策承擔責任和承受后果。當公司的生產經營行為造成環境污染時,基于公司之法人獨立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的法理,由公司自身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獨立承擔法律責任,而公司管理層雖然是實際決策者和管理者,但通常情況下除了可通過“雙罰制”追究其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外,他們并不需對外承擔民事責任,能夠“獨善其身”。此外,當公司因為環境違法行為而遭受罰款、責令限產限排乃至停產關閉等行政處罰時,通常而言,最受害的往往并非管理層而是處于弱勢地位的公司普通職工——他們對公司的生產經營決策無緣置喙、無能為力,卻要吞食暫時失業、生活難以為繼等苦果。
對企業管理層進行環境道德教育,主要方法有三:一是進行生態文明理念和環境法實證方面的培訓,促使其將法律規定內化為自身的環境道德觀念,主動順應生態文明的時代潮流,實現生產經營決策的生態化。譬如,作為跨國石油公司的英國BP石油公司很早就提出了“超越石油(beyond petroleum)”的口號,并將發展可再生能源作為公司的重大戰略。二是加強法律責任的追究,提高企業違法成本,通過追責倒閉企業管理層帶領企業自覺履行環境保護的法定義務,從而反向實現環境法律的道德化。三是建立企業管理層的黑名單制度,因環境問題而承擔法律責任的企事業單位,環保部門應將其環境違法信息記入社會誠信檔案,并及時向社會公布這些企事業單位及其核心管理層(決策者)的名單,迫使企業管理層自覺遵守環境法律法規,從而間接實現環境法律的道德化。
最后,鼓勵并大力發展環境非政府組織(NGO)。環境NGO的大力發展是加強生態社會建設的必然要求,是社會治理走向多元共治的重要表現,也是推動生態文化建設的組織保障。相對于公民個人而言,環境NGO具有人才、技術和資金等方面的顯著優勢,發展環境NGO有助于實現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專業化、規范化、有序化和權威化。
然而,目前我國的環境NGO不僅面臨人員缺乏、資金不足、規模不大和總體數量不多、社會影響有限等挑戰,而且其工作主要集中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調查、推動環境信息公開、對環境受害者進行法律援助等領域,很少能站在推進環境教育和環境道德建設的高度開展有關工作。
2014年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專章規定了公眾參與和信息公開,這對于推動環境治理由“政府—企業”之二元治理模式向“政府—企業—社會”之多元治理模式的轉變具有重大意義。然而,我們應當認識到,只有廣大公眾對生態文明建設具有較為全面、正確的認知,只有全社會普遍樹立了環境道德價值觀,環境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制度方能真正得以有效實施。當前,促進環境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最主要的是要在法律上放開其設立的限制性條件,放寬其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資格限制。
推進道德生態化,加強環境道德建設,雖路漫漫其修遠,但應篤定目標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