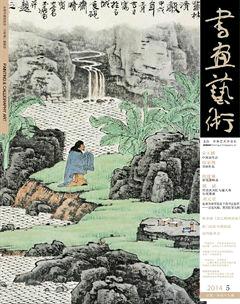簡論黃賓虹與潘天壽的筆墨觀
陳斌
黃賓虹與潘天壽都是中國山水花鳥畫創作的巨匠,和吳昌碩、齊白石被稱為20世紀傳統中國畫四大家。在上世紀中西文化激烈沖突,傳統文化處于被強烈沖擊的情境中,他們固守著中國畫的筆墨傳統,從其內部尋求突破,形成了并峙的幾大高峰。不過我們如果拿黃、潘二人來作比較,首先可以發現他們作品面貌與筆墨語言上的顯著不同;同時作為傳統意味的文人,他們傳世的筆墨觀點又透出小異而大同。
論者所謂“白賓虹”時期的作品,還明顯地受到“黃山畫派”的影響,畫面規整,景物粲然,顯示出不凡的傳統繪畫功底。這一面目的作品顯然較容易為人接受。從其師承授受來看,所受的正是相當正統的摹古訓練。“少時以家藏多明人畫,最愛天啟、崇禎間所作”,啟蒙老師也教導他作畫“當如作字法,筆筆宜分明,方不至為畫匠。再叩以作書法,故難之,強而后可。聞其議論,明昧參半……”然而,中年以后及至九秩變法,黃賓虹的畫面貌日趨黑密厚重,即所謂“黑賓虹”。雖然黃賓虹不乏傅雷等這樣的知音,但是此類黑團塊似的作品并不為當時大眾的認可。可以說,黃賓虹的從“白”到“黑”,是走向了傳統的反面,做出了徹底與傳統之法決裂的姿態。他自己也預感到了會受到中傷和非難,因而預言50年后始能識其真畫。
潘天壽的成才路徑似乎正好與黃賓虹相左。年輕的潘天壽完全憑借才氣作畫,少不了“亂頭粗服”和“行不由徑”。其師吳昌碩也慨嘆他“天驚地怪見落筆,巷語街談總入詩”的才情,他曾把自己學得像苦鐵的畫大部撕毀,以示求自家面目的決心;但缶老也擔心其筑基不牢的險境,警示他“只恐荊棘叢中行太速,一跌須防墮深谷,壽乎壽乎愁爾獨”。不過最終潘天壽取得了成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沉雄博大、蒼古高華、奇崛厚重的風格特征。畫面注重章法結構的布局經營,既造險,又破險,營造出非凡的物象氣勢。畫面干凈,物象分明,線條明確而有力。尤其是他的巨幅畫作,更顯示出非凡的境界與氣度。然而他的以線取勢、以墨取韻,也有被貶為墨韻不足等缺點。
黃賓虹化古為新,而潘天壽則可以說是由險入正;雖然藝術路徑有別,但畫面上都講究“詩書畫印”四全,都仍是傳統文人畫的路數。其所堅持的也都是傳統繪畫最基本的語言方式——筆墨方法。筆墨方法不僅包括寫意畫的筆法墨法,也包括工筆畫的“骨法用筆”以及相關的暈染法。傳統型中國畫的生命活力,體現于它仍在流動和演進;但這種流動演進不采取突變、質變而采取漸進的方式。它的內容、情感、具體程式、畫法與風格都不斷求變,但不改變由其基本語言方式決定的傳統(民族)風格。這一原則可借梅蘭芳“移步不換形” 的戲曲改革主張來表述。“移步”是有所前進,“不換形”是不改變它的基本特色。對中國畫而言,不換形就是不改變它的筆墨語言方式——包括它的材料工具和相應的程式性,對力感、節奏、韻致的要求,以及對道與技、心與物、形與神、人格與風格和諧關系的追求等。[1]黃、潘二人可以說正是踐行了這一藝術觀念。兩人都面臨中西文化沖突的歷史境遇,都對傳統有著深入的了解,同時也沒有無知地一味排斥西方。黃賓虹是認為對歐、日“借觀”以外,還須“返本以求”[2],但“鑒古非為復古,知時不欲矯時”。他曾說,“畫有民族性,無時代性,雖因時代改變面貌,而精神不移,今非注重筆墨,即民族精神之喪失”。[3]潘天壽也說,“若以己之短,步趨人之長,久之,恐失己之長耳”,認為“若徒眩中西折中以為新奇或西方之傾向東方,東方之傾向西方,以為榮幸均足以損害兩方之特點與藝術之本意”。
那么,具體到黃、潘二人的筆墨論,究竟存在著哪些同與異呢?關于黃賓虹的筆墨觀,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五筆七墨”。他在《虛與實》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平、留、圓、重、虛”,后在1934年的《畫法要旨》中,概括為“平、留、圓、重、變”五筆法。從具體執筆、用力、用鋒、行筆等操作層面進行分析。平則如書法之錐畫沙;圓則如折釵股;留為屋漏痕;重如高山墜石;變也似弩發萬鈞,全都是書法用筆的概括,也是自己繪畫實踐的總結。這和傳統“書畫同源”觀并無二致。按王中秀的解讀,這五筆法也可以說是用鋒法[4]。除了中鋒用筆之外,黃賓虹也并不排斥側鋒、偏鋒等法。唐張彥遠即概括說:“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因此可以說,黃賓虹是抓住了傳統書學畫學中的核心問題在闡發。潘天壽也說,“吾國繪畫,以筆線為間架,故以線為骨。骨須有骨氣;骨氣者,骨之質也,以此為表達對象內在生生活力之基礎也”[5]93。在潘先生看來,中國繪畫是以墨線為主表現畫面上的一切形體的;繪畫上的用線又和書法藝術的用線有關,“以書法中高度藝術性的線應用于繪畫上,使中國繪畫中的用線具有千變萬化的筆墨趣味,形成高度藝術性的線條美,成為東方繪畫獨特風格的代表”。黃、潘二人都在書法上用功甚深,兩人對書法用筆的認識是一致的。當然,黃賓虹在用筆的論述上,更具體細致,更有實際意義;而潘天壽的相關理論則相對概括,偏于宏觀,也沒有那么系統化。但兩者的理論精神還是相通的,仍然承續的是傳統文人畫理論中的精髓。
墨法方面,黃賓虹進行了更加深入地闡發,分有濃墨、淡墨、破墨、潑墨、漬墨、焦墨、宿墨共七法。可以說,這正是黃賓虹對前人理論和自己筆墨實踐的理論總結。郭熙《林泉高致?畫訣》有云:“運墨有時而用淡墨,有時而用濃墨,有時而用焦墨,有時而用宿墨,有時而用退墨,有時而用廚中埃墨……”。董其昌《畫旨》中也云:“老米難于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墨、焦墨、盡得之矣。”而黃賓虹其實是在墨的材質、運墨手法、用墨效果等方面,基于前人的基礎,進行了系統全面的闡發。潘天壽也在《聽天閣畫談隨筆》里大量的文字論述了墨法問題,而且是筆墨結合而論。比如“筆不能離墨,離墨則無筆。墨不能離筆,離筆則無墨。故筆在才能墨在,墨在才能筆在。蓋筆墨兩者,相依則為用,相離則俱毀”。另還有“用墨之注意點有二:一曰:‘研磨要濃。二曰:‘所用之筆與水,要清凈。以清水凈筆,蘸濃墨調用,即無灰暗無彩之病。老手之善于用宿墨者,尤注意及此”。[5]105他還在墨色的枯、濕、濃、淡、焦、潤等方面,也多所闡述。雖然角度和論述方式不同,但顯然潘、黃兩人的用墨理論也基本上是類同的。
綜觀黃、潘兩人的筆墨論,應該說大同小異,由此我們再反觀他們書畫作品的面目,會有新的體悟,同時也證明在傳統筆墨規則下也可以生發出不同的可能性。這其實也正可以用于比照受眾對兩個藝術巨匠藝術風格接受上的有趣事實。黃賓虹的畫風在當時看來還是曲高和寡的。賓翁自己曾說“我用重墨,意在濃墨中求層次,以表現山中渾然之氣趣”。潘先生在紹介賓翁的文中則給了他極高的評價:“然畫事中,用墨每難于筆,尤難以層層積累,先生于此,特有獨創,五彩六墨,錯雜并施,心應手,手應筆,筆應紙,從三五次至數十次,出于米襄陽、董叔達諸大家墨法之外。……繪事更深入于實中運虛,虛中運實,平中運奇,奇中運平之章法,以濃墨破淡,以淡墨破濃,寫其游歷之曉山、晚山、夜山與雨后初晴之陰山,每使滿紙烏墨如舊拓《三老碑》版,不堪向邇。然遠視之,則峰巒陰翳,林木蓊郁,淋漓磅礴,絢爛紛披,層次分明,萬象畢現,只覺青翠與遙天相接,水光與云氣交輝,杳然深遠,無所抵止。”[6]這種筆墨境界也就是現在的論者經常所謂的“渾厚華滋”,而實際上這也是黃賓虹自身畢生追求的。有意思的是,黃賓虹則評價潘天壽筆力能抗鼎,但是認為略少韻味。在吳茀之先生看來,這可能是指潘畫少墨色渲染之故。然其實潘畫如《焦墨山水圖軸》《雨后千山鐵鑄成》,把焦墨用到極致,也產生“潤含春雨,干裂秋風”之效果,傳達出非同一般的韻味。當然,在一幅畫面上,可能呈現的筆墨層次不如黃賓虹來得豐富,這也是有諸多學者嘆息潘老藝術之路過早中斷的原因。
另外一個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黃潘二人都兼擅山水、花鳥二科,黃賓虹的花鳥為其山水所掩,潘天壽則主要是以花鳥名世。潘老評價賓翁的花鳥“人們只知道黃賓虹的山水絕妙,花鳥更妙,妙在自自在在”,確是至評。畫科之分在兩位藝術家眼里沒有那么分明,關鍵是如他們這般嫻熟運用筆法墨法的畫家,可以單一或融合地進行創作。黃老古拙的用筆是他畫出既剛健又婀娜的花鳥作品的關鍵。潘老“強其骨”的用筆趣味也造就了他把山水和花鳥很好地融合在一件畫幅里。
因此,我的看法是,正如黃、潘兩人的筆墨論一樣,雖然兩人一個更擅用墨,一個則更擅用筆,但筆墨語言的使用上仍然大同小異的。兩人的用筆用墨雖然以不同的面貌呈現,卻已都是臻于化境,他們的繪畫也是最大限度地接近現代然而終尚未跨出傳統。黃賓虹在衰年變法中的作品更講求筆墨形式本身的意味,這和黃先生對西方現代派藝術的認知和借鑒是不無關系的。后世的現代水墨等藝術實踐都從他這里找到了根源。但是如果仔細領悟黃賓虹的筆墨論,就可以發現他們的筆墨實踐還是存在極大的區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吳冠中所謂的“如果離開繪畫具體表現的內容,那么筆墨等于零”這樣的論點實乃空谷足音。后來的論爭中脫離具體的語境而進行的討論不能不說就顯得有些盲目了。因為除了筆墨之美以外,還有題材美、意境美、構圖美等等方面,潘天壽正是在這些方面作出了重大的開拓。巧妙的構圖、高妙的造境,及高超的筆墨功力等因素才共同構成了潘畫的獨特風格。從黃賓虹、潘天壽的筆墨論及其書畫實踐中,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點。他們的理論和實踐應該說對后世的學人發展傳統中國畫是有長遠的啟發的。
注釋:
[1] 郎紹君.中國畫批評二題//國畫家[J].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1).
[2] 黃賓虹.黃賓虹文集[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24.[3] 黃賓虹.與傅雷書.
[4] 黃賓虹.虹廬畫談[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
[5] 潘天壽.潘天壽談藝錄. [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
[6] 潘天壽.黃賓虹先生簡介//潘天壽美術文集[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