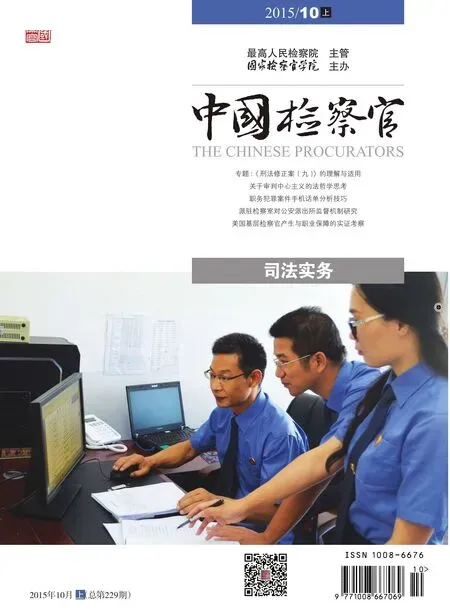未成年人搶劫犯罪案件適用法律疑難問題研究
●黃樹山 劉彥君/文
未成年人搶劫犯罪案件適用法律疑難問題研究
●黃樹山*劉彥君**/文
因未成年人身心的特殊性,公安司法機關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應遵循特殊的處理原則。在未成年人搶劫犯罪案件中,對于普通型搶劫罪、轉化型搶劫罪、攜帶兇器搶奪型搶劫罪的認定,應按照未成年人不同的年齡段有所區分。
未成年人犯罪搶劫少年司法轉化型搶劫罪
關心、愛護、保障未成人的健康成長,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是全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本文根據國家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與刑法理論上關于搶劫罪的基本認識,對未成年人搶劫行為構成犯罪適用法律的有關問題進行探討。
一、普通型搶劫罪之不同年齡段司法認定的區分
關于普通型搶劫罪的司法認定,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與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是否要作出區分,與危害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有著緊密的聯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7條第1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使用輕微暴力或者威脅,強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隨身攜帶的生活、學習用品或者錢財數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輕微傷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學習、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認為是犯罪。”第2款規定,“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具有前款規定情形的,一般也不認為是犯罪。”當然,這里的規定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具體表現為:(1)行為手段只能是輕微的暴力或者威脅,不能是較為嚴重侵害被害人人身健康的暴力或者威脅;(2)被害人只能是其他的未成年人(大多是正在上小學、中學的學生);(3)行為對象只能是隨身攜帶、個人用于學習生活的用品或者數量不大的錢財;(4)行為沒有造成被害人輕微傷以上傷害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學習、生活等危害后果。
在情節不是很輕,社會危害性程度較大時,對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所實施的危害行為,則應認定為犯罪。不過,此時應該注意在實施同樣的危害行為的情況下,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與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在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區別。這種區別不限于對未成年人的量刑影響方面,還體現于定罪上,即放寬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構成犯罪之罪行標準的掌握。具體而言,若沒有造成人身傷害,被害人僅有數額不算太大的財產損失,那么在存在初犯或者偶犯、家庭極度貧困、希望解決患絕癥親屬之困難等情形下,可以盡可能考慮不作為犯罪處理。
在情節顯著輕微,社會危害性程度較小時,對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所實施的危害行為,均不認為是犯罪。在適用上述規定時,還要注意:(1)在有上述行為表現的情況下,若行為人是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就一概不追究刑事責任,既不能認定為搶劫罪,也不能認定為其他犯罪;若行為人是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則在一般情況下不認定為犯罪,同樣也既不能認定為搶劫罪,也不能認定為其他犯罪(如尋釁滋事罪或者敲詐勒索罪等)。但若此類行為人多次或者長期針對不特定對象實施該危害行為,則可以認定為尋釁滋事罪。另外,此年齡段未成年人若針對特定對象多次或者長期實施該危害行為,數額累計達到敲詐勒索罪構罪標準以上,則可以認定為敲詐勒索罪。(2)在行為對象上,所謂的學習、生活用品與數量不大的錢財在價值數額上是基本相同的。不過,最高司法機關對構成搶劫罪的數額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首先可參考最高司法機關關于其他侵犯財產罪之構成犯罪數額的規定,其次可以考慮行為人當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最后要考慮未成人在學習、生活中所用物品的一般價值,同時再考慮此價值物品或者錢財對未成年人日常生活的實際影響,因為未成年人的生活資料通常是父母等監護人供給,其一般不會掌握數額較大的錢財。(3)關于行為的后果,除了被害人受傷狀況、財產損失外,還要考慮其他后果,即被害人在心理上受到嚴重損害,不能進行正常的學習生活等。其中,比較突出的表現就是被害人不敢正常到學校學習、生活,或者即便到校,但產生嚴重心理壓力或者疾病的情況。
除了上述情形之外,在被害人是其他人群的情況下,對于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實施的危害行為是否認定為搶劫罪,與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構成搶劫罪的情況可以作不同的對待,即考慮將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的“情節輕微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搶劫行為不作為犯罪處理,將該年齡段未成年人與已滿16周歲未成年人在認定構成犯罪的標準上作更寬一些的把握。
二、轉化型搶劫罪之不同年齡段司法認定的區分
對于不同年齡階段未成年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后為窩藏財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的情況,《解釋》第10條規定予以分別處理,即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盜竊、詐騙、搶奪他人財物,為窩藏財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當場使用暴力,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殺人的,應當分別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人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財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當場使用暴力,即便沒有造成被害人傷亡,也認為符合《刑法》第269條之規定,按照搶劫罪來追究刑事責任。
對于上述規定,理論上有不同的認識,現結合一個現實的案例分析。2013年5月8日11時許,被告人牛某竄至息縣城關鎮千佛庵路某理發店門口,趁馮某某不備,將馮某某手中錢包搶走,內有現金3000余元及手機一部(價值639元)。其逃至該理發店附近一巷內后,被緊追其后的馮某某堵在了巷口,被告人牛某為抗拒抓捕,遂從路口處撿起一塊瓦片砸向馮某某,并趁其躲避之機逃走。被告人牛某犯罪時屬于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關于如何對牛某的行為進行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牛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理由是:牛某不符合轉化型搶劫罪的主體要求。《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由此可見,構成轉化型搶劫罪的前提是犯盜竊、搶奪、詐騙罪。而《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的已滿14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應當負刑事責任的八類犯罪中并未包括搶奪罪。因此,牛某的行為不符合盜竊罪的主體,也不能成為轉化型搶劫罪的主體。第二種意見認為,牛某的行為構成搶劫罪。理由是:第一,第17條第2款所規定的搶劫罪應包括轉化型搶劫罪的情形;第二,構成轉化型搶劫罪的前提并非必須構成盜竊、搶奪、詐騙罪。
檢察機關在辦理該類案件時認為牛某不能成為轉化型搶劫的主體,牛某在實施搶奪行為后,又實施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罪證的行為,但未對他人造成人身傷害,其行為不宜認定為轉化型搶劫罪。
2003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關于相對刑事責任年齡的人承擔刑事責任范圍有關問題的答復》第2條規定:“相對刑事責任年齡的人實施了《刑法》第269條規定的行為的,應當依照《刑法》第263條的規定,以搶劫罪追究刑事責任。但對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可根據《刑法》第13條的規定,不予追究刑事責任。”此后,200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10條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盜竊、詐騙、搶奪他人財物,為窩藏財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當場使用暴力,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殺人的,應當分別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
無論從罪刑法定原則還是未成年人刑事保護政策來看,對于14至16周歲的人,在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后,又實施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罪證的行為的,不宜認定為轉化型搶劫罪。如果事后使用暴力的行為造成了被害人重傷、死亡結果的,可以追究其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主要理由在于:一是對于14至16周歲的人適用轉化型搶劫罪,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根據《刑法》第17條規定,對于14至16周歲的人,《刑法》只能對其所實施的八種行為進行評價。如果認為14至16周歲的人在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后,又實施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罪證”的行為,將此種行為認定為是轉化型搶劫罪,則說明刑法對于行為人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進行了評價,這顯然是違反了《刑法》第17條第2款的規定。二是對于14至16周歲的人適用轉化型搶劫罪,有違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刑事政策。《解釋》第7條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使用輕微暴力或者威脅,強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隨身攜帶的生活、學習用品或者錢財數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輕微傷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學習、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認為是犯罪。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具有前款規定情形的,一般也不認為是犯罪”。司法實踐中對于未成年人所實施的搶劫行為,一般也是按此操作的。轉化型搶劫社會危害性比普通搶劫罪要小,對于14至16周歲的人,基于刑事政策的考慮,結合其社會危害性,對其不以犯罪論處并不會放縱犯罪。此外,就14至16周歲的人的認識能力而言,承認其對于普通搶劫罪的認識能力成熟,并不能承認其對轉化型搶劫罪的認識能力也成熟了。畢竟,轉化型搶劫罪是行為人在“犯盜竊、詐騙、搶奪罪”后的一種本能的反抗。
三、攜帶兇器搶奪型搶劫罪之不同年齡段司法認定的區分
《刑法》第267條第2款規定,攜帶兇器搶奪的,依照搶劫罪定罪處罰。在現實生活中,未成年人攜帶兇器對他人實施搶奪的情形比較常見,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對于該問題的分析既要注意對“攜帶兇器搶奪”這一情節的正確理解,又要注意未成年人構成搶劫罪的具體特點。
攜帶兇器搶奪是對搶劫罪客觀行為方式的擴張性解釋,在能否適用于未成年人的問題上應當特別慎重。一種意見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2日發布的《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的規定,“攜帶兇器搶奪”是指行為人隨身攜帶槍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進行搶奪或者為了實施犯罪而攜帶其他器械進行搶奪的行為,必須是行為人在攜帶兇器搶奪時并未將該兇器向被害人出示或者對被害人使用。否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6月8日發布的《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條的規定,應直接按照搶劫罪的規定定罪。而之所以按照搶劫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是因為行為人攜帶兇器搶奪,在主觀上有對被害人使用或者向被害人出示表達威脅的意圖,盡管這種主觀意圖并未轉化為客觀表現,被害人也沒有感受到行為人對自己的暴力侵害意圖。《刑法》第267條第2款的規定顯然將行為人為使用而攜帶兇器但實際并未使用的情形,在《刑法》意義的評價說等同于行為人使用兇器實施搶劫的情形,且都評價為搶劫罪,實際上擴大了搶劫罪之實行行為的客觀表現,可謂非典型性的搶劫罪,而這種非典型性在程度上甚至比轉化型搶劫還要低。
在司法實踐中,關于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是否構成這種不典型的搶劫罪的問題,一般持否定性的意見。首先,攜帶兇器搶奪型搶劫罪在社會危害程度上低于轉化型搶劫。畢竟,在轉化型搶劫中,行為人實際地使用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而攜帶兇器搶奪中,行為人并未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其次,攜帶兇器搶奪型搶劫罪是對搶奪罪的升格處罰。《刑法》和有關刑事司法解釋將搶劫罪的客觀行為表現予以擴張,包括攜帶兇器搶奪的情形,實際上是對攜帶而未使用兇器搶奪的情形給予嚴厲的懲罰,以有效地保護社會,其針對的對象主要是實施搶奪犯罪的行為人,即符合搶奪罪犯罪主體資格的行為人,而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顯然不符合搶奪罪的主體資格。
已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可以構成攜帶兇器搶奪型的搶劫罪,原因如下:其一,其完全具備搶奪罪之犯罪主體的資格,在沒有攜帶兇器而搶奪的情況下能構成搶奪罪,在攜帶兇器搶奪的情況下也符合被升格處罰,可以按照搶劫罪來處理。其二,其可以構成轉化型搶劫罪,那么,可以對其考慮是否構成攜帶兇器搶奪型之搶劫罪的問題。因為其在確實實施攜帶兇器搶奪之情況下,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程度上并不亞于成年人,符合攜帶兇器搶奪型的搶劫罪的構成要求。
*河南省息縣人民檢察院辦公室主任[464300]
**河南省息縣人民檢察院公訴科檢察員[46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