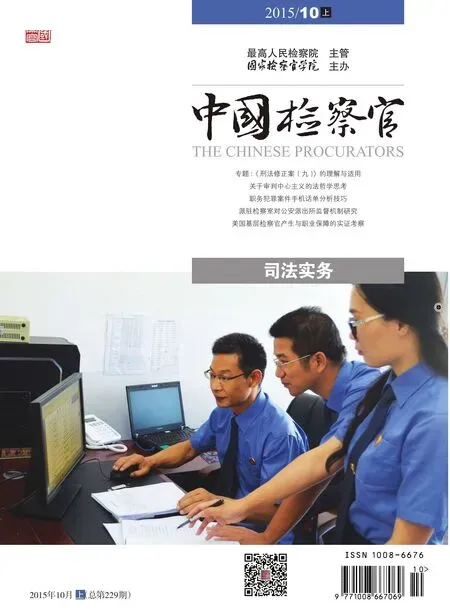民事檢察監督的現狀與完善
——以依職權監督為視角
●馬書振 潘美全/文
民事檢察監督的現狀與完善
——以依職權監督為視角
●馬書振*潘美全**/文
民事檢察監督制度是保障民事訴訟活動公正的一項重要制度。但是,對于民事檢察監督這種公權介入私權的訴訟模式,在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均是褒貶不一,爭論激烈。尤其是檢察機關依職權監督的方式由于無論是在理論研究方面還是立法方面都存在不成熟、過于原則化的弊端,這嚴重影響了民事檢察監督制度在我國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具體實施。本文試圖對檢察機關依職權的監督機制進行梳理和反思,就如何更好地發揮檢察監督權力展開探討,企盼對我國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檢察權民事訴訟模式依職權監督
現行《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規定了檢察機關民事訴訟監督案件的來源包括三類,一是當事人申請監督;二是當事人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控告、舉報;三是人民檢察院依職權發現。對于第一類、第二類案源基本不存在爭議,似乎更符合民事訴訟中當事人意思自治、私權至上的理念。但是,對于第三類案源卻頗有爭議,爭議的焦點并非弱化檢察監督,而是如何實現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統一,如何平衡當事人申請監督與依職權監督的關系,如何更好地保持訴訟架構的穩定。
一、依職權監督的理論基礎和監督方式
(一)理論依據:列寧的法律監督理論
權力制衡、以權制權是法治建設的核心,民事檢察監督便是來源于權力制約權力的機構設置邏輯。現實中,不管是《憲法》還是《民事訴訟法》均已確立了“實踐以檢察權制約審判權”的模式。那么,民事檢察監督作為檢察權的組成部分,檢察權的性質必然決定了民事檢察監督的屬性。我國檢察權的理論依據來源于列寧的法律監督理論,即、“使法律監督權從一般國家權力中分離出來,成為繼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之外的第四種相對獨立的國家權力。[1]任何一種權力的行使都有其特定的模式或者規范。[1]檢察權作為一種法律監督權也需要合法、合理的操作規程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既不能缺位亦不能越位。
(二)監督方式:恰當配置、科學實施
至于民事檢察監督在《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方式,有學者認為其是一種國家干預模式。[2]即在職權主義模式下,民事檢察監督作為一種國家公權力介入民事訴訟領域,與法院審判權一起對當事人訴權進行干預。不管何種介入模式,其目的都是啟動對民事案件的再次審查處理。人民檢察院作為啟動的主體之一,其依職權主動介入的模式必須恰當配置、科學實施,必須嚴格遵守《民事訴訟法》的規定。
《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限定了人民檢察院依職權監督的案件有三類: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審判、執行人員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為的;依照有關規定需要人民檢察院跟進監督的。筆者認為,民事檢察監督雖是對民事訴訟活動的全面監督,但仍應保持謙抑性。以當事人申請為主,檢察機關依職權監督為輔,尊重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原則,只在當事人私權影響到公共利益的時候再主動介入民事訴訟活動。
二、依職權監督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一)依職權監督爭議的焦點問題
如前文所述,現行《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規定的檢察機關民事訴訟監督案件的三類案源中,第一類和第二類案源基本不存在爭議,似乎更符合民事訴訟中當事人意思自治、私權至上的理念。對于第三類案源卻頗有爭議,主要詬病在于檢察機關依職權主動進行民事檢察監督妨害了審判獨立,妨害了當事人的處分權,妨害了訴訟結構的平衡。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民事訴訟活動中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不可避免的會與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的民事檢察監督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司法的公正和公共利益的不受損害。因此,爭議的焦點并非弱化檢察監督,而是如何實現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統一,如何平衡當事人申請監督與依職權監督的關系,如何保持訴訟架構的穩定。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應該是相互統一的關系,在維護司法公正、社會公共利益的同時,個人利益也應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在保護個人利益時,也不能損害公共利益。
(二)民事訴訟模式的轉化問題
從檢察權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民事檢察監督經歷了一個起伏的過程,從最開始的全面監督甚至可以代為起訴、參與訴訟到被廢除,又到如今的以抗訴為主的多元化監督模式。這一發展軌跡隱藏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國民事訴訟模式的轉換。所以,從本質上說,民事檢察監督運行中出現的問題都是因對訴訟模式抉擇的理念差異。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指出:“如果將法律理解為社會生活的形式,那么“作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則是這種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桿頂尖,對船身最輕微的運動也會作出強烈的擺動。”[3]所以說,程序法和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影響著人們生活和國家發展的方方面面,這也體現當事人私權利的維護。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扎根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集權政治體制中的職權主義模式已然不能適應當前社會的新要求。在民事訴訟糾紛的解決機制上減少公權力的干預,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愿,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司法救濟制度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在訴訟模式的選擇上也出現了大陸型當事人主義、和諧主義、協同主義等不同的觀點。但是,我們也必須清楚的認識到:任何一種制度的選擇都離不開本國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國情。
(三)民事訴訟模式的選擇問題
本文認為,訴訟模式選擇之根本在于如何劃分公權力與當事人私權利在民事訴訟中的職能分工而不是絕對化某一種模式。具體來說,對民事檢察監督持消極態度的一個重要論據就是檢察機關依職權監督是對當事人私權的干預。本文認為,這一觀點站不住腳。首先,不管是當事人申請還是檢察機關主動依職權監督,都是一種啟動方式,目的在于啟動對案件的再審或再次審查程序,以糾正錯誤的裁判或行為。只要合理配置啟動權限,完全可以在檢察機關依職權監督與當事人申請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點。其次,有觀點認為檢察權主動介入會導致訴訟結構失衡。筆者認為,任何一種權力的行使必然會牽扯到個人利益,但我們應動態地看待民事檢察監督權的行使。從表面上看,民事檢察監督的過程和結果確實是有利于某一方當事人的。但是,立法設立這一制度的目的不僅僅是對個案當事人利益的保護,更重要的是為了有效制約法院的司法權,從而實現訴訟的公平正義。[4]不論是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還是《民事訴訟監督規則》,都對民事檢察監督權的運行設定了一定的要求。例如《民事訴訟法》第209條中對當事人向檢察機關申請再審檢察建議及抗訴設定了一個前置程序,即必須先向法院申請再審,在符合本條規定的三種再審情況之一時才可以轉而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此舉一方面是督促當事人及時行使權利,另一方面亦要求檢察機關保持謙抑態度,不能鼓勵當事人放棄法院的自我糾正程序而直接干預生效裁判。最后,《民事訴訟監督規則》亦規定了檢察機關依職權監督限于三種案件類型,不能隨意擴權,這也體現了對當事人私權力的維護。
三、依職權監督機制的完善
“任何利益間的沖突,都存在選擇的一般性原則。當發生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時,或者由此產生了的權衡與選擇的問題時,為獲得某種利益或者肯定某種事物、行為的價值,就要放棄或否定與之對立的另一些權益或價值。”[5]本文認為,民事檢察監督權介入民事訴訟領域,一方面要保持自己“法律監督權”的本質,在對民事訴訟活動的公權監督上不能退位;另一方面也要遵循民事訴訟的原則,不能因檢察監督而造成訴訟結構的失衡。
(一)合理設定依職權監督的案件范圍
《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設定了三類案件可依職權主動監督。本文贊同此規定,但在實踐中要嚴格把握,并不是所有涉及國有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都可以依職權啟動程序。舉例說明:筆者辦理的甲某與乙公司項目部(乙公司系國有企業,乙公司項目部是其下屬分支機構)民間借貸糾紛一案,雙方達成了一筆近300萬的借條,通過法院調解方式予以確認并進入執行程序后乙公司項目部無還款能力,法院追加乙公司為被執行人。此案件涉及甲某和乙公司項目部負責人虛假調解侵害國有資產的嫌疑。對于該調解書的監督存在兩種方式,一是案件當事人申請再審,包括甲某、乙公司項目部以及乙公司;二是檢察機關以涉及國家利益為由依職權主動監督。我們采取了前一種方式,建議乙公司首先向法院提出主張,在法院不作為的前提下,依照乙公司的申請受理該案。假設該案各當事人均怠于行使權利,既不向法院提出再審申請,又不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那么檢察機關應當主動依職權介入,監督法院調解程序是否存在違法情況,監督有關人員是否存在犯罪情況。
(二)合理把握依職權監督的方式
檢察機關在依職權調查案件事實時,必須遵循基本的民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不能替代當事人承擔舉證的責任。確需調查核實時,也應注意按照提出檢察建議或者抗訴的需要了解必要的信息,不能將調查核實權理解為類似自偵案件中的偵查權,應尊重并保護民事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對于涉及個人隱私、商業秘密、信息安全等事項,更要依法行事,嚴格遵守相關規定。例如,上述案例中,甲某與乙公司項目部在庭審時并沒有明顯的抗辯即達成調解協議。但是,民間借貸合同為實踐性合同,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間不僅要達成貨幣借用合意,還必須實際給付借款才能生效。因此,查明該筆借款是否實際給付是審理該案的前提和基礎。由于法官并未查明該事實,僅依當事人自認即判令乙公司項目部償還借款,所以此案確有調查核實之必要。檢察機關通過調查,發現該筆近300萬元的借款并未實際支付,亦即該借貸關系并未生效。因此,法院調解書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據此,檢察機關依法向法院發出再審檢察建議。
民事檢察監督工作的深入發展要求我們在實施監督的過程中不斷探索其最佳的運行機制。這是強化法律監督力度,有效推進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保障司法權威的必然要求,也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的內在要求。[6]檢察機關在依職權監督的過程中只要張弛有度,找準職能定位就能最大程度地保證民事檢察監督的正當性。
(三)不斷更新依職權監督的理論基礎
通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全面發展,司法改革不斷推進,人民群眾法律意識也不斷增強,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人民的“權利”觀念日漸增強,對于計劃經濟時代下的“干預私權”的思想已有所認清。因此一方面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理論基礎“干預學說”已經有所動搖和改變,另一方面國外發達國家普遍采納的“公益學說”的合理性也逐漸被承認和推崇。我國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發展和改革應當順應國際潮流、更新理論認識,摒棄“干預”理論,減少和弱化對私權領域的過度干預,逐步吸收“公益學說”,將檢察監督反限于對公共權益的有力保護。[7]
注釋:
[1]參見王桂五:《列寧法律監督理論研究》,載《檢察理論研究》1993年第4期。
[2]參見湯維建:《我國民事檢察監督模式的定位與完善》,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3]參見[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頁。
[4]參見張晉紅:《關于取消和弱化民事抗訴制度理由之商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8頁。
[5]參見宋英輝:《刑事訴訟原理導讀》,法律出版社2003版,第118頁。
[6]參見韓善宏:《民事檢察監督法律制度實證研究》,山東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第12頁。
[7]參見浦亮:《論民事檢察監督權之擴張與謙抑——兼評〈新民訴法〉對檢察監督制度的修改》,載《法制博覽》2015年第5期。
*河南省南陽市新野縣人民檢察院[473500]
**山東省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檢察院[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