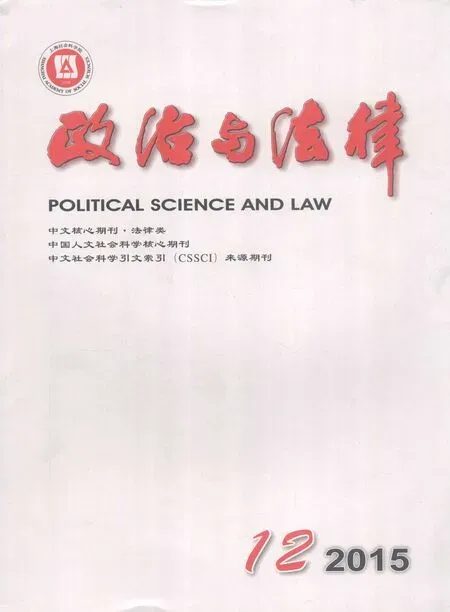刑法上職務便利與工作便利的區別必要性辨析*
尹 琳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上海200020)
刑法上職務便利與工作便利的區別必要性辨析*
尹琳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上海200020)
在現行刑法中,“利用職務便利”是貪污罪、受賄罪等職務犯罪成立的客觀方面必備要件之一。但是,司法認定經常會把“利用職務便利”與“利用工作便利”混為一談。從本質看,“工作便利”的內涵與外延,比“職務便利”大,這是刑法將“利用職務便利”作為職務犯罪成立客觀方面要件的原因。貪污罪的“職務便利”側重于直接管理與支配,而受賄罪的“職務便利”更側重于對事項的決定與處置的管理性。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在工作過程中侵占公有財物或收受他人的財物,就侵犯了其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或不可收買性,導致國民對其職務的公正性喪失信任,應當成立職務犯罪。因此,“職務便利”與“工作便利”區別的根本意義在于區別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利用職務便利”獲取財物構成貪污罪、受賄罪等職務犯罪,而“利用工作便利”獲取財物構成的是財產類犯罪。
職務便利;工作便利;區別;受賄罪;貪污罪
在我國現行刑法中,規定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利用職務便利”為構成要件的罪名有14個之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更是貪污罪、受賄罪等職務犯罪成立的客觀方面必備要件之一。另外,雖然我國刑法并未設有“利用工作便利條件”的相關規定,但在司法實務認定中,對于一個行為,到底屬于“利用職務便利”還是屬于“利用工作便利”,經常會成為困擾司法實務人員的疑難問題。因此,研究“利用職務便利”與“利用工作便利條件”的區別必要性,可以幫助司法實務合理界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準確認定此類犯罪,更好地打擊職務犯罪。
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內涵
(一)“職務”與“工作”的概念界定
“職務”一詞最早出現在行政法學和行政法領域。行政法意義上的“職務”,是指某主體在一定機關或者事業單位中所實施的國家和社會管理的行政權責,這也就是行政職務。①林嵐:《論我國刑法中的“利用職務之便”》,西南政法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現代漢語詞典》將其解釋為“職權規定應當承擔的工作”。從該解釋可以看出,“職務”不僅包含了“工作”,還包含了“職權”,“職權”可以說是“工作”所對應的特定權力的外化。因此,職務是一項工作,不能與“職權”畫等號;亦即不能把“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僅僅解釋為“利用職權便利”。②黃祥青:《“利用職務上便利”與“利用工作條件便利”之區別》,《人民法院報》2004年7月19日,有學者認為所謂職務,是指公務員處于其地位應當作為公務處理的一切事務,其范圍雖然大多由法令規定,但由于法令不可能完全列舉公務員的事務,故公務員為了完成其任務而基于公務員的立場所實施的行為,也屬于職務。③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第二版)》,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35頁關于“工作”的概念,《現代漢語詞典》對其解釋包含有三個方面內涵,即“從事體力或腦力勞動;職業;業務,任務”。從上述解釋可以看出,“工作”的含義不僅包括“職務”,也包括一般的業務。
因而,從日常生活的通俗解釋上來看,“工作”應該包含“職務”。刑法上的“利用工作便利”,是指行為人與非法占有的財物之間并無職責上管理與支配的權限,僅僅是因為在工作中形成的機會或偶然情況接觸到他人管理、經手的財物,或因工作關系熟悉周圍環境等,對非法占有財物形成了便利條件。④王佩芬:《“利用職務便利”與“利用工作便利”的區別》,《檢察日報》2009年7月22日。從該解釋也可以看出,“利用工作便利”的內涵十分寬泛。所以,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利用職務便利”是包含在“利用工作便利”之內的。此外,理論界有觀點認為:“工作便利一詞容易讓人進行擴大解釋,這樣的結果往往是:凡是利用了工作關系所實施的行為,這些行為都被視為利用了職務便利。”⑤王俊平、李山河:《受賄罪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頁。正因為“工作便利”的內涵與外延要比“職務便利”大,我國刑法為了更合理地規范和界定職務犯罪的罪名,沒有使用“利用工作便利”,而是將“利用職務便利”作為此類犯罪成立的客觀方面要件。
(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理論探討
我國現行刑法中,總共有14個罪名直接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利用職務便利”作為犯罪構成的要件,而刑法并沒有直接規定“利用工作便利”為犯罪構成的要件。因而,為了探明職務便利與工作便利區別的必要性存在與否,需要對刑法中規定“利用職務便利”的罪名進行分析,本文著重針對貪污罪和受賄罪進行分析。
1.刑法第382條貪污罪的分析
我國刑法第382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是貪污罪。”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1999年9月16日《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標準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立案規定”),在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務上主管、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權力及方便條件。
與此同時,理論界對于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觀點。有許多學者持和上述立案規定的解釋相同的觀點。也有觀點認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務上主管、管理、經營、經手公共財物的權力及方便條件。⑥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6頁。該觀點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解釋,比司法解釋要寬泛,認為利用“經營”的便利也是一種手段。還有觀點主張,所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自己職務范圍內主管、經營、管理公共財物的職權所形成的便利條件。⑦劉憲權:《刑法學(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32頁。此種觀點不將“經手”公共財物的便利當作利用職務之便,認為職務便利與從事公務的身份密切相關,其根本屬性在于管理性。而經手的便利不具有管理性質,營業員雖有經手公款的便利,也不能構成貪污罪,所以經手公共財物的便利不屬于職務便利。①同前注⑦,劉憲權書,第832頁。還有觀點認為,貪污罪中的利用職務之便是指直接利用本人職務上的權力,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利用本人主管、經管財物的職務的便利條件;另一種是擔任其他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因其執行公務而臨時經手、管理公共財物。②王作富:《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下)》,中國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4頁。
綜合上述司法解釋和理論界的觀點來看,貪污罪中作為犯罪成立的客觀方面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不外乎“主管、管理、經營、經手”這幾種形式。筆者認為,以上這幾種形式都應該作為職務上的便利條件。因為職務是單位給予的一種職權性工作,在這種職權下,會進行持續反復的工作,故這種職務應該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在這樣的條件下,持續反復的“經營”、“經手”都應該認為具有相應的管理性,應認定為職務上的便利。
2.刑法第385條受賄罪的分析
我國刑法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案規定”,在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力,即自己職務上主管、負責或者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條件。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中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擔任單位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不屬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相比較來看,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案規定”強調了“利用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力”,而不包括本人職權可以制約他人所形成的便利條件,偏重限制直接受賄的成立范圍。③孫國祥:《受賄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新論》,《法學論壇》2011年第6期。而最高人民法院“紀要”,并沒有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進行直接的解釋,其采取的是直接列舉一些“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具體情形。
理論界對于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只要國家工作人員所索取或者收受的財物與其職務行為有關,就可認定為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因為索取或者收受與職務行為有關的財物,就意味著對方必須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付出財產上的代價,侵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④同前注⑥,張明楷書,第1071頁。也有學者提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現有職務范圍的權力,即利用本人因現有職務而主管、負責或者承辦某種公共事務所形成的便利條件。⑤孫國祥:《刑法學》,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55-656頁。該學者還提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應涵蓋以下七種情況:利用本人直接主管、經辦和參與某種具體公共事務的職權;利用本人的一般職務權限;利用濫用職權所產生的便利條件;利用自己分管、主管的下屬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利用不屬自己分管的下級部門國家工作人員職權;利用自己居于上級領導機關的地位而形成的對下級部門的制約力;利用自己居于監管地位所形成的對被監管對象(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制約力。⑥同前注⑩,孫國祥文。此外還有學者認為,受賄罪因為是用手中的權力為他人謀利而收取他人財物,其利用的職務便利,只能是利用對某一事項有審批、控制、支配、安排等權的職務便利,偏重于對事項的決定和處置的管理性。⑦同前注⑦,劉憲權書,第852頁。
3.貪污罪與受賄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區別
通過前文的論述可以得知,受賄罪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不同于貪污罪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貪污罪側重于直接的管理與支配,而受賄罪除直接主管、經辦或參與以外還包括間接的管理或者制約。筆者認為,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涵義更為寬泛,在刑法法條中使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這種語言進行表述,有可能造成狹義理解,不甚合理。比如有些國家的刑法典就沒有直接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是規定‘公務員就職務’或‘公務員對其職務’要求、期約或收受利益”。①同前注⑥,張明楷書,第1071頁。因而,雖然貪污罪與受賄罪的客觀方面都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但是這兩罪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內涵不同,主要區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貪污罪與受賄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所實施的行為不同。貪污罪中的行為是非法占有公共財物,而受賄罪中的行為則是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
第二,貪污罪與受賄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所侵害的法益不同。貪污罪行為所指向的是公共財物,而受賄罪行為指向的卻并不是財物,而是為他人謀取的不正當利益。因此,貪污罪所侵害的法益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而受賄罪所侵害的法益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
第三,貪污罪與受賄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表現形態不同。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包括主管、管理、經營、經手,其側重于直接管理與支配,而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更側重于對事項的決定和處置的管理性,因而,受賄罪還包括對事項的間接的管理和制約。
二、有關“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比較法考察
(一)德國
德國刑法典在第三十章是有關于職務犯罪的規定。其中第331條對接受利益罪所作的規定是:公務員或對公務負有特別義務的人員,針對履行其職務行為而為自己或他人索要、讓他人允諾或收受他人利益的。其第332條對索賄罪的規定是:公務員或對公務負有特別義務的人員,以已經實施或者將要實施的、因而違反或將要違反其職務義務的職務行為作為回報。②許久生、莊敬華譯:《德國刑法典》,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頁。
從條文中可以看到,德國刑法典中違反職務義務、履行職務行為是職務犯罪中不可或缺的犯罪構成要件要素。
(二)法國
法國新刑法典中關于違反廉潔義務的犯罪,對于職務行為有如下的闡述:其一,完成或放棄完成屬于其職務、任務或委托權限范圍的行為或者可由其職務、任務或委托權限提供方便之行為;其二,濫用其實際影響或設定的影響,以圖指使他人從權利機關或公共行政部門取得有別于人的禮遇、工作職位、市場或其他任何有利于己之決定。③羅結珍譯:《法國新刑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頁。由此可以看出,法國對于職務犯罪中是否利用了職務之便有較為明確的法律規定,只要是職務、任務、委托權限范圍內,或可以借由職務、任務、委托權限提供方便的就應當認為是利用了職務之便,濫用或者利用職務的影響力謀取利益也應當屬于利用職務便利的范疇。
(三)日本
1.對日本刑法典的相關規定的解讀
日本刑法對于受賄有相關的規定:公務員就職務上的事項,收受、要求或者約定賄賂的;公務員就其職務上的事項,接受請托,使請托人向第三者提供賄賂,或者要求、約定向第三者提供賄賂的。①張明楷譯:《日本刑法典(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頁。
日本認定職務便利一般以該職務行為與犯罪行為之間是否具有對價關系為判斷基準,在此意義上來說,職務犯罪的核心要件即職務行為與該犯罪行為的對價關系,如果能夠肯定這種對價關系,則意味著將職務行為置于犯罪行為的影響之下,從而對職務的公正性產生危險。從日本的刑法相關規定可以看出,首先,職務并不限于法令直接規定的事務,職務不僅包含自身正當的職務,而且包含了不正當的職務;其次,內部的事務分工對于職務行為的判斷并不重要;再次,根據日本判例與學說,除了公務員的本來的職務行為外,與職務有密切關聯的行為也是職務行為(即準職務行為);最后,職務行為不僅包括現在的職務行為,而且包括過去的職務行為與將來的職務行為。
關于賄賂罪的保護法益,日本判例一般采取信任保護說即“公務員職務的公正性及其社會普遍的信任”的立場,多數學說也持同樣的觀點。賄賂罪的本質在于公務的不可收買性。公務員因為收取賄賂導致人們對公務的公正性失去信任,必須處罰。②[日]山口厚:《從基本判例學習刑法各論》,成文堂2010年版,第312頁。從這種立場看,賄賂與職務行為處于對價關系是賄賂罪的基本成立要件,所以不論公務員的職務行為是否缺乏公正,都被認為是犯罪。在原則上,如果侵害了職務行為的公正性,就需要加重處罰。
2.職務行為的關聯性問題
在賄賂罪中,斡旋受賄罪作為例外,公務員僅在有關自己的“職務”行為中獲得不正當利益時才成立。因此,確定職務行為的范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日本的判例、通說認為,職務行為只要屬于該公務員一般的職務權限范圍的事務即可。還有兩種與職務密切關聯行為也被稱為準職務行為:其一,并非自己本來的職務,但屬于習慣上負責的職務,或者屬于由自己的職務所派生出來的職務;其二,利用自己職務的事實上的影響力。③[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論》,劉明祥、王昭武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85頁。這些行為在嚴格意義上不屬于職務行為,但是與職務行為有密切的關系,而這些行為是否具有關聯性還存在爭議。
這其中最具有爭議的行為是,利用在履行職務之際所遇到機會的行為,或者利用在職務上所獲得知識的行為。日本的判例對此持兩種觀點:“第一,不承認存在職務關聯性。市政府建設部開發科職員,對來訪的公司有關人員介紹市政府建成的工業用地,因為沒有該公司所期待的土地,接受委托私下尋找賣主,并幫忙斡旋買入別的土地的行為,不算是與職務有密切關系。第二,承認存在職務關聯性。戰災復興院派駐到地方建筑事務所的工作人員,負責發行建筑材料需求的分配證明,推薦業者向特定店鋪購買板狀玻璃的行為,被視為與履行職務有密切關系的行為。國立大學音樂系教授斡旋自己教育指導的學生購買小提琴的行為,應肯定其職務密切關聯性。”④[日]鹽見淳:《賄賂罪的職務關聯性》,載西田典之等編《刑法的爭點》,有斐閣2007年版,第261頁。筆者認為,依據日本判例的觀點來看,上述利用在履行職務之際所遇到的機會,或者利用在職務上所獲得的知識的行為是否應視為與職務有密切關聯性,最根本的判斷標準應該是行為和職務是否具有直接關聯性。
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判例分析
(一)關于貪污罪
周某某在擔任保安隊長時,負責監督、管理四個小區日常保安工作和收費情況,并將小區保安人員收取的停車費匯總后上繳至某物業公司指定的銀行賬戶。周某某擔任保安隊長期間,利用前述職務上的便利,采用隱瞞實際的停車費收入、偽造虛假數據報表等方式,將保安人員匯總上繳到其處的部分停車費予以侵吞。最終法院認為周某某受國有公司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國有財產,其行為已構成貪污罪。①參見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2012徐刑初字1093號刑事判決書。
該案中,周某某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還是利用工作便利,是影響貪污罪成立的關鍵問題。前文已述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應包括利用職務上主管、管理、經營、經手公共財物的權力及方便條件。該案中,周某某主要職責之一是審核、匯總保安人員收取的停車費后上繳公司,因而,他的行為是利用“經手”國有財產的方便條件侵吞國有財產,故符合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這一要件。
(二)關于受賄罪
方俊在擔任慈溪市園林管理處副主任時,分管綠化建設及綠化養護等工作,對綠化建設、養護等工程的方案、招投標、竣工驗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決定權。方俊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綠化建設及養護施工單位提供方便。該案中,方俊作為專業部門的工作人員,具有相關行業的技術,表面上為相關單位提供勞務以獲得報酬,而實際上只是提供了少量服務來掩蓋收受財物的事實。②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第二庭、第三庭、第四庭、第五庭編:《中國刑事審判指導案例(6)》,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198頁。
該案中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正確區分正當的勞務報酬與非法受賄的界限。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該指導案例中提出應綜合考慮以下幾個方面內容:其一,國家工作人員是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財物還是利用個人技術換取報酬;其二,是否確實提供了有關服務;其三,接受的財物是否與提供的服務等值。③同上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第二庭、第三庭、第四庭、第五庭書,第198頁。
明確了正當的勞務報酬與非法受賄的判斷標準,對于國有企業工程師利用自身掌握的技術在業余時間去幫助民營企業解決問題的情形,也就可以進行很好的解釋。如果國有企業工程師是利用技術去解決民營企業技術上的問題,民營企業并沒有通過國有企業工程師謀取其他不正當的利益,而且提供的服務也是等值的,則不構成受賄罪。而本案中的方俊則不同,雖然表面上看給相關單位提供了相關技術上的幫助,但是事實上只是提供了少量服務來掩蓋收受財物的事實,為的還是謀取不正當的利益。
戴某在擔任國家工作人員期間,利用為有關中小企業提供政策法規咨詢、提供創業指導、管理咨詢、聯系、組織專業服務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協助做好各專項資金申報的咨詢、輔導、初審工作等職務便利,多次收受相關企業和人員給予的錢款、購物卡等。最終法院認為,戴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④參見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2014)徐刑初字第1203號刑事判決書。
該案中戴某的行為是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還是利用熟悉政策而提供勞務幫助,這直接影響到受賄罪的成立與否。在前述方俊受賄案中,已經提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正確區分正當的勞務報酬與非法受賄的界限的判斷標準。該案和上述案件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涉案的國家工作人員都是具有相關行業技術、熟悉相關知識的人員。從戴某任職的上海市中小企業發展服務中心的工作性質來看,它是協助落實國家和該市有關中小企業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協助推進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和誠信體系建設,協調和組織中小企業跨行業、跨區域活動等的部門。因而,這本來就是扶持推廣中小企業發展的部門,所以戴某在相關企業申報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時給予幫助,應該屬于他的工作內容。判決指出戴某在相關企業申報過程及初審工作中給予幫助,但卻沒有明確說明戴某所提供的幫助內容是什么,也沒有明確解釋戴某為初審工作提供了什么幫助,這種幫助是否利用了戴某本人的職務。比如,戴某有審批初審材料的決定權,如果他否定,那么申報單位就無法進行下一關的申報,但是判決并未指出這一點,可以認為戴某本身并不具備這種決定權。另外,判決指出戴某在某公司申報國家發展專項資金時,為申報工作提供政策上的幫助,這也是戴某的工作內容,并非戴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因此,單憑判決所指出的“戴某在相關企業申報過程及初審工作中給予幫助”或者“提供政策上的幫助”等行為,就認定戴某的行為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頗為勉強。其實,如果說戴某的行為屬于他的工作內容更為妥當。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明確解釋戴某所提供的幫助內容,是判決中的缺憾。
筆者認為,戴某在進行政策咨詢、輔導及申報幫助和初審工作中給予幫助,收受財物,這種行為已經侵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導致人們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公正性喪失信任,應該認定為受賄罪。國家職務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財物,本質上符合錢權交易的特征,應當屬于受賄,在此過程中行為人出于某種考慮也會向行賄方提供個人技術服務的活動,這在原則上不能對定罪產生影響。①同前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第二庭、第三庭、第四庭、第五庭書,第198頁。綜合該案案情,戴某提供的服務和收受的財物,也不宜認定為價值相當,因為如果沒有戴某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影響,相關單位是不會提供數額如此大的財物的。此外,該案在判決書中提及,戴某所在中心規定“在專項資金申報項目初審過程中,不得對項目單位收取費用”。故將戴某的行為認定為受賄罪是妥當的。
四、“利用職務便利”與“利用工作便利”區別的必要性存在與否
(一)關于侵害的法益
法益是指,根據憲法的基本原則,由法律所保護的、客觀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脅的人的生活利益。②同前注⑥,張明楷書,第67頁。刑法上的法益,類似于我國傳統刑法理論中所說的犯罪客體,我國的犯罪客體是指犯罪所侵害的社會關系。因而,通過分析可以知道“利用職務便利”與“利用工作便利”所侵害法益的不同,這樣可以更好地理解兩者之間的區別。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貪污罪、受賄罪等職務罪的犯罪成立的構成要件。貪污賄賂罪的法益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不可收買性。因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獲取財物,所侵犯的法益最主要的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不可收買性,其次也可能包括財產的所有權。相比較而言,“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獲取財物,所侵犯的法益首先就是財產的所有權。因為“工作”本身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工作”也不像“職務”有一定的特性。雖然兩者都是利用某種手段,但是利用“職務”是利用工作中的一種職權,利用這種職權所侵犯的不僅僅是財產的所有權,更重要的職務行為本身。正因侵害法益的不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獲取財物所構成的犯罪是貪污罪、賄賂罪等職務犯罪,而只“利用工作便利條件”獲取財物所構成的犯罪只能是一些財產犯罪。
(二)關于刑事政策
從立法現狀看,我國對于職務犯罪的立法及司法解釋都帶有擴大化的趨勢。從當前的刑事政策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對職務犯罪采嚴打態勢,司法機關對于職務犯罪中“利用職務便利”有定型化傾向。但是,司法機關不能將“利用工作便利”或屬于“工作內容”的行為,一律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否則將導致職務犯罪擴大化的危險發生。
在嚴打職務犯罪的刑事政策之下,一些國家工作人員以提供勞務獲得報酬的形式受賄成為一種典型的案件。在此類案件中,國家工作人員提供勞務正當與否經常會成為爭議的關鍵點。因而,關于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有權利運用自己的相關專業知識提供勞務獲得報酬,也是一個問題。就筆者來看,一部分國家工作人員是沒有該權利的,這部分國家工作人員主要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最高人民法院“紀要”指出:“刑法中所稱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指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包括在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軍事機關從事公務的人員。”因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主要指的是《公務員法》上的公務員,《公務員法》第42條規定:“公務員因工作需要在機關外兼職,應當經有關機關批準,并不得領取兼職報酬。”
所以,筆者認為這部分國家工作人員(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沒有權利提供勞務獲得報酬的,如果他們因提供勞務獲得了報酬,只要該勞務與他們的公職工作相關,即可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收受了賄賂。因為,他們沒有提供勞務獲得報酬的權利,故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工作便利”和“利用職務便利”的涵義可以是相同的。而除此之外的國家工作人員(比如事業單位科研人員、國有企業工程師等),應該可以有這樣的權利,但前提是必須同時提供了與所收受報酬相當的勞務。對此類案件,在判斷是非法收受賄賂還是正當勞務報酬問題上,就要根據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在方俊受賄案中的指導標準進行具體判斷。
(三)小結
關于“利用職務便利”與“利用工作便利”是否有區別的必要性,筆者認為,從職務犯罪的角度看,沒有區別的必要性。例如,作為國有事業單位的普通科研人員,臨時受命管理國家社科院基金項目的資金,在管理該項目經費過程中,如果此人用假發票報銷部分經費,那么他應該構成貪污罪,此時不需要區別他的行為是利用職務便利,還是利用工作便利。
在職務犯罪與非職務犯罪的認定上,就存在區別的必要性。廣義上的利用工作便利包含了利用職務便利。如果是利用了職務便利之外的工作便利,則只構成普通財產犯罪。比如,國有企業倉庫管理人員利用到財務室報賬機會,偷窺并記住出納開保險箱時輸入的密碼,趁沒人將保險箱里的財物竊為己有,倉庫管理人員涉嫌盜竊罪,此時就有必要區別倉庫管理人員是利用職務便利還是利用工作便利。如前文所述,“利用工作便利”的范圍是比“利用職務便利”更大的,也就是說一個行為要符合“利用職務便利”,必須先符合“利用工作便利”,然后該行為必須是基于工作身份上的職權所產生的,才能符合“利用職務便利”。
因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與“利用工作便利條件”區別的根本意義在于區別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獲取財物所構成的犯罪是貪污罪、賄賂罪等職務犯罪,而只“利用工作便利條件”獲取財物所構成的犯罪只能是一些財產犯罪。
(責任編輯:杜小麗)
DF636
A
1005-9512(2015)12-0051-08
尹琳,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學博士。
*本論文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刑事法學創新學科的成果之一,也是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2015年“兩個能力建設”課題的成果。感謝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武成對本論文寫作所給予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