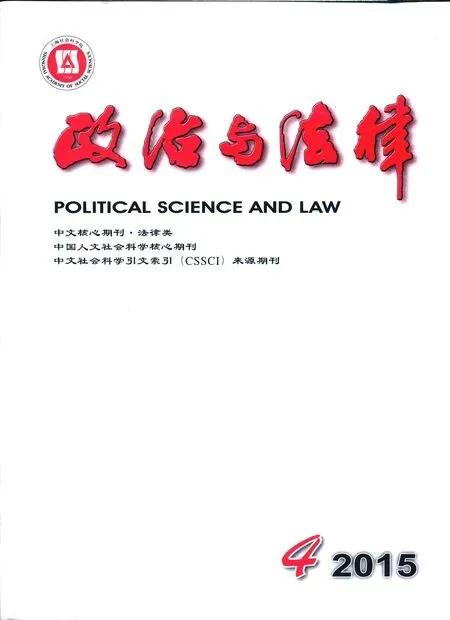論經濟性裁員中的勞動合同解除*
江鍇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200042)
論經濟性裁員中的勞動合同解除*
江鍇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200042)
我國現行勞動法對用人單位經濟性裁員作出了前提限制、程序限制、補償限制和錄用限制的規定,但對于這些限制性規定的內涵、法律性質以及具體應如何理解和適用,在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爭議。經濟性裁員中客觀存在著協商解除和單方解除兩種性質不同的行為,協商解除和用人單位單方解除應適用不同的效力判定規則。對協商解除的效力,只要其與集體合同的相關約定不抵觸,即應予以充分的尊重。對于用人單位的單方解除,則應基于合同解除權的形成權屬性,并充分考慮經濟性裁員所具有的處理集體勞動關系的特殊性質,對勞動法律就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做出的限制性規定,從個別勞動關系和集體勞動關系兩個層面進行綜合解釋:“通知工會”義務相對應的只是工會的監督權;“聽取工會或職工的意見”義務既是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程序性義務,也是其集體合同的締約義務;“裁減人員方案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義務既是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程序性義務,也是勞動行政部門依法審查集體合同的規則的體現。
經濟性裁員;勞動合同協商解除;勞動合同單方解除;集體勞動關系
一、問題的提出
用人單位通過經濟性裁員所欲實現的根本目的是在一段較短的時間內解除相當數量的勞動合同,以使相關勞動法律關系歸于消滅,因此在現實的裁員過程中,一般并存著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解除勞動合同以及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兩種情形。對于經濟性裁員,我國《勞動法》第27條①《勞動法》第27條規定:“用人單位瀕臨破產進行法定整頓期間或者生產經營狀況發生嚴重困難,確需裁減人員的,應當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后,可以裁減人員。用人單位依據本條規定裁減人員,在六個月內錄用人員的,應當優先錄用被裁減的人員。”和《勞動合同法》第41條、第42條、第43條②《勞動合同法》第41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減人員二十人以上或者裁減不足二十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單位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后,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可以裁減人員:(一)依照企業破產法規定進行重整的;(二)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的;(三)企業轉產、重大技術革新或者經營方式調整,經變更勞動合同后,仍需裁減人員的;(四)其他因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經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的。裁減人員時,應當優先留用下列人員:(一)與本單位訂立較長期限的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二)與本單位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三)家庭無其他就業人員,有需要扶養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用人單位依照本條第一款規定裁減人員,在六個月內重新招用人員的,應當通知被裁減的人員,并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招用被裁減的人員。”第42條規定:“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的規定解除勞動合同:(一)從事接觸職業病危害作業的勞動者未進行離崗前職業健康檢查,或者疑似職業病病人在診斷或者醫學觀察期間的;(二)在本單位患職業病或者因工負傷并被確認喪失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在規定的醫療期內的;(四)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的;(五)在本單位連續工作滿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五年的;(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第43條規定:“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應當事先將理由通知工會。用人單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勞動合同約定的,工會有權要求用人單位糾正。用人單位應當研究工會的意見,并將處理結果書面通知工會。”對作為裁員發動主體的用人單位設置了一系列限制性規則,有學者將其概括為前提限制、程序限制、補償限制和錄用限制。③前提限制,是指企業重整等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需裁減人員二十人以上或者裁減不足二十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百分之十以上。程序限制,是指用人單位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后,裁減人員方案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補償限制,是指用人單位應向被裁減的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錄用限制,是指在經濟性裁員的六個月內重新招用人員的,應當通知被裁減的人員,并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招用被裁減的人員。參見邱婕:《經濟性裁員中的勞動合同解除》,《中國勞動》2005年第6期。但對于這些限制性規定是否能夠既適用于協商解除又適用于單方解除,以及具體應如何適用,在理論和實踐中均存在爭議。除此之外,在適用的過程中,對于某些限制性規定的性質和內涵也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不利于這些規定實現保護勞動者的功能。這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雖然協商解除與單方解除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勞動合同解除方式,但當它們同時出現在現實的裁員過程中時,則在對其的效力判定上可能產生規則適用混淆的問題。具體而言,前述勞動法律對裁員作出的前提限制、程序限制、補償限制以及錄用限制的規則適用于用人單位單方解除的情形當無異議(前提限制是用人單位取得解除權的構成要件,程序限制、補償限制及錄用限制屬于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規則),但這些限制性規定是否應同時適用于協商解除?若非全部適用,那么哪些規定會影響協商解除的效力?這些問題并非不證自明,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最新公布的《企業裁減人員規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中,認為前提限制和程序限制均應適用于協商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企業裁減人員規定(征求意見稿)》第18條規定:“企業出現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與職工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人數達到20人以上的,應當提前30日向本企業工會或者全體職工告知有關情況,并同時將擬解除勞動合同人數報告當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xhd/SYzhengqiuyijian/201412/ t20141231_147714.htm,2015年1月12日訪問。但對未遵循該規定所作的協商解除的效力如何又未予明確。筆者對此規定的正當性與合理性表示質疑。
另一方面,對于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以實現裁員目的的情形,由于合同解除權是一種形成權,它只是給予一方的,并不需要別人的意思表示參與,而只是根據權利人自己一方的意思來發生法律效果的法律之力。⑤[德]卡爾·拉倫茨、曼弗瑞德·沃爾夫:《德國民法中的形成權》,孫憲忠譯,《環球法律評論》2006年第4期。因此依法理,在裁員中,用人單位一旦取得法定解除權,則只要依法行使解除權即可產生解除勞動合同的效果,他方的意思表示應無法影響此效果的發生。然而,《勞動合同法》第41條在對裁員所作的程序限制規則中采用了“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的表述,使得實踐中對工會或勞動行政部門是否能以自己之意思直接影響用人單位單方解除之效力產生了分歧。⑥這從各地有關規定的內容中可見一斑。例如《天津市企業經濟性裁減人員暫行規定》(津勞局[2001]241號)即認為企業對工會就裁減人員方案提出的意見必須予以修改完善,且市勞動行政部門對裁減人員方案有核準權;《無錫市勞動局關于印發〈企業經濟性裁減人員實施辦法〉的通知》(錫勞察[2001]8號)則認為勞動行政部門對用人單位提交的裁員方案只進行登記備案,無權核準。若將“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裁減人員方案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理解為用人單位取得解除權的條件,則會與《勞動合同法》第43條規定的“通知工會”義務產生矛盾;若解釋為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程序性規定,則依解除權之法理,工會及勞動行政部門將不能阻止勞動合同被解除的后果產生,就又無法實現法律限制用人單位實施不正當裁員行為的目標。因此,如何理解用人單位的“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裁減人員方案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義務的性質及其履行效果也是必須予以回應的重要問題。
二、經濟性裁員中協商解除的效力判定規則
經濟性裁員是現代社會中一種較為常見的社會現象,是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在出現經營狀況重大困難等客觀經濟情況巨大變化的情形下,于一定時間內集中使相當數量勞動合同關系歸于消滅的行為。經濟性裁員是企業在雙方約定的有效期限內非正常地終止勞動合同,即企業單方面否定了正在履行的勞動合同的效力,極大地損害了勞動者基于合同所產生的預期利益,因而很容易遭到他們的抵制與反對,從而加劇勞資矛盾,引發勞資糾紛。⑦張在范:《勞資協商的引入與我國經濟性裁員法律制度的重塑》,《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故我國勞動法針對經濟性裁員過程中的解除勞動合同行為,作出了前提限制、程序限制、補償限制和錄用限制的規定,以防止用人單位隨意裁員,維護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由于在經濟性裁員過程中發生的協商解除是不同于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一種合意解除,前述限制性規定并非均適用之。
(一)協商解除與單方解除具有不同的法理基礎
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當解除的條件具備時,因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關系自始或僅向將來消滅的行為,也是一種法律制度。⑧崔建遠主編:《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頁。盡管勞動合同是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一種特殊合同,但總體上仍須遵循一般合同解除的基本法理。勞動合同解除依解除方式的不同可分為單方解除與協商解除;⑨參見王全興:《勞動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頁。單方解除依解除權來源的不同又可進一步分為法定解除和約定解除。與單方解除不同,協商解除從本質上就是勞動合同的雙方當事人通過訂立一個以解除勞動合同為主要內容的新合同,以實現消滅勞動法律關系目的的合意行為,因此協商解除行為不是行使解除權的行為,不以解除權的存在為必要,當然,也并不排斥解除權的存在。大陸法系民法理論認為,合意解除與民法所規定的合同解除權性質不同,不適用民法關于契約解除的規定,其效力應依當事人的約定而發生。⑩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頁。
盡管協商解除和單方解除所產生的法律后果均是使合同法律關系歸于消滅,但兩者具有不同的法理基礎。對于單方解除,解除權對權利人而言是一種利益,①同前注⑧,崔建遠主編書,第197頁。故無論是法定解除中的法律配置解除權,或是約定解除中法律對解除權分配和行使的約定效力的判定,都會有較強的價值判斷體現在其中。當然,約定解除也是合同當事人通過合意的方式確定解除權的歸屬,因此法律在對其進行價值判斷的同時也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但由于協商解除是合同雙方當事人基于對合同履行情況的共同判斷所作出的解除合意,法律不會也不應對其合意背后的原因作過多的價值判斷而影響其效力。
具體而言,就法定解除而言,從學說上,法律規定的合同解除條件分為一般法定解除條件和特別的法定解除條件。一般法定解除條件是指適用于所有合同的解除條件,大致包括了合同一方當事人嚴重違約以及發生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無法實現兩種情況。前一種情況法律基于過錯原則將解除權配置于非違約方,例如《勞動合同法》第38條規定了用人單位違約或過錯情況下的勞動者單方解除權,第39條規定了勞動者違約或過錯情況下的用人單位單方解除權。后一種情況法律則基于公平原則將解除權配置于合同雙方,例如《勞動合同法》第40條第3項。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基于傾斜保護勞動者的原則,勞動法已賦予勞動者預告任意解除權(《勞動法》第31條、《勞動合同法》第37條),因此未再明示授予其不可抗力情況下的解除權,這并非勞動法違背了不可抗力下解除權配置的公平原則。特別的法定解除條件則僅適用于特定的合同,如勞動者的預告任意解除權是勞動法基于傾斜保護勞動者的立法目的所作的特殊制度安排,體現了法律對于特殊社會關系的價值判斷。
然而對于協商解除,如前所述,是合同雙方當事人基于對合同履行情況的共同判斷所作出的解除合意,盡管勞動關系具有實質不平等的特點,但解除合意是以消滅勞動法律關系為目標的,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已基本處于平等的磋商地位,且解除的原因一般無法精確查明,故對于雙方達成的解除合意法律不宜作過多的價值判斷,進而影響其效力。
(二)只有補償限制是影響協商解除效力的規范
對于協商解除,《勞動合同法》第36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勞動合同。”盡管經濟性裁員過程中,更多情況下用人單位是單方通過行使解除權的方式達到解除勞動合同的目的的,但根據法律規定,用人單位欲實施經濟性裁員必須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并形成裁減人員方案,之后還要將該方案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勞動法》第27條以及《勞動合同法》第41條)。因此,從用人單位啟動裁員程序,到最終解除相當數量的勞動合同以實現裁員目的,是要經過一個時間周期的,在這段時間中,用人單位和單個勞動者之間完全有可能就勞動合同解除事宜達成合意,以協商解除的方式解除勞動合同。
如前述,勞動合同的協商解除從本質上就是勞動合同的雙方當事人通過訂立一個以解除勞動合同為主要內容的新合同,來實現消滅勞動法律關系目的的合意行為,因此,對協商解除效力的判定只應遵循勞動合同效力判定的一般規則,即合意的意思表示真實,用人單位未免除自己的法定責任、排除勞動者權利,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勞動法》第18條以及《勞動合同法》第26條)。至于協商解除勞動合同的形式要件,盡管各地有不同的規定,但現行勞動法并未對此作出特殊要求,②參見董保華主編:《勞動合同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頁。故不宜認為協商解除之形式是影響其效力的要件。
另外,《勞動合同法》第46條規定,用人單位向勞動者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并與勞動者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鑒于在經濟性裁員過程中,用人單位是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的一方,其應當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即補償金是經濟性裁員中協商解除的生效要件。
基于此,在前提限制、程序限制、補償限制和錄用限制中,只有補償限制屬于經濟性裁員過程中協商解除的效力判定規則,在立法規范層面上,無法解讀出前提限制、程序限制和錄用限制規則會對協商解除的效力產生否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不按《勞動合同法》第41條規定的前提限制、程序限制規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達成解除勞動合同的合意,且合意中不包含后續優先錄用勞動者的內容,不會影響該解除合意的效力。筆者認為,現行勞動法符合立法規范協商解除行為效力的法理。
(三)征求意見稿將前提限制、程序限制規則適用于協商解除不具有正當性與合理性
雖然經濟性裁員規則相較一般的勞動合同解除確有特殊之處,但其主要針對的是用人單位單方解除的情形,現行勞動法并未就經濟性裁員過程中發生的協商解除作出不同于一般勞動合同協商解除的特殊規定。征求意見稿第18條的規定在其正當性與合理性上存在問題。
對于征求意見稿第18條“企業出現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與職工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人數達到20人以上的(前提限制),應當提前30日向本企業工會或者全體職工告知有關情況,并同時將擬解除勞動合同人數報告當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程序限制)”規定的性質,可以有兩種解釋:其一,該條是協商解除的效力性規定,即用人單位不按此規定執行,協商解除不生效力;其二,該條只是勞動行政部門對經濟性裁員中協商解除的管理性規定,即用人單位不按此規定執行,不影響協商解除生效,只是要承受行政法上的后果。
一方面,如果該條屬于協商解除的效力性規定,則由于作為部門規章的征求意見稿與上位的勞動法律有關協商解除的效力規定相沖突,而不具有正當性。另一方面,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說明,作出該規定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減輕規模性解除勞動合同對職工和社會的影響”,③參見《關于〈企業裁減人員規定(征求意見稿)〉的說明》,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xhd/SYzhengqiuyijian/201412/ t20141231_147714.htm,2015年1月12日訪問。如果該條僅僅是協商解除的管理性規定(先不說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也很成問題,例如協商解除數量的計算周期是多久),則似乎較難實現這一立法目標,因而也不具有合理性。
其實,即使征求意見稿第18條作為協商解除的效力性規定具有正當性,用人單位不履行告知工會和勞動行政部門的義務即否定協商解除效力的做法,也很難實現“最大程度減輕規模性解除勞動合同對職工和社會的影響”的目的。畢竟協商解除是當事人之間的解除合意,其化解矛盾的效果大大優于用人單位的單方解除,簡單通過立法直接限制協商解除效力的做法并非最優選擇。
三、經濟性裁員中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規則具有特殊性
(一)影響經濟性裁員單方解除效力的因素
一方面,用人單位行使法定解除權的前提是依法取得解除權,因此依法取得解除權是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行為得以生效的因素之一。《勞動合同法》第41條規定,當出現以下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的情形時,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1)依照企業破產法規定進行重整的;(2)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的;(3)企業轉產、重大技術革新或者經營方式調整,經變更勞動合同后,仍需裁減人員的;(4)其他因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經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這里,企業“重整”、“經營發生嚴重困難”、“經營方式調整”、“客觀經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就是用人單位取得法定解除權的條件,只要客觀上出現前述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即取得法定解除勞動合同的權利。
另一方面,取得解除權不過是合同解除的前提,由于我國法律并未采取當然解除主義,當用人單位取得法定解除權后,合同并不必然解除,欲使它解除,一般還需要解除行為。④同前注⑧,崔建遠主編書,第190頁。解除權人行使解除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也會直接影響單方解除的效力,例如《勞動合同法》第43條規定了用人單位在取得法定解除權后,在解除勞動合同前,要將理由通知工會。當然,在符合法定解除權行使要求且不與法律規定相沖突的前提下,合同當事人也可對解除權行使的具體方式進行協商。
(二)程序限制規定不是用人單位取得解除權的條件
《勞動合同法》第41條規定:“用人單位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職工的意見后,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可以裁減人員。”如本文開頭所述,對此規定存在兩種可能的解釋:其一,這種程序限制是用人單位取得法定解除權的條件;其二,這種規定是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程序規則。
對于第一種解釋,筆者認為并不成立,理由是,若將該規定定性為用人單位取得法定解除權的條件,將會使《勞動合同法》第43條的規定顯得多余。《勞動合同法》第43條規定:“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應當事先將理由通知工會。”依文義解釋,這里用人單位的“通知工會”義務是其取得解除權后實施“單方解除勞動合同”行為時的解除權行使程序要求。如果說在經濟性裁員中,用人單位履行向工會或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意見并將裁員方案報告勞動行政部門的義務是用人單位取得解除權的條件,那么在用人單位取得解除權后“單方解除勞動合同”之時,即已經向工會履行了說明情況并聽取意見的義務,再要求其滿足“應當事先將理由通知工會”的解除權行使程序要求,就顯得有悖邏輯而且多此一舉。
然而,如果按照第二種解釋,認為《勞動合同法》第41條的程序限制規定僅僅是用人單位取得解除權后在行使解除權時應遵循的程序規則,那么又會存在以下兩方面的障礙:第一,仍然會與《勞動合同法》第43條的規定有重合之處;第二,合同解除權作為一種典型的形成權,其與請求權最大的區別即在于,它只是給予一方的,并不需要別人的意思表示參與,而只是根據權利人自己一方的意思來發生法律效果的法律之力,⑤同前注⑤,卡爾·拉倫茨、曼弗瑞德·沃爾夫文。如果向工會或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意見并將裁員方案報告勞動行政部門的義務對用人單位而言只是行使解除權的程序規定,那么依形成權法理,工會或全體職工以及勞動行政部門將不能依自己之意思來阻止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后果的發生,這樣就會使立法限制用人單位違法裁員的目的落空。
2014年,海委將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落實中央關于水利改革發展的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和水利部的各項工作要求,積極踐行可持續發展治水思路,全面加快海河水利改革發展,積極推進各項工作取得新成效。
對于第一個障礙,由于裁員只是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一種情形,還存在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其他情形(例如因勞動者的過錯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參見《勞動合同法》第39條),而《勞動合同法》第43條是針對所有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程序性規定,所以經濟性裁員中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程序性規定在內容上與其有重合之處(即用人單位均須將解除理由通知工會)并非不合邏輯,且鑒于經濟性裁員對勞動者和社會產生的較大影響,立法在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一般程序規則基礎上作特殊規定也具有合理性。
對于第二個障礙,由于涉及的問題較多,實有必要對其展開詳細的分析論述。
四、對經濟性裁員中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規則的解釋
其實,要解決《勞動合同法》第41條能否有別于《勞動合同法》第43條規定的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程序規則,從而實現立法嚴格、有效限制用人單位違法裁員目標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理解用人單位的“應當事先將理由通知工會”的義務(以下簡稱:通知工會義務)以及“向工會或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意見并將裁員方案報告勞動行政部門”的義務(以下簡稱:聽取工會意見義務)的內涵及其關系。
(一)通知工會義務相對的是工會的監督權
對于勞動法在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過程中設置通知工會義務的目的,有學者概括為立法認可“工會對用人單位單方解除的干預”,從而實現工會的維權職能,并進而依現行法(《勞動合同法》第43條、《勞動法》第30條及《工會法》第21條)規定,將工會“干預”的內涵總結為:(1)工會對辭退有知情權;(2)工會對不當辭退有要求糾正權;(3)工會有義務支持和幫助勞動者提起仲裁和訴訟。⑥同前注⑨,王全興書,第181頁。筆者贊同這種對工會干預內涵的表述,但認為對干預的法律性質及法律效果有必要進一步澄清。
首先,就工會的知情權而言,其是指工會有知曉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行為的權利,用人單位只需要將解除勞動合同的理由通知工會即可,所以這里并不存在工會以其意思直接影響用人單位作出單方解除的效力的空間。
其次,雖然若工會發現用人單位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勞動合同約定而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情況時,有權要求用人單位糾正或重新處理,但是,一方面,立法并未就用人單位“不糾正或不重新處理”的后果作出規定,所以工會之意思表示在此并不能直接產生否定用人單位單方解除行為效力之效果;另一方面,立法又規定了工會有義務支持和幫助勞動者提起仲裁和訴訟,若工會之要求糾正權即可否定用人單位單方解除之效力,那么再規定工會的仲裁和訴訟幫助義務就多此一舉。
最后,立法之所以規定在勞動者就用人單位的解除行為申請仲裁或提起訴訟時,工會有支持和幫助的義務,正說明了勞動法認為在對解除權效力存有異議的情況下,只有解除權行使對象(此處指勞動者)通過仲裁或訴訟的方式才能由仲裁機構或法院對此予以確認,即只有仲裁機構和法院才是判定解除行為效力的合法主體。
綜上,無論是知情權、要求糾正權、還是支持和幫助勞動者提起仲裁和訴訟的義務,總體上用人單位的通知工會義務相對應的是工會對用人單位是否依法依約行使解除權的一種監督,要求糾正權無法直接產生否定用人單位單方解除效力的后果。
(二)聽取工會意見義務的內涵應不同于通知工會的義務
在對《勞動合同法》草案進行討論的過程中,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提出:“現在草案第41條規定經濟性裁員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聽取意見當然是很好的,比不聽意見是很大的進步。我有一個擔心,我擔心本法對用工單位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的限制性規定失去意義。因為企業是不是必須裁員,是不是經濟性裁員,到底應該裁多少?我認為這需要協商和監督的。如果用人單位只是聽取意見,很容易因為用人單位一意孤行而出現職工群體性事件。最好的辦法,是用人單位與工會商量或者召開職代會來討論決定。職工是通情達理的,只要通過討論,就會比較圓滿地解決,否則,就可能激化勞動關系雙方的矛盾。”⑦參見中國人大網:《勞動合同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與終止——分組審議勞動合同法草案發言摘登(三)》,http://www.npc.gov. cn/npc/xinwen/2007-04/29/content_364967.htm,2014年12月15日訪問。
這位委員對聽取工會意見義務的理解具有代表性。筆者以為,如“聽取工會意見”對用人單位而言只有“聽”是必須履行的義務,“取”則是可以選擇的權利,那么用人單位自然容易“一意孤行”。若依此解釋聽取工會意見義務,事實上就會使這一義務的設置失去現實意義,立法只需規定前半句“向工會或全體職工說明情況”即可。但若只規定“向工會或全體職工說明情況”的義務,則又會與通知工會義務產生的效果相同。如此,則難免使人對立法分兩個條款、以不同的表述規定會產生同樣履行效果的義務的做法的科學性和必要性產生質疑。因此,較為合理的解釋應是,聽取工會意見義務的內涵是完全不同于通知工會義務的,只有在“聽”和“取”均是用人單位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的前提下,即工會可以否定用人單位單方解除行為效力的情況下,立法限制用人單位隨意裁員的目標才能實現。然而,如前所述,這里就出現了現實需要和形成權法理之間的矛盾。
(三)個別勞動關系層面聽取工會意見義務的內涵
有學者指出,合同解除權行使程序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提供行使合同解除權的有效方式和途徑;第二,是對權利人的有效約束;第三,是對合同相對人的有效保護。⑧參見郝磊:《合同解除權制度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207頁。我國勞動法規定,在經濟性裁員中,用人單位必須首先“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其次“聽取工會或職工的意見”,最后“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才能裁員。筆者以為,先不論這里工會、勞動行政部門之意思表示對用人單位解除行為效力的影響,至少在經濟性裁員的個別勞動關系層面,立法的前述三點要求首先構成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法定程序當無疑義。也就是說,用人單位在取得經濟性裁員法定解除權后,首先必須依法定程序(即“說明——聽取——報告”程序),才可以將解除的意思最終告知勞動者以達到解除合同的效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前述合同解除權行使程序的意義在經濟性裁員的立法中已經得到充分體現。
然而,如果僅僅是一種程序性規則,則工會和勞動行政部門均無法對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效力予以直接干涉,單個勞動者要對用人單位的解除權提起異議之訴(包括申請仲裁)又不方便(即使有工會的支持和幫助),這樣就會使人感到立法面對經濟性裁員這一特殊社會現象時保護弱勢勞動者一方的力量仍顯不足。難怪有人大代表在審議立法過程中提出:“‘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可以裁減人員’,建議修改為‘裁減人員的方案經過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獲準后(或幾個工作日后),可以裁減人員’。理由是他一報告就可以裁員,勞動行政部門就沒有審定的時間了,是不是可以給一個時間,或者批閱以后來裁員,以減少當地政府協調這方面問題的難度。可以關口前移,在裁減人員之前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既然報告了,就要把好這個關。”⑨參見同前注⑦,中國人大網文。但這種認為勞動行政部門可以通過行使行政權來使自己的意思表示直接否定解除行為效力的觀點,顯然是違背法理的,并不可取。因此,欲使工會和勞動行政部門之意思表示能直接限制用人單位在經濟性裁員中濫用解除權的行為且不違反法理,就需要更系統全面地對勞動法進行解讀。
(四)集體勞動關系層面“聽取工會意見”義務的內涵
從個別勞動關系層面言,經濟性裁員中用人單位取得并行使法定解除權行為的性質與其取得并行使其他法定解除權行為的性質并無區別,但經濟性裁員同時關系到眾多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問題,故經濟性裁員從實質上已非單純的處理個別勞動合同的行為,其也是一種處理集體勞動關系的法律活動。集體勞動關系是以個別勞動關系為基礎,以團結權為保障,以雇員團體與雇主或雇主團體為主體而建立的法律關系。⑩謝德成、王天玉:《集體勞動關系的法律目標及規范重點》,《當代法學》2010年第2期。盡管經濟性裁員在個別勞動關系層面表現為用人單位單方行使法定解除權以解除勞動合同,但其同時應適用集體勞動關系相關法律的規定。法律調整集體勞動關系的重點之一即在于規范集體協商,完善集體合同立法,①參見同上注,謝德成、王天玉文。而我國現行法也已就集體協商、集體合同作出了相關規定(主要有《勞動法》第33條至第35條、《勞動合同法》第51條至第56條以及《集體合同規定》),其中關于集體協商內容的規定就包括了裁員(《集體合同規定》第8條第10項以及第18條②《集體合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第22號)第8條規定了集體協商雙方可以就裁員事項進行集體協商,簽訂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其第18條規定:“裁員主要包括:(一)裁員的方案;(二)裁員的程序;(三)裁員的實施辦法和補償標準。”)。由此可見,對于裁員方案、程序、實施辦法及補償標準,用人單位與工會完全可以通過集體協商簽訂集體合同的方式予以確定。
其實,合同解除權的相對方確實也是可以通過與解除權人協商來確定行使解除權的具體方案的,但這種個別協商存在的最大問題在于,基于解除權的形成權屬性,即使協商不成,也無法影響解除權人單方解除合同的效力。但前已述及,經濟性裁員并非單純的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行為,還是一種處理集體勞動關系的活動。筆者認為,聽取工會意見義務的內涵,除了在個別勞動關系層面是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法定程序,在集體勞動關系層面還應解釋為是法律為用人單位設置的集體合同締約義務,理由如下。
第一,從法理上來看,只有解釋為集體合同的締約義務,才能正當地實現工會和勞動行政部門的意思表示對用人單位的解除行為效力產生直接影響的目標。一方面,前已述及,用人單位與工會可以就裁員事項進行集體協商并簽訂集體合同;另一方面,根據勞動法理,集體合同的效力高于勞動合同,③對此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集體合同的效力絕對高于勞動合同;另一種觀點認為只有在集體合同的內容相較勞動合同對勞動者更有利的情況下其效力才高于勞動合同。參見談育明:《集體協商機制——集體協商與集體合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47頁。因此工會可以將對裁員方案的意見體現在集體合同之中,從而對抗用人單位解除單個勞動合同的效力。
第二,從文義解釋來說,聽取工會意見義務不僅包含“聽”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取”。用人單位“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后,對于工會或職工就此提出的意見用人單位并非“聽”過即可,更要通過集體協商,“取”雙方之合意以集體合同的形式呈現出來,才能算是完整履行了自己的法定義務。
第三,從現實功能來講,也宜將聽取工會意見義務解釋為集體合同的締約義務。首先,用人單位無論是依《勞動合同法》第40條第3項(即因情勢變更解除勞動合同)還是依第41條取得法定解除權,均適用第43條的通知工會義務。而如前所述,通知工會義務相對應的僅是工會的監督權,一旦工會發現用人單位報告的解除理由雖然是基于《勞動合同法》第40條第3項,但實際用人單位已經“裁減人員二十人以上或者裁減不足二十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百分之十以上”,工會即可直接以其意思表示與用人單位訂立集體合同并進而直接影響用人單位的單方解除效力,這能處理好通知工會義務與聽取工會意見義務之間的關系,使兩者“無縫對接”。其次,將聽取工會意見義務解釋為集體合同的締約義務,意味著第41條規定的要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的“裁減人員方案”是經用人單位與工會集體協商后訂立的集體合同,能適用集體合同的生效規則(《勞動合同法》第54條),從而使第41條中勞動行政部門的作用得以明確,即勞動行政部門應自收到作為集體合同文本的“裁減人員方案”之日起十五日內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若未提出異議,“裁減人員方案”即行生效,若有異議,則可依《集體合同規定》第44條至第46條)處理。④其實已經有地方上的相關規定照此規則來解釋《勞動合同法》第41條的“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可以裁減人員”,例如《重慶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關于加強我市企業規模性裁減人員監管工作的通知》(渝勞社辦發[2008]292號)。最后,將“聽取工會或職工的意見”解釋為集體合同的締約義務,既能避免用人單位通過選擇適用法律來規避法律對其裁員行為的限制性規定,實現工會和勞動行政部門以其意思直接限制用人單位濫用解除權從而有效保護勞動者的目標,又不違背法理,使工會和勞動行政部門的“干預”行為變得名正言順。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指的用人單位的集體合同締約義務有兩個方面的內涵:若用人單位之前未就裁員事項與工會簽訂集體合同的,則在其行使解除權實施裁員之前就必須與工會就裁員的相關事項展開集體協商、簽訂集體合同,且最終的解除方案不得低于集體合同約定的對勞動者的保護標準;若用人單位就裁員問題已經和工會簽訂了集體合同,則在其行使解除權之前必須就其解除行為是否與集體合同的相關內容相沖突接受工會的審查,當然用人單位與工會也可對集體合同的內容進行協議變更,但最終的解除方案還是不得低于集體合同約定的對勞動者的保護標準。
至于在經濟性裁員中對用人單位不履行該集體合同締約義務的救濟,則可依集體勞動關系法律的相關規定執行:集體協商過程中發生爭議,雙方當事人不能協商解決的,當事人一方或雙方可以書面向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協調處理申請;未提出申請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認為必要時也可以進行協調處理(《集體合同規定》第49條)。協調處理集體協商爭議應當按照以下程序進行:受理協調處理申請;調查了解爭議的情況;研究制定協調處理爭議的方案;對爭議進行協調處理;制作《協調處理協議書》(《集體合同規定》第53條)。《協調處理協議書》應當載明協調處理申請、爭議的事實和協調結果,雙方當事人就某些協商事項不能達成一致的,應將繼續協商的有關事項予以載明。《協調處理協議書》由集體協商爭議協調處理人員和爭議雙方首席代表簽字蓋章后生效。爭議雙方均應遵守生效后的《協調處理協議書》(《集體合同規定》第54條)。因履行集體合同發生的爭議,當事人協商解決不成的,可以依法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集體合同規定》第55條)。
五、結語
既然明確了經濟性裁員也是一種處理集體勞動關系的活動,用人單位與工會應當就裁員事項通過集體協商簽訂集體合同,那么協商解除確定的解除方案也應當不能低于集體合同確定的對勞動者的保護標準,低于的部分應適用集體合同確定的標準。因此筆者建議,征求意見稿第18條可修改為:“企業出現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與職工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的,應當將解除方案告知本企業工會,工會發現解除方案有低于集體合同確定的裁員方案對勞動者的保護標準的,應通知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適用集體合同確定的相關標準。”
對于用人單位的單方解除,應充分考慮經濟性裁員所具有的處理集體勞動關系的特殊性質,對勞動法做出的特殊限制性規定從個別勞動關系和集體勞動關系兩個層面進行綜合解釋:通知工會義務相對應的只是工會的監督權;“聽取工會或職工的意見”既是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程序性義務,也是其集體合同的締約義務;“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可以裁減人員”既是用人單位行使解除權的程序性義務,也是勞動行政部門依法審查集體合同的規則的體現。
其實,集體勞動關系的本質是反映和揭示勞動過程中從屬性的人身關系與物質利益關系,它的基本表現方式則是對立與合作,而且,最為重要的是,集體勞動關系包含著集體主義的積極要素,它既能滿足資方的需要,又能滿足勞動者的需求。⑤同前注⑩,謝德成、王天玉文。就經濟性裁員來說,盡管出于保護弱勢勞動者的目的,立法對用人單位的裁員行為作出了諸多限制性規定,但有一些規定(如《勞動合同法》第41條中的優先留用規定)對于勞動行政部門的監督而言存在很大難度。究其原因,就在于這些事項的決定往往被用人單位內部的經營管理狀況所左右,作為外部力量的行政部門無從知曉。因此,對于經濟性裁員的規范,不能只依賴行政權力的直接介入,用人單位與工會和職工的充分協商才是關鍵。
(責任編輯:陳歷幸)
DF472
A
1005-9512(2015)04-0111-10
江鍇,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博士研究生,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人員。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集體勞動爭議處理和應對的法律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4AZD04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