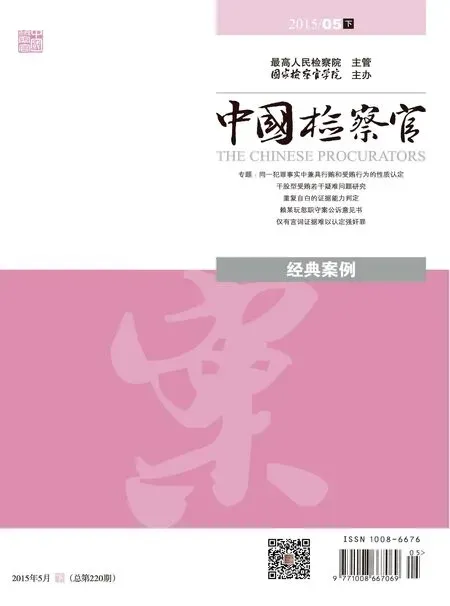犯罪行為定性中的民事身份因素淺析
文◎楊祖剛周明軍
犯罪行為定性中的民事身份因素淺析
文◎楊祖剛*周明軍**
股東是公司的出資人,享有公司的股權及其他法定權利,公司股東與公司之間的這種民事身份關系在特定的情形下,對股東犯罪行為的定性有較大的影響。因此在對股東的犯罪行為定性時要全面、理性的分析股東與公司的身份關系,使得定性準確。
股東 受賄 職務 共犯
本案中,曾某是信達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股東,股東是公司的出資人,享有公司的股權以及法定權利,公司股東與公司之間的這種民事身份關系在特定的情形下,對股東犯罪行為的定性有較大的影響,對這種關系的認識不同,得出的結論則截然不同,因此在對股東的犯罪行為定性時要全面、理性的分析股東與公司的身份關系,使得定性準確。
一、股東身份對曾某行為定性的影響
(一)曾某作為信達房地產公司的股東,能否成為收受信達房地產公司賄賂的受賄人
在案件辦理過程中,關于股東能否成為收受自己持有股份的公司賄賂的受賄人,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股東與公司關系密切,公司的利益即為股東的利益,股東收受公司的賄賂相當于是自己收受了自己的賄賂,與邏輯不符,所以公司股東不可能成為收受本公司賄賂的受賄人。另一種觀點認為,公司與股東雖有利益上的牽連,卻是相互獨立的法律主體,各有各的法定權利和義務,兩者之間完全可以存在各種社會交易,因此在特定情況下股東可以成為收受自己持有股份的公司賄賂的受賄人。筆者贊同后一種觀點。首先,我國《公司法》第3條明確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股東履行出資后,享有公司對應的股權,出資財產的所有權屬于公司,由此可知,股東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以及股東與公司的主體身份不能劃等號,兩者是相互獨立的法律主體,相互之間可以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發生各種法律關系。其次,我國《刑法》將公司納入了單位犯罪的主體范圍,這一規定明確體現出公司具有獨立的主體身份性質,且明確將公司行為與股東的個人行為區別開來。單位犯罪包括雙罰制,既處罰公司也處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責任人。所以公司犯了罪,并不等于是公司的股東犯了罪,由此可見在我國的刑法理論和規定中,公司與公司的股東是兩個不同的且相互獨立的法律主體,兩者均可能成為犯罪主體。
本案中,曾某為信達房地產公司的股東,與信達房地產公司是兩個不同的法律主體。曾某作為自然人,雖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但可與國家工作人員相互勾結,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之便,為信達房地產公司謀取利益并收受好處費,與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共犯。因此,曾某與國家工作人員相互勾結收受信達房地產公司賄賂的情形,可以成為共同受賄人,曾某具有的公司股東的身份不影響其受賄罪共犯的認定。
(二)曾某受信達房地產公司的委托代表公司給向某行賄的行為,是否屬于職務行為
《現代漢語詞典》將“職務”一詞解釋為職位所規定應承擔的工作。職位即崗位,在企業中是指一個企業在有效時間內給予某一員工的特別任務及責任。職務行為是某一組織中的工作人員為履行工作職責所為的行為。本案中,曾某是信達房地產公司的股東。根據《公司法》第4條規定:“公司股東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股東對公司的重大事務享有參與決策的權利,但并不表明股東可以直接操控公司的運作。公司的股東如果只具有股東身份,沒有擔任公司的管理者或經營者,其行為不能視為職務行為。即使在公司中擔任一定職務,但其行為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規定,超出了其職責范圍,也不能認為是其履行職務的行為,曾某作為信達房地產公司的的股東,受委托代表公司向向某行賄的行為是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不能認定是履行職務的行為,其在接受公司委托給向某行賄的過程中通過欺騙的手段侵占公司財物,不能認定利用了職務便利,不能定性為職務侵占罪,而認定為詐騙罪較為妥當。
二、曾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是受賄罪的共犯
通過上述民事身份因素對犯罪行為定性影響的分析,結合案件的整個犯罪事實,筆者認為曾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與國家工作人員向某構成受賄罪的共犯。
(一)主體身份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規定:“根據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曾某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其與國家工作人員向某相互勾結,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為信達公司謀取不正當利益,曾某與向某共同收受了500萬元行賄款。曾某的股東身份并不影響其成為收受信達房地產公司賄賂的受賄人,曾某與向某依法應認定為受賄罪的共犯。
(二)主觀方面
曾某與向某通謀,主觀上有為信達房地產公司謀取利益收受賄賂的犯罪故意,且這種犯意貫穿于整個犯罪事實。首先,在曾某得知城市建設投資公司有土地項目進行招商后,便找到負責項目招商工作的向某,并與向某共謀,由曾某尋找開發商,向某利用職權保證項目由曾某找來的開發商承接,并提高開發商的房屋產權比例,兩人從開發商處收取好處費平分,這是曾某與向某收受賄賂的事前通謀。其次,曾某與趙某等人成立信達房地產公司承接商品房建設項目,六股東商定將500萬元用于送禮,曾某將此信息告知了向某,向某表示同意,并表示愿意給信達房地產公司提供幫助,這是曾某與向某的事中通謀,兩人對受賄的金額達成共識。最后,曾某實際向向某轉交行賄款,并與向某商定分配方案,向某分得210萬元,曾某分得290萬元。由此看出,從預謀受賄到商定受賄金額再到分配受賄款,曾某與向某的通謀過程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完整性,貫穿于整個犯罪事實的發展過程。
(三)客觀行為方面
曾某與向某相互勾結,通過利用向某的職務之便,幫助信達房地產公司謀取利益,收受了信達房地產公司500萬元賄賂。城市建設投資公司的土地招商項目由公司的經營科負責招商,向某作為經營科的科長負責項目招商的具體工作。向某接受信達房地產公司的請托,在土地招商項目招投標時,利用職務便利給信達房地產公司提供了幫助,使得信達房地產公司通過圍標的非法方式獲取了土地招商項目的開發權,然后向某又幫助信達房地產公司對項目房屋產權的分配比例提高了5%。隨后信達房地產公司將用于送禮的500萬元現金交給了曾某,曾某隨即與向某進行了分贓。
(四)客體方面
曾某與向某共謀,利用向某的職務便利,幫助信達房地產公司通過圍標的方式競得土地項目開發權,事后收受信達房地產公司500萬元好處費的行為,嚴重損害了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和國家的利益,也嚴重損害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應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三、曾某犯罪金額的認定
通過對犯罪構成四要件的綜合分析,曾某與向某的行為應構成受賄罪共同犯罪。還需要強調說明的是,在辦案過程中有觀點認為,曾某通過欺騙的手段侵占了信達房地產公司290萬元錢財,應構成職務侵占罪。筆者認為,曾某將290萬元錢據為己有并不是其通過欺騙手段侵占信達房地產公司財物的結果,而是其與向某共同受賄分贓的結果。首先,曾某與向某從一開始便相互勾結,兩人皆有通過土地招商項目從開發商處拿好處費的意圖。其次,曾某雖然在未與向某商定的情況下對趙某等股東提出要500萬元用于送禮,但其在事后把趙某等人愿意用500萬元送禮的事情告訴了向某,并獲得了向某的同意。曾某從信達房地產公司拿到500萬元后,也明確告知向某拿到的好處費金額是500萬元,并與向某商量好處費的分配方案。因此曾某對其他股東提出要500萬元送禮并不存在欺騙故意,是曾某想與向某從信達房地產公司收取500萬元好處費這個主觀意圖的外在表現,這種意圖也得到了向某的同意。所以,曾某并沒有侵占信達房地產公司財物的主觀意圖,其對趙某等股東提出需要500萬元送禮的行為是其與向某共同受賄行為的組成部分。曾某將290萬元錢據為己有的行為不能構成職務侵占罪,也不能構成詐騙罪,而是與向某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受賄金額為500萬元。
*湖南省辰溪縣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局長[419500]
**湖南省辰溪縣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419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