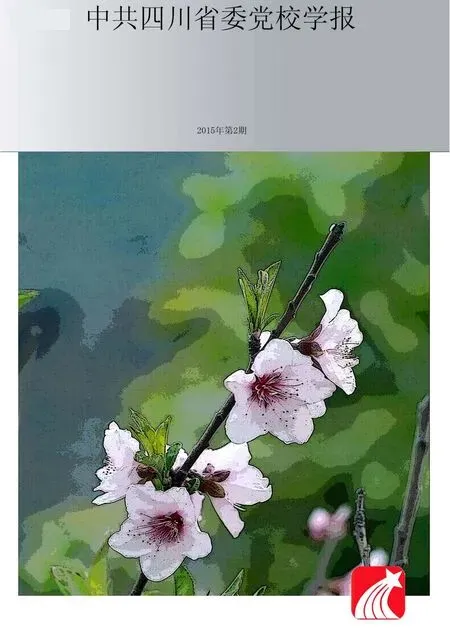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發展小城市的必要性探討
李 崑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院,四川成都 610071)
?
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發展小城市的必要性探討
李 崑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院,四川成都 610071)
城鎮化;小城市;體制改革
小城市是我國城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城鎮化一般規律看,小城市在為居民創造較好的公共服務、提高居民參與發展能力方面確有必要性;從我國城鎮化戰略與進程看,沒有相應的體制改革,就不會有小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從發展現實需求看,小城市是城市帶動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平臺。借鑒國際經驗,在小城市的發展中,政策和制度需要鎖定作為作用對象的小城市;在政策指向上,“人”的因素應當重于“城”的因素;行政體制是否有效,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居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是否得到發揮,是小城市戰略能否成功的關鍵。
小城市是我國城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前的城鎮化戰略層面上,中小城市作為城市網絡的必要構成部分,已經得到重視和強調。但理論上是否將中小城市作為城鎮化戰略的重要內容,爭論是十分激烈的,存在相當強的反對聲音。有必要在理論層面對小城市發展的價值進行必要探討,以厘清發展問題,理順發展思路。
一、從城鎮化一般規律看發展小城市的必要性
城鎮化是所有國家和地區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必須經歷的過程。在理論中,城鎮化有多重含義。從社會學角度看,城鎮化是一個創新觀念和實踐由城市向郊區擴散的過程,是社會價值與社會治理在更大規模上實現的過程;從人口學角度看,城鎮化是一個城市人口占比不斷提高的過程,是人類居住地不斷演進和功能完善、居民福利和權利得到持續保障的過程;從發展經濟理論的角度看,城鎮化是一個經濟增長和社會分配演進的內在構成部分;從空間經濟理論的角度看,城鎮化是一個城市空間規模、密度和空間拓展活動變化的過程。
總結而言,城鎮化的實質是適應生產力發展規律的資源集聚和配置過程,核心是農業人口的非農化。在當前的階段,就小城市發展而言,以下五個層次的城鎮化均有其現實的指向和意義。其一,從工業化的角度看,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社會過程。其二,從資源配置和利用的角度看,城鎮化是資源配置手段由傳統的非市場化配置轉向市場化配置的過程,是土地、資本和勞動等資源利用高效化的過程。其三,從財富的角度看,城鎮化是工業經濟所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形式多元化、價值穩定化的過程。換言之,城鎮就是居民財富的載體,如果它足夠健康的話。其四,從農民的角度看,城鎮化首先是一個剝奪作為“農民”的人的過程,其次又是一個賦予被剝奪的“農民”“市民”身份的過程。傳統的城鎮化兩者分離,現代的城鎮化要求兩者融合。
工業化作為一個經濟組織和社會結構演進的一般化過程,在現代城市的發展中起著基礎性作用。不同的工業化水平決定不同的城市發展水平。從發展階段上看,城鎮化可以分為工業化時期的城鎮化(以生產的集中為主要特征)和后工業化時期的城鎮化(以社會勞動分工的高度復雜化為主要特征)。社會勞動分工的高度復雜化、產品交易結構的成熟化以及區域勞動市場結構的動態化是城市作為一個工業化子過程的一般性特征(Scott,1986)。從人口遷移動力機制上看,城鎮化進程的快慢取決于三個因素,即人口自然增長過程中城鄉差距的大小、城鄉之間人口遷移趨勢以及新城市區域的持續出現;第二個因素,即城鄉之間人口遷移的趨勢是決定城鎮化進程的關鍵性因素,這種遷移是對工業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勞動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空間不平衡的必然反應(Ledent,1982)。
從世界范圍看,城鎮化進程經歷了一個由加速發展到減速發展的過程。1800年,世界城鎮化水平僅為2.5%,在超過3%的年均增長速度的支撐下,到上世紀中葉,世界城鎮化的水平已達到30%,今天,世界城鎮化平均水平已超過50%,到2030年,城鎮化增速將減緩到1.5%,即使在這一速度下,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人口比例都將超過農村人口比例(UN,2008)。這一進程中的各國城鎮化,既有共性,也有明顯的差異。從空間格局來看,發達國家的城鎮化在經歷了大都市區的高速發展(集中化)后,單核模式已被更為多元化的發展模式取代,先后出現了郊區城鎮化(分散化)、城市群和城市帶(一體化和區域化)等不同的階段。而在發展中國家,一方面也出現了大都市區快速發展的情況,但同時也還存在著大量半城鎮化(Periurbanization)現象。就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而言,城鎮化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有其消極的一面。概言之,城鎮化在提供了發展手段、解決了發展問題的同時,也創造了新的發展問題。今天,大都市區、城市群和城市帶已經成為城鎮化的主流模式。①因此,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城鎮化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過程。
從城市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出于資源的限制和競爭的影響,小城市的數量遠比大城市要多。小城市的發展歷來就是城市研究的重要內容。但對于理想的城市規模大小,理論研究并無確定的實證證據和理論分析支撐。早在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0)的“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論中,圍繞中心地,按照人口、市場影響范圍和功能控制關系,就對不同等級的中心度進行了劃分和研究。現代城市理論研究眾多。總括而言,現代研究認為,城市的功能和空間地理位置對城市規模的大小有直接的影響;城市規模的擴張速度一般快于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速度,慢于城市生產要素的集聚和發展速度。對于小城市而言,盡管其作為一個大的市場網絡中的節點,對于周邊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有積極的帶動作用,但就一個工業化過程而言,如果沒有一個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網絡做支撐,中小城市的發展條件不可能比大城市好。甚至在一些只能有中小城市存在的區域,如果沒有城市極核的存在,整個區域被邊緣化的可能性將大大提高(Perlik et al., 2001)。
這是僅僅從經濟增長出發的觀點。如果將發展的重點從產業轉移到居民的福利,那么小城市的發展就有著充分的價值。相對于投資效率較高的大城市而言,小城市在為居民創造較好的公共服務、提高居民參與發展能力方面確實有其必要性。隨著大城市的過度城鎮化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問題逐漸顯現,過去城市發展理論所指出的“擴散效應”并沒有出現,更多地是大城市無止境地吸納周邊生產要素的“回波效應”。在這樣的背景下,小城市的發展不僅在理論上已經得到充分的重視,而且在實踐中,小城市發展戰略也已經為很多國家所采納,成為城市發展戰略的內在構成部分。
必須認識到,小城市的發展面臨著投資效率、城鎮化成本、城鎮傳統地位以及體制等四大方面的約束。這些約束性因素,并非不能改變。觀念的轉變至關重要。只要產業選擇思維發生改變,以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真正能夠實現,那么投資效率的約束就會自然消失;只要將城鎮化的社會成本顯性化,納入到城市發展的基本考量標準中,對大中小城市發展成本的權衡結果也會隨之逆轉;只要在一個覆蓋面積更廣,影響人群更大的城市網絡中統籌考慮大中小城市的發展路徑,城市傳統地位的約束就會匿于無形。
二、從我國城鎮化戰略與進程看小城市發展的必要性
自1949年始,我國的城鎮化可以分為四個時期(李善同,2008),即1949~1957年的起步時期、1958年~1978年的不穩定發展時期、1979年~1999年的穩定快速發展時期以及2000年至今的加快發展時期。②
小城鎮的發展則表現出與城市發展不同的特征。改革開放以前,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小城鎮發展極其緩慢,數量絕對下降。1978年改革開放后至1994年,農業經濟快速恢復,相對而言,城市經濟,尤其是大城市經濟發展較慢,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村小城鎮發展速度較快。1979年十一屆四中全會指出,“有計劃地發展小城鎮建設和加強城市對農村的支援。這是加快實現農業現代化, 實現四個現代化, 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的必由之路。……我們一定要十分注意加強小城鎮的建設, 逐步用現代工業交通業、現代商業服務業、現代教育科學文化衛生事業把它們武裝起來, 作為改變全國農村面臨的前進基地”。1980 年國務院頒發《批轉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紀要》中指出,“依托小城鎮發展經濟, 有利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 有利于就地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 有利于支援農業和促進當地經濟文化發展, 有利于控制大城市的規模。從長遠看, 對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 也有重要的意義”。
隨著限制大城市、發展小城鎮政策的明晰和鄉鎮經濟的活躍,1984 年至1994 年, 全國建制鎮從6211個增加到15160個。1998年,特大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下降到36.6%。1994年以后,城市經濟的活躍在客觀上形成了比鄉鎮經濟更具競爭力的發展模式,分稅制的實施、市管縣體制的確立又在體制上進一步強化了大城市相對于小城鎮的體制優勢,兩相作用之下,小城鎮發展開始滯后于大城市發展。盡管在政策層面上多次強調小城鎮的重要性,③但小城鎮的發展實質上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
回顧我國城鎮化的進程與小城鎮的發展,以下的認識是值得思考的:其一,工業化與城鎮化相伴隨行。計劃經濟時期為實現工業化而犧牲城鎮化的發展戰略盡管有短期效應,但長期來看,弊害較多,工業化缺乏必要的空間和要素支撐。反過來,由于制度扭曲造成的過度依靠城鎮化來推動工業化的實踐中,工業化和城鎮化均缺乏可持續的基礎。其二,城鎮化進程自然趨向于大城市(特別是其中的特大城市)更快發展。以小城鎮為主的發展戰略有較強的社會價值,但經濟效率較低。這在上世紀80年代以后“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城鎮化戰略實施中得到了充分的證實。如果出于社會價值實現的考慮,要促進小城市的發展,需要制度和政策的有意識和實質性的傾斜。而這種傾斜與市場發展的方向有可能相悖,因此并不容易獲得決策層的認同。其三,制度的調整與變革是推進城市快速發展的基本前提。肇始于農村的市場化改革帶動了小城鎮的發揮,而隨之興起的城市經濟改革又引起了小城鎮的衰落,改革的脈動決定著中小城市的命運。沒有相應的體制改革,就不會有小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三、從發展現實需求看發展小城市的必要性
當前,城鎮化和工業化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基本驅動力。我國城鎮化面對的挑戰是:農村勞動生產率低下,城市綜合承載能力薄弱,城鎮化質量的區域化差異逐步加大。人財物快速流向沿海發達城市和主要的行政中心城市,廣大中西部地區和發展相對滯后的中小城鎮,亟需國家的政策性扶助。有鑒于此,中央有關文件指出,當前要把推進城鎮化發展制度創新的重點放在大力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上面,通過戶籍制度、保障房建設、財稅和投融資、土地利用計劃、產業政策等方面的改革與調整,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提高城鎮規劃水平和發展質量,使其成為繁榮農村經濟、轉移農村勞動力和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載體。小城鎮發展戰略的實施已經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切入點。
可以將小城市在我國城市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總結為以下幾方面。第一,小城市是未來城市群、城市帶的基本單元,是優化城市群空間布局的重要形式。相對于大城市而言,作為次級單元的小城市,無論是在生產、消費還是銷售、物流,小城市均能起到積極的作用。第二,小城市是城市帶動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平臺,是繁榮農村經濟、轉移農村勞動力的重要載體。工業化所要求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同步提高,有賴于小城市作為市場和服務的功能發揮。第三,小城市作為公共服務提供平臺的發展和壯大,在促進城鄉統籌的同時,也將成為未來公共服務體系覆蓋更為廣闊空間范圍的前沿基地。
四、借鑒國際經驗、啟動小城市發展體制機制改革
小城市的發展中,政策和制度的影響較大。以下就以韓國和美國的小城市發展為例,對政策在中小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做簡要的闡述。
其一,政策和制度需要鎖定作為作用對象的小城市。究竟哪些中小城市應當成為政策作用的主要對象,政策需要有一個較為明確的界定。例如在韓國,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以實施“小城市開發事業”的形式促進小城市發展,以促進社會福利較為公平的供給,緩解城鄉發展差異。所謂小城市,就是人口在2萬人以上10萬以下的、作為下級農村定住系統的農村上級中心地。在行政上,小城市高于邑面(鎮)、低于中心城市(縣)(申東潤,2010)。美國的相應計劃,即社區(小城市)發展撥款計劃(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Program, CDBG)于1974年啟動,CDBG致力于為中低階層提供住房、生活環境、經濟機會等方面的支持。除一般的人口要求外(人口5萬以上的城市、人口20萬以上的縣),CDBG采用一個指標打分體系來識別需要支持的社區和小城市,主要包括三個指標類別,分別是:第一,反映小城市或社區的貧困狀況、住房的老化情況、小城市的衰退情況,權重85%。第二,反映外來移民增長影響下的社區或小城市財政壓力,權重15%。第三,反映貧困深度和密度,權重5%。1982年,小城市的CDBG由聯邦政府移交州政府管理。州政府采用的指標略有不同,除上述指標外,還包括了社區或小城市的基礎設施缺陷(5%)的評估。美國與韓國相比較,美國的識別過程更為復雜,但就指標的設計來看,整個CDBG政策的指向人群非常明顯,越是貧困人口集中的地方,財政支持資金的力度越大。
其二,在政策指向上,“人”的因素應當重于“城”的因素。國外很多國家的中小城市發展經歷了從側重公共服務到側重小城市功能打造、再到重視人的發展的改變。韓國的小城市開發一開始是以提高小城市公共服務能力為主要目的的。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文化福利設施、災害防治、住宅改善、產業發展等多個項目。隨著基礎性工作的完成,當前的主要工作已經轉向為小城市尋找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戰略上來,城市新產業和城市功能的打造成為政策作用的重點(申東潤,2010)。美國的CDBG近年來每年投入的資金大約在42億到44億美元之間。主要采用兩個公式來決定支持的資金大小。公式A主要看城市的人口(權重25%,下同)、貧困人數(50%)、住房擁擠人數(25%),公式B則主要看收入低下人數(20%)、貧困人數(30%)、轄區內居住在1940年前的房屋內的人數(50%),根據這兩個公式計算出來的撥款額度,取其大者再乘以一個系數作為最終的依據。在最近的調整中,人口和經濟情況的權重被進一步降低,貧困的權重進一步提高。資金的支出主要在小城市和社區的住房、公共設施、公共服務、城市/社區管理和規劃等方面。從這一指標上看,聯邦政府通過CDBG作用的最終對象并不是城市或社區,而是人群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1982年以后,在聯邦政府層面,CDBG的資金使用保持前后的一致性。但在各州的執行中,有些州將CBDG的資金主要用于社區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上(Fossett, 1987),有的州則將其用于社區經濟發展方面(Krane, 1987),所取得的效果并不一致。
其三,行政體制是否有效,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居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是否得到發揮,是小城市戰略能否成功的關鍵。在韓國的小城市建設中,中央政府起的作用較大,而地方政府受行政決策權限和財政權限的約束,參與激勵較小。而自上而下的小城市戰略,盡管在形式上建立了地方政府和居民意見反饋機制和參與機制,但資源投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局面使得這些機制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申東潤,2010)。美國的CDBG在執行過程中,明確提出了以下基本原則:①社區建設應以創造就業崗位和價廉安全體面的居住環境為起點。②社區的規劃和執行應當由社區策動,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進行。③社區建設中的復雜問題需要協調、綜合和可持續的解決方法。④政府的運行必須更有效率、更有效果。⑤通過交流、溝通,促進居民對社區建設信息的把握,以提高居民參與社區建設的程度。1982年,當小城市CDBG的管理權限轉移給州政府后,獲得CDBG計劃支持的小城市數量大大增加,小城市也能夠更為自由地根據自身發展的實際來使用資金。但就目的而言,由地方政府控制的CDBG計劃,在資金使用的效果上,對中低階層的住房等基本生活條件的改善并未起到直接的作用(Watson,1992)。
注釋
①按照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2008)的描述,今天的城鎮化盡管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扮演了非常積極的角色,但同時也帶來了城市分異(Urban Divide)問題,即經濟分異(收入不平等)、空間分異(空間不平等)和社會分異(機會不平等)等三個方面。其中空間分異的原因較為復雜,既有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也有土地和房產市場的低效率、無效的金融機制和落后的城市規劃等因素的影響。解決城市分異的思路就是塑造包容性城市(Inclusive City),通過就業幫扶、財政激勵和規范的合同和司法體制來提高經濟包容性,通過保障居民權利、保障居民和非政府組織對城市治理的參與來提高社會包容性,通過城市文化的培育和發展來提高城市的包容性。
②(1)1949~1957年的起步時期。1949年,我國共有132個城市,城鎮化水平10.65%。全國居住在城鎮地區的人口共5767萬,其中城市市區人口3949萬。隨著“一五”計劃的實施,到1957年,我國的城市發展到176個,城鎮化水平上升到15.4%,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長6.25%。(2)1958年~1978年的緩慢發展時期。1950年代末期的經濟波動和自然災害,以及1966年開始的文革,使得城鎮化進程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緩慢。1966年至1978年,全國僅增加城市26個,平均每年增加2個,1978年全國城市193個,城鎮人口為17245萬,城鎮化率上升為17.92%。(3)1979年~1999年的穩定快速發展時期。改革開放后,隨著發展政策的落實和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城鎮化進程大大加快。1980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陸續展開。進入90年代后,中小城鎮化發展戰略得以實施,帶動了城鎮化水平的快速提高。1982年,城市數量 245個,1999年,城市個數達到666個,新增城市473個,城鎮化率達到34.78%。(4)2000年至今的加快發展時期。至2009年底,全國共有設市城市654個,城鎮化水平46.59%,城鎮人口達到62186萬。其中,地級及以上城市287個(包括4個直轄市和15個副省級城市),縣級城市267個。全國200萬以上人口城市23個,100-200萬人口城市33個,50-100萬人口城市86個,20-50萬人口城市39個,市區非農業人口在20萬以下的城市共273個。城市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顯著。
③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件首次明確指出:“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有利于鄉鎮企業相對集中,更大規模地轉移農業富余勞動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動,有利于提高農民素質,改善生活質量,也有利于擴大內需,推動國民經濟更快增長”。 2002 年十六大報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2008 年,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形成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互促共進機制”。2010年,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按照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帶小的原則,遵循城市發展客觀規律,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科學規劃城市群內各城市功能定位和產業布局,緩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區壓力,強化中小城市產業功能,增強小城鎮公共服務和居住功能”。
[1] 中國城市狀況報告(2010/2011)[M]. 聯合國人居署.2011.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計劃財務與外事司.
[2]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09)[M]. 中國計劃出版社. 2010.
[3]李善同. 中國城市化過程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J]. 中國建設信息. 2008(6). 6.
[4]申東潤. 韓國小城市發展的經驗[J]. 當代韓國. 2010夏季號.55-65.
[5]Scott, A. J.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 Geographical Agenda[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6, No. 1 (Mar., 1986), pp.25-37.
[6]Ledent, J. Migratio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0, No. 3, Third World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A Symposium (Apr., 1982), pp. 507-538.
[7]United Nations.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0/2011: Bridging the Urban DIvide[J].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2008.
[8]Manfred Perlik, Paul Messerli, Werner B?tzing. Towns in the Alps: Urbanization Processe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Demarcation of European Functional Urban Areas (EFUAs) in the Alps[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 21, No. 3 (Aug., 2001), pp. 243-252.
[9]CDBG Formula Targeting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Need[M].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2005.
[10]Watson, S. S. Decentraliz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Decisions: A Study of Oklahoma's Small CitiesProgram[J]. Publius, Vol. 22, No. 1 (Winter, 199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 109-122.
(責任編輯:楊致遠)
2015-05-05
李崑(1980-),男,漢族,四川資陽人,碩士研究生,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院學位辦副主任,助理研究員/編輯。
F292
A
1008-5955(2015)02-0050-05